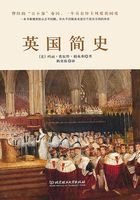第一节 努尔哈赤优礼蒙古贵族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初三,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贝勒巴克、莽果尔代台吉、巴浑台吉前来向努尔哈赤叩贺新年。他们带来的骆驼、马、牛、羊,都没有接受,全都退给了他们。巴克之所以前来叩贺新年,据他前此派来的使者的解释是:巴克台吉说,在他被捕后释放时曾讲过,每年来向汗叩头,那话是不能违背的。
同一天,蒙古喀尔喀巴岳特部恩格德尔额驸来向努尔哈赤叩贺新年。
正月初八日,蒙古喀尔喀的拉巴实希卜台吉,带他属下的四十户和畜群,叛逃来了。
当天,后金对拉巴实希卜给予赏赐,赏赐的物品有:貂镶皮袄、狐皮子、貂皮帽、皂靴、玲珑腰带(原档残缺)及缎九匹、毛青布一百匹、银酒海一件、碗二个、碟二个、櫃八个、狍四只、雉四十只、米八斗、柴八车,并全给一应器皿。赐其随从皮袄六件、貂皮子四件、腰带一条。赐莽古塔布囊(塔布囊意为驸马)貂镶皮袄、猞猁皮衤屯子,貂皮帽、皂靴、玲珑腰带、毛青布一百匹、蟒缎一匹、缎九匹及櫃八个,并全给一应器皿。又赐狍四只、雉四十只、米八斗、柴八车。赐其十名随从镶肩棉袍十件、腰带四条。
正月二十一日,遣释鄂齐尔桑时,台吉巴克誓曰:“巴克我被擒于阵,该杀之身,蒙父汗收养,遣我回里,今又释代我为质之子鄂齐尔桑归。若负父汗养育之恩,中他人谗言而变心,巴克、多尔济、鄂齐尔桑我三人,定受天地谴责,祸患及身。若不远离与父汗不睦之伊勒登贝勒之子,则受天地谴责,殃及我等。”原注:鄂齐尔桑乃巴克贝勒之长子,曾代父为质。引者注:多尔济为巴克之次子。(见《满文老档·太祖》册43.)至此,喀尔喀扎鲁特部贝勒巴克、色本等人因参与宰赛对铁岭的掠夺而被后金俘获一事全部完结。
正月二十五日,遣巴克台吉、鄂齐尔桑、多尔济还,并赍书曰:“台吉索诺木饮酒,妻子未加劝阻,死后而泣,被我国人恥笑。尔多尔济、鄂齐尔桑二人,若不谏阻尔父饮酒,父因酒殒,悔之莫及,泣而何益?当令尔国之人等,凡逼人饮酒者,皆治以罪,殷实之人罚马、中等人罚牛、末等人罚羊。”(《满文老档·太祖》册44.)
二月十四日,蒙古喀尔喀巴岳特部恩格德尔额驸遣来送书的使者巴拜返回蒙古,努尔哈赤要他带书信给恩格德尔,书信说:“额驸!尔以二百男丁往会于喀尔喀,其喀尔喀之业兴乎?前来我处,我之势强乎?今往彼处,我于尔何怨有之?若从我言前往彼处,则赐尔千人男丁一年所得之银六十六两,粮一百一十石,仍将给尔;若不从我言,不往彼处,而留守此地,则不仅不给千丁所得之官银、官粮,且不准尔之使臣往来。而喀尔喀诸贝勒皆知尔,看守其逃人的萨拉沁,仍将与尔为敌。若返回后,召之即来,则不治尔罪。其先来之人,皆给官职,沿及子孙,累世不绝,且不究其罪,并以黄册敕书记录钤印颁给之。所谓杀身之罪何必挂齿,尔与豢养之父汗争位乎?除非因争位,杀豢养之父汗及诸额驸、妹夫,叛往蒙古之地而死于追赶者之箭锋而已。除此之外,岂有藉故他罪而杀尔之理乎?勿再提及是言。以愿归宁求生之人,赐尔等八千男丁之官粮官银、衣食充裕,任尔围猎放鹰,往返游玩,行止不限。若不耐久居,则可言明,若欲往蒙古之地,亦不禁止,汗与贝勒亲送渡河。归来之时,赐额驸男丁二千,格格男丁二千,岱青(恩格德尔之子)男丁一千,共男丁五千。每年得银三百三十两,粮五百五十石,供差役九十人,牛四十五头,收藏诸物之兵丁九十人。赐尔弟男丁二千,得银一百三十二两,粮二百二十石,供差役三十三人,牛十六头,收藏诸物之兵丁三十三人。赐尔之二子各五百男丁,给一子之五百男丁,每年得银三十三两,粮五十五石,供差役九人,牛四头,收藏诸物之兵丁九人。赐额驸格格及尔弟、尔三子,共男丁八千,每年得银五百二十两,粮八百八十石,供差役一百四十人,牛七十头,收藏诸物之兵丁一百四十人。”(《满文老档·太祖》册45.)
努尔哈赤对有很大可能来归的恩格德尔额驸夫妇许下如此丰厚赏赐的承诺,不仅在于争取仅仅辖有百名男丁的普通台吉恩格德尔一家,而且要争取蒙古各部有更多的贝勒台吉来归,要与后金的主要敌人蒙古察哈尔部展开更大规模的争夺战。
七月初三日,努尔哈赤的女婿恩格德尔,驱其人丁牲畜前来,为示诚信而誓曰:
“愿仰赖英明汗为生而前来。既来之,则蒙汗怜爱,亲如赤子。倘有负汗父眷养之恩,则上天鉴之。既见恶于父母兄弟而来投,所思一切尽已得之。若不念汗之优宠,逆理而行,则祸患及身,必致灭亡。若秉持忠心,竭力图报,必享安逸之福也。”
七月初四日,蒙古科尔沁兀鲁特诸贝勒之誓词曰:
“闻英明汗之名,见恶于察哈尔汗,为仰赖英明汗而来。来之即蒙汗怜悯如子。倘不思汗之眷养,我等蒙古诸贝勒,怀有邪恶之心,则其怀邪恶之心之贝勒,必为上天鉴察,以致祸患及身;若思令汗之眷爱,秉以忠心,则上天眷悯,共享太平之福也。”
同一天,努尔哈赤令其诸子誓曰:
“上天佑汗,使之与异国蒙古各部贝勒相会。仰体天心,则蒙古诸贝勒即获死罪亦不致身亡。不思天意,则与会之诸贝勒,凡有心怀二志,包藏祸心者,上天鉴察,必降祸患于起事之贝勒。倘能信守对天之盟,仰体上天之意,尽忠尽善,合谋相处,则蒙上天垂佑,世代得享太平之乐也。”
努尔哈赤说:“喀尔喀之诸贝勒上再无主,彼等各自随意而生。为求生活更加安逸,前来归附。兀鲁特诸贝勒,恶其蒙古国汗,故慕我来归。凡此来归之诸贝勒若有罪,则与我八贝勒同等视之。死罪则免其死,遣还故地。来归之诸贝勒,尔等于此处结亲立业,凡娶我女之人,当勿以我女为畏。实乃怜悯尔等远地来附,以女妻于尔等而已。岂令尔等受制于女乎?至于尔等蒙古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以女妻幕友及大臣等,每凌辱其夫扰害其国者,我亦有所闻。倘我女有如此凌辱其夫者,尔等当告于我……该杀者诛之,不该杀者则废,另以他女妻之。若诸女不贤,不告于我,则尔等之过。倘尔等告之,我等庇护而不加责斥,则我之过也。尔等若有艰苦之情,毋庸隐讳,可将所思告我。”(《满文老档·太祖》册57.)
就在努尔哈赤大力争取蒙古各部前来归附时。发生了后金的额驸巴拜之妻、汗家格格自缢的事件。巴拜为蒙古贝勒,他所娶之妻是汗的女儿,但究竟为哪一位公主,不详,很可能是努尔哈赤的族女或养女。看来这个事件轰动一时,并牵涉出另一个事件。
努尔哈赤说:“巴拜额驸之妻格格自缢。闻巴拜额驸之母哭诉曰:‘昔嫁栋鄂额驸之子格格自缢身死,故杀栋鄂额驸之子以报之。今我等与彼相同,如何是好。’岂可将尔与彼等同之?……我将长女(固伦公主,栋鄂格格)妻栋鄂额驸,招其为婿。复将我二孙女妻其二子。然竟欺凌其女,将一有夫之美妇,离其夫,给其子为妾。又收所降之二女,未还其夫,修饰后给其子。因美饰此三美妇而与之,故而冷淡我孙女。因受凌辱,该女将其苦告其叔兄。所告之言诸贝勒未曾奏我,即擅自劝而遣之。该女之夫因其告之,竟将其妻殴踢致死。如此致死,彼等却告以自缢而死。经众人前往审验,并非自缢身亡,乃他杀致死,而以自缢掩饰之。罪状即此。倘将尔等为求生而来归附之贝勒与交战不胜而归降之人,一体相待,何以称我为英明乎?系何人因何故将尔等与彼同等待之?高山之上见及远,善人之名闻于后。喀尔喀诸贝勒闻我为善,情愿来归,故恩养该情愿来归之诸贝勒,乃我亲自所定。所谓后代子孙皆以眷养之言,此乃是也。眷养尔等尚未足矣。”原注:巴拜乃蒙古国之贝勒,汗之婿。栋鄂,乃路名。所谓额驸,降汗之诸申国时,以长女妻之,故云额驸,名何和里,(见《满文老档·太祖》册57.)
通过上面努尔哈赤的自述,牵涉出两例汗家女儿婚后遭遇人身伤亡的不幸事件,即蒙古巴拜额驸之妻、汗家格格之自缢而死的事件,和在此之前栋鄂额驸何和里之儿媳、汗之孙女之被殴踢致死的事件,这两件事说明:努尔哈赤家族嫁给女真和蒙古贵族的众多女儿的婚事也有不称心如意者,有的甚至酿成人身伤亡的悲剧,而且不是一件,但遇到这类事件,努尔哈赤都能根据客观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给予不同的处理,而不是一律处死出事之额驸。栋鄂额驸何和里之子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后来喜新厌旧,将其“踢殴致死”,并伪称“自缢而死”,而被努尔哈赤杀掉;而蒙古巴拜额驸之妻、汗家格格自缢而死,与前一情况不同,其夫没有受到惩处。并且此后努尔哈赤仍不断地嫁出汗家的女儿,其中大部分嫁给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坚持满蒙联姻,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婚姻联盟来招抚,乃至最后混一蒙古各部。
第二节 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和后金法律酷刑一瞥
天命思想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基本的统治思想,后金的统治阶级也接受了这一思想观念,作为后金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的努尔哈赤就自称为“天之子”,即“天子”。他的天命思想,既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又受中国历代天命思想的强烈影响。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御衙门,谕诸贝勒大臣说:
“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即为奴。汗以天为父,敬念不忘,明修天赐基业,则汗所承基业何以废也?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敬念不忘,勿怀贪黩之心,勿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以公忠自效之,则诸贝勒大臣之道,何以败也?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敬念不忘,不起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件,不违法度,竭尽其力,则祸患何以及身也?奴以主为父,敬念不忘,不生盗贼、奸宄、强暴之事,谨守奴仆之分,尽心效力,则刑戮何以随身也?汗受天之恩,而不顺天意,乃以自恃其才力而为之,不勤修政道,逆理而行,天若谴之,欲废其汗,汗能自守其位乎?贝勒大臣受汗之恩,而不顺汗意,乃以自恃其才力而为之,存有盗贼、奸宄、强暴之心,恣行贪邪,汗若谴之,即褫贝勒大臣之职,贝勒大臣能自保其爵乎?民违贝勒大臣之法度,行盗贼、奸宄、强暴悖乱之事,贝勒大臣若谴之,则灾祸及身也。奴违主命,不敬谨效力,而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受其主责之,则刑戮相随也。尝闻古籍有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秉忠善之心而失者无,怀邪恶之念而逞者亦无。故自上而下,凡秉忠善之心而行者,福必积矣。福大岂有不致善之理乎?凡怀邪恶之念而为者,罪必集也。罪大岂有不遭殃之理乎?凡诸申、汉人、蒙古,皆应去邪恶,存忠善。自汗、贝勒乃至刍荛(割草打柴)之丁,运水之妇,祸非外来,皆由自致也。何则,汗与贝勒乃天所授,如不修道行善,以副天意合人心,乃存小人之心,则天必谴之,基业废矣。夫大臣乃汗之所授,如不能以所委之事,竭尽忠勤,乃存邪辟怠慢之心,则汗必罪之,其身败矣。刍荛之丁,运水之妇,如不违其主,敬谨尽心效力于所委柴薪运水之事,则其主又以何罪之?若不尽心效力而怠顽违抗,其主生怒,则必将罪之矣。所谓凡人之福,皆由自致者,此也。”(《满文老档·太祖》册44.)
努尔哈赤接受汉族的天命思想和汉族儒家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的伦理理论,结合女真族的社会实际创造出的如上伦理学说,无非是要建立起君、王(贝勒)、臣、民、仆的等级体系,并使这个体系中的各种人物都能各得其所,各安本分,从而达到稳固后金的统治秩序的目的。
如果有谁触犯了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君、王(贝勒)、臣、民、仆的等级体系,犯下了“盗贼、奸宄、强暴之事”,努尔哈赤就要予以严惩,给以无情的镇压。后金在行使镇压之权时,其刑罚之残酷令人惊诧不已。
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颁布口头法,严厉镇压偷盗现象。他说:
“能不偷盗吗?今后如果男人为盗,要女人脚踩赤红的炭,头顶灼热的铁锅处死刑。如果畏刑,就要很好地规劝各自的夫。不听规劝,就要告发。男人偷盗的财物粮食,女人不要谁要。雍舜为盗,杀了雍舜的妻。”(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58.)努尔哈赤以口头法的形式规定的这种酷刑,使人有些不敢相信。
事实是,在努尔哈赤时代,在口头法和某些成文法的法律条文中充斥着许多惨无人道的酷刑。惩处的办法多种多样,离奇怪诞,残忍酷烈,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下面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案例。
1.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努尔哈赤的胞弟舒尔哈齐被削夺兵权后移居黑扯木。努尔哈赤命令收回舒尔哈齐的财产和阿哈,使其孤立,时有族人名阿席布者,因未曾劝止弟贝勒反而鼓动挑唆,是以杀之。“又将大臣乌尔昆蒙兀,吊缚于树,下积柴草,以火焚之,借以辱弟贝勒,使孤立。”(《满文老档·太祖》册1.)最后将大臣乌尔昆蒙兀活活烧死。
2.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苏克达的舒赛牛录的阿奇,离开众兵,杀了鸡烧着吃,另有四人和他一起吃时,被明朝清河的士兵全部杀死。对于这五个被明兵杀死的士兵,努尔哈赤命令,“割取他的肉分给众牛录看,(使之)加以警惕。”(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
3.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满洲五大臣等看了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书信后,都异常愤怒,“有谓来使可杀,有谓可劓刖之放归”。《满洲实录》卷6.所谓劓刖,都是我国古代的酷刑,割掉鼻子叫作劓,砍掉脚叫做刖。
4.天启元年(1621年),在海州发现八个汉人向井中投毒药,在逮捕了他们后,让这八个投毒的汉人吃自己的毒药,结果这八个人全都毒死了。(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2.)
5.天启元年(1621年),在一次作战中雅逊败走,致使冲入军中的四贝勒皇太极的处境十分危殆。努尔哈赤给雅逊定的惩罚是:“罪应寸磔”,但后来没有执行,只是削其职。(《满洲实录》卷6.)磔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酷刑,即分尸。寸磔,就是把犯人的肢体分裂成若干个很小的碎块。杨倞注:“磔,车裂也。”
6.天启二年(1622年),汤古岱阿哥旗的尼隆阿牛录的一人盗诸申(女真)的鞍,处以乱刺鼻、耳、脸、腰刑,杀了。(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5.)
7.天启二年(1622年)前来后金侦察的十二个朝鲜人在被捕获后,剜了其中十人的眼睛后杀了,另外二个人刺眼、削鼻耳,送书信被放回去了。(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7.)
8.天启二年(1622年),三个八旗兵在广宁被蒙古人杀死。凶手被捕获后,努尔哈赤命令驻守的诸大臣说:“牢固地拘留那男人。穿透手掌心钉在木头上,骑着驴,把两脚捆在驴的腹下带来,唯恐跑水自杀。带到这里来,让众人看着处死刑。子女们在那里,让众人看着杀死。”(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9.)
以上所列,只是努尔哈赤时代官方所实施的酷刑中的一部分,远远不是全貌。上行下效,在民间,流行的酷刑也不少,只是缺乏文献记载,后人难以考证而已。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满文老档·太祖》中记载了一个私人用刑的案例:女奴隶主锡拉纳的弟弟阿讷的妻子,“竟无先例地烙家婢的阴部”。(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42.)就连后金当局都认为这个女奴隶主的做法太过分,应予严惩,定其死罪。后来免死,刺了耳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处治这个残忍的女奴隶主的同时,法官又指责受迫害的女奴不该逃走,并判了她削鼻耳之罪。(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42.)这一判决显然是针对她逃亡做出的。女奴隶主施用酷刑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努尔哈赤时代酷刑严重存在于民间的客观状况。
公私酷刑的大量存在,说明女真统治集团的残忍野蛮和缺乏教养,说明这个时代的法律还很幼稚,还没有完全脱离蒙昧状态,奴隶制度的野蛮势力在法律上还很强大。这些都是努尔哈赤时代在由习惯法、汗的口头命令向成文法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十二日,努尔哈赤的同父母的妹妹、小福晋死了,二女从死,(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59.)即以二女殉葬。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努尔哈赤时代社会风俗的残暴性。这是努尔哈赤最后一个胞妹病亡,努尔哈赤前去吊唁,并大哭。
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至少有三个女儿,也就是说努尔哈赤至少有三个妹妹。
塔克世的女儿之一,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八月嫁给了归附努尔哈赤的嘉穆瑚寨主、伊尔根觉罗氏噶哈善,他是努尔哈赤的最早、最得力的“古出”成员之一。翌年(万历十二年、1584年)努尔哈赤的妹夫噶哈善被努尔哈赤的族叔(三祖索长阿之四子)龙敦组织人暗杀了。后来努尔哈赤又把自己的这一胞妹嫁给了郭络罗氏常书。常书是哲陈部沾河寨主,因此人们称后与常书结婚的塔克世的女儿之一为沾河公主。沾河公主与常书婚后共生了三个儿子。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沾河公主以常书不仁,想要离婚,但汗念最初的交情,没有准许离婚。夫(常书)在妻死前约十五年就别居,即使夫迁延待死,妻也不去会面。作为兄的汗,多次对妹发怒,但对妹夫仍然爱护。(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59.)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十二日病死的塔克世之女就是努尔哈赤的这个妹妹,是他仅有的一个胞妹。
塔克世的女儿之二,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八月嫁给了郭尔罗氏杨书,杨书是常书之弟。万历十一年(1583年),常书、杨书和噶哈善同时归附努尔哈赤,三人成为努尔哈赤“古出”的成员。上述塔克世的二女,何者居长,何者为次,不得而知。
塔克世的女儿之三,是塔克世的幼女,嫁给了后金的开国者之一、清初五大臣之一的钮祜禄氏额亦都。(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4;《清史稿·常书传》卷233;《清史稿·额亦都传》卷231;《清史稿·公主表》卷172.)
塔克世的上述三女并不全是努尔哈赤的胞妹,只有嫁给噶哈善者为胞妹。
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汗家的女儿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满文老档·太祖》记载说:二十四日早晨,巴都虎副将往告:兀鲁特之奇布塔尔台吉射杀我给昂阿拉阿哥为女之格格。遂将其执而问之曰:“与尔有何怨恶?”奇布塔尔对曰:“并无怨恶之处,乃我死数已定,故而杀之。”该兀鲁特众贝勒曰:“既已杀汗之戚,请解我处,由我等处以凌迟之刑。”我诸贝勒曰:“倘凌迟处死异地来附之贝勒,恐将以恶传闻之。”故交付彼等处以绞刑。原注:奇布塔尔酗酒射杀。该女乃汗之近族孙。这里又出现了当时流行的两种酷刑:凌迟和绞刑。凌迟是古代分割犯人肢体的一种惨酷的死刑。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时代流行的公私酷刑着实骇人听闻。
后金进占广宁以后,首先由于辽民的激烈反抗斗争,后金不得不集中全力巩固后方;后来由于明廷重用孙承宗和袁崇焕挡住了后金西进的道路,明金的西战场陷入了胶着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努尔哈赤大力拓展其他对明斗争的战线,加紧对北方蒙古和对东方东海女真以及朝鲜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