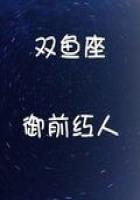由于国内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和国外汉学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中国文化在包括南北欧以及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影响。这至少可以向国人传达这样一些信息:即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遗产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魅力,这一影响和魅力现在并不是在逐渐消散,而是在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可以在世界文化的“中心”———欧洲见出。在新的世纪,它必将以新的姿态展现出新的活力。毫无疑问,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这一课题已经引起了国内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注意,他们开始搜集资料、著书立说,试图向国人展现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介绍以及在西方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研究概况,以便弥补过去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中实际上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之缺憾。而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西方的了解则大大甚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① 正如季羡林先生在20 世纪末所正确指出的,“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在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想要上纲上线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必须要认真完成的。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① 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说来就是这样一个工程浩大的“送去”计划的一部分:即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中,我们一方面要总结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中欧文化的偶然接触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则应有目的、有计划地把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送到西方去。鉴于南北欧稍微远离欧洲帝国的中心,而且又有不少语言上的障碍,因此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讨论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欧洲的传播和接受时有意无意地竟然忽视了这一不该忽视的地区。而本书的写作在这方面也许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但其主要目的仍在于以此为基础促使研究者们继续深入地研究和发掘那些未开垦的学术处女地,以弥补中欧文化交流中实际上存在的不平衡状态之缺憾。
我们说,要把中国文化的辉煌成果送出去,这绝不意味着也像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对东方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殖民主义式的侵略和渗透,正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的结尾中所指出的,“我不希望向我的读者表明,东方主义的答案是西方主义”。② 我们不应当以一种不恰当的“西方主义”来作为西方人建构的“东方主义”的对立面,从而使得这二者长期存在的对立继续下去;③ 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致力于平衡中西方文化交流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逆差,从而使西方人更多地消除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偏见,更加全面、完整地了解中国,这样也许对我们继续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成果不无裨益。那么我们今天要把中国文化送出去,是不是就意味着对历史上曾实行的拿来主义措施予以否定呢?绝不是这样。拿来和送出实际上标志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两个不同阶段:当有着辉煌传统和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便试图甩掉有可能阻碍其前进的历史重负,从西域借鉴新的思想和文化成果是十分必要的,这时,我们的立足点自然就是拿来,即把国外(包括西方)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成果有选择地拿过来用以发展中国自身。可以说,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精华对推进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于一些保守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惊呼中国文化“被殖民”了,中国现当代的文学语言充满了模仿之作和欧化的语言,新诗也早已不见了古典诗词的典雅词句和严整的韵律,甚至连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和独特话语等等。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世界开放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全盘西化”所造成的后果。针对这种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成果的论调,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情况果真如此严重吗?从本书所披露的欧洲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借鉴来看,恐怕远非如此。一方面,近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确实在很多方面受到欧洲作家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优秀的欧洲作家的名著几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家喻户晓,他们的优美的文学语言虽然经过翻译但仍然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语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些欧洲作家中的不少人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不少精神食粮,对他们的创作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因此,这样的中外文化关系应当是互动的,影响和启迪也应当是相互间的,并不存在谁“殖民”谁的问题。
确实,中国自打开国门以来,就一直是进口大大多于出口,不仅是科学技术上如此,文化艺术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达国家未必就能够相应地生产出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有时反而恰恰在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倒能够出现伟大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大家。这一基本的常识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我们的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却经常以自己的著作受到西方汉学家的称赞而倍感自豪,似乎一切只有西方的标准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的汉学界最近几年确实已经发生了一种转型式的变化:从注重古典轻视现代逐步过渡到越来越密切地关注现当代中国仍在进行着的社会变革,以及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事件和个人情感的变化;从拒斥理论逐步过渡到关注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的前沿课题,并试图在方法论上进行革新。此外,全球化时代网络的发达和无所不在,更是使得传统的据稀有资料为己有的做法过时了,因此,在这方面,西方的汉学家确实有许多可以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对语言的重视和对原始资料的追踪甚至达到穷尽的地步,著述选题的慎重和论述的严密,以及注重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乃至直接对话,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国国内的同行认可等等,均是我们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如此,我们仍应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自信,而不应当以自己的成果是否得到西方汉学家的承认为标准。
2 Decolo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