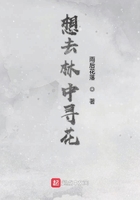长鲸靠着秋千晒了晒太阳,钟侯川就像个小丫鬟一样立在旁边照顾着,生怕长鲸睡着了会摔跤,晒到钟侯川额头开始冒汗了,长鲸仿佛才醒过来,拉着钟侯川进屋了。
钟侯川勤快的给长鲸倒了杯茶,长鲸笑道:“不枉我照顾你一场。”
钟侯川这才反应过来,好奇的问道:“大当家昨晚怎么知道有人会来行刺,来的那样及时?”
长鲸指了指门后的哑铃,钟侯川好奇的过去看了看,哑铃像缩小版的寺庙撞钟,小钟里面垂下一根五彩斑斓的绳子,绳子很长,垂到钟侯川的膝盖处,钟侯川手刚放上去,长鲸便插话道:“老头才走你就想他了?”
钟侯川新奇道:“只要碰响这个哑铃,大当家就会赶过来么?”
长鲸咂嘴道:“这是一副对铃,我睡觉怕吵,老头特意让人寻来的哑铃,所以不管怎么摇,这个也不会响,老头那还有一个,是会响的,只要我这边一碰,他那边就会响,二叔说这叫‘彝铃’,是外族人的物什。我自己立院子住以后老头他们不放心,就寻了这个东西来。”
钟侯川虽然来这不久,却被长鲸身边的物什惊讶了无数次,很多东西是连他这个身份高贵的世子都没见过的。
俩人正讨论着这彝铃,四叔火急火燎的跑进来,拉着长鲸到处查看,长鲸配合着他转来转去,看过伤口以后才放心的道:“还好还好,胳膊腿都齐全,其他只是皮外伤。”
钟侯川:“.…..”
长鲸:“.…..四叔,要是缺胳膊少腿了能等到现在才找你么?我就算爬也早爬你那去了。”
四叔又放了一堆药在桌上,自言自语的喃喃道:“最近怎么了,一个个的老受伤,以前就你这最不需要药材,最近全往你这搬了。”
长鲸反问道:“我难道不是从小受伤惯了的么?”
四叔呆了片刻,好像是那么回事,不过长鲸自觉,每次受伤后都自己蹦跶到药庐去找他上药,长鲸的院子还没受过汤药的熏陶。
四叔再三详述了俩人各自吃的药,嘱咐钟侯川和长鲸俩人要相互照顾,长鲸一看这架势,赶忙胡乱答应着就把四叔打发走了。
钟侯川认认真真的听了去给长鲸煎药,没想到长鲸不领情,一点要喝的意思都没有,钟侯川就端着药碗跟在长鲸后面,长鲸到哪他就跟到哪。
长鲸不耐烦道:“你是牛皮糖么?”
钟侯川耐心的解释道:“猜到你可能怕苦,我特意加了花蜜进去,不苦的。”
长鲸:“你就是加一碗花蜜进去我也不喝。”
钟侯川也不打算和她斗嘴,就站在她面前,把药敬到长鲸面前,长鲸装瞎看不见,后来自顾自的躺床上睡了一觉,没想到醒了的时候,钟侯川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还在床前立着,看样子刚刚去热过一遍了。
长鲸被磨的没了脾气,坐起来道:“你先去把你的药喝了,我就喝这个。”
钟侯川平静回答:“在你刚刚睡着的时候我的药已经喝了,这个是你的。”
长鲸又气恼又无奈,随后接过药碗一口气干了,钟侯川笑着接过碗问道:“没骗你吧,是甜的。”
长鲸倒也没太注意是苦是甜,钟侯川又安慰道:“我替你尝过之后才给你准备的。”
长鲸:“.…..”感觉又有些余味未了,长鲸舔了舔嘴皮,好像是甜的。
两人就那么不好不坏的相处着,那几天一到喝药的时候钟侯川就像甩不掉的黑影一样围着长鲸,两人每天都会在院子里进行几轮追逐战,固执的钟侯川每每让长鲸不得不认输。
就那么过了一段时间,钟侯川带给长鲸的新鲜感已经过了,长鲸便又开始到处作妖,搞得寨子鸡飞狗跳,隔三差五钟侯川就会听见长鲸快速奔跑时的银铃发出清脆的响声。哪怕隔了一个山头都能听见大当家挥着鞭子大喊长鲸兔崽子,父女俩三五不时的就在寨子里上演一出你追我赶的戏码,逗得寨子里的人捧腹大笑。
刚开始听到大当家挥着鞭子讨伐长鲸的时候,钟侯川活生生吓出一身冷汗,后来才发现,那根本就是这父女俩的日常,他刚来时所看到的父慈子孝才是破天荒的异象。
已经入冬了,天气虽然冷,长鲸就像个小火炉一样,穿着点单薄的秋衣就满山转悠,钟侯川可谓实打实的裹了厚厚一层,长鲸老嘲笑钟侯川是个粽子。钟侯川也算是摸透了长鲸的脾气,这丫头天生的放浪形骸无拘无束,大当家管不住她,几个叔叔又宠的无法无天,好在长鲸本性良善,没有形成些不好的习惯,因此寨子里的人虽然担心长鲸戏弄他们,却也不讨厌长鲸,隔日就能开开心心的同长鲸玩笑。
这天日暮时分,长鲸快速回家,把在看书的钟侯川拖出房间,关上门快速的换了衣服,随后出门对钟侯川道:“我衣服袖口破了,你得空帮我补一下,没空就让四叔给我下山买一套,我先出去躲一下。”说着就往院外跑了。
钟侯川没来得及问她怎么了长鲸就跑没影了,不过看样子,大概又犯事了,钟侯川叹口气走进屋里,长鲸的衣服扔的满地都是,钟侯川一件件拾起,找到破口处,拿出针线包就开始缝了起来。是的,长鲸经常爬高下低,衣服总是动不动就被割破了,钟侯川闲来也无事,研究了两天衣服的针脚走势,无师自通了好几种针法,长鲸每次拿着衣服看都惊呆了,钟侯川不仅脑子好使,手还非常巧,什么都一学就会,除了武功。
刚缝了没几针,大当家果然气冲冲的跑进屋子来,看到钟侯川正无比贤惠的给自家闺女缝衣服,惊诧了片刻,随后问道:“那鬼丫头跑哪去了?”
钟侯川乖巧的用女声回道:“她换了身衣服就出去了。”
大当家对这种温柔听话的孩子怎么都来不了脾气,可惜长鲸永远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当家抬眼往屋子扫了一圈,便气冲冲的又出去了,走到门口又折回来看了钟侯川一眼,钟侯川面色平静的看着他,大当家气道:“给她缝什么衣服,冻死她得了。”
说完大当家的人影也不见了,钟侯川无奈的摇摇头接着缝衣服。
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更何况对付长鲸这样的,大当家早就游刃有余了,不多久就把长鲸绑回去了,大当家想也不想就把长鲸带到书房去,推开门后,大当家领先跨进去,长鲸听到里面的说话声才知道大家聚在里面议事,虽然她不存在面子的问题,但这次大当家特意选在众人面前收拾她,看来是打算严惩了,便在门口彳亍。
大当家一拉绳子,长鲸才被拽进去,刚巧二叔三叔也在,看着长鲸手被绑的结结实实的,被大当家一路连拉带拖的扯到书房,随后大当家把绳子栓在自己手腕上,向众人歉礼:“抱歉,耽搁了一会儿,你们继续,我后面补上。”
长鲸被大当家拽着走到正座旁,大当家坐下后,长鲸就安静的立在大当家旁边,若是看不到那根绳子,倒颇有父慈子孝的画面感。长鲸偏生不是那样会老实的人,不停的朝二叔三叔递眼色,不时的动动被绑住的手,二叔三叔心领神会刚要求情,大当家便狠狠的剜了长鲸一眼,对二叔三叔道:“谈完正事再说。”
范伯便笑着接话道:“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商量的差不多了,就等大当家给个名目我们就可以去施展了,另外今天收到的两封外族契约书,我们研究过了,没问题,就等大当家盖了印章回复。”
大当家看出大家有意替长鲸解围,便故意拖延时间道:“把详情说与我听。”
众人:“……”
二叔接话道:“西北那边的据点已经落定,各路人马的安排也到位了,都是可信之人,中南地区还在筹备……”
长鲸一听这些官话就犯困,干脆席地而坐,不等二叔说完便已经开始打盹,不过盹了片刻头就碰到椅子上,长鲸碰醒后听到现在是三叔和范伯再说外族送来通商的契约文书,长鲸听的只打哈欠。因为哈欠声在整个书房显得十分违和,大家又把注意力放在长鲸身上。
大当家随手一甩,长鲸一下被绳子牵着扑在地上,二叔三叔都来不及接住她。
长鲸自己又站起来看着大当家,大当家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发作起来:“你说你一个姑娘家,整天穿的不伦不类,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你这样的以后哪户人家看得上你?”
长鲸踢着脚尖小声回道:“本来也没打算嫁出去。”
大当家气的拍桌而起,二叔以为大当家又要收拾长鲸,赶紧上前拦着:“大哥消消气,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三叔借机解开长鲸的绳子,长鲸调皮的对三叔道:“谢三叔。”
大当家听此更来气了,指着长鲸对二叔发怒道:“这能好好说?”
二叔把大当家按坐在椅子上,接着安抚道:“长鲸还小,在长大点就懂事了。”
大当家气的又立马弹起来,反问道:“再过两年她就及笄了,还小?”
三叔摆摆手让长鲸溜之大吉,自己过去劝大当家,长鲸刚想跑大当家一甩手上的绳子,长鲸脚下的绳子就像长了脚似的,绊了长鲸一下,长鲸又光荣的摔倒了,一屋子的人都静止了片刻。
长鲸想着跑也跑不了,干脆站起来,自觉的捧着手走到大当家面前,大当家又把长鲸捆上了,不止手,这次连脚一起捆上了,长鲸也猜不到大当家这次要用什么招数,便温顺的跟个小羔羊一样由着大当家把自己捆起来。
大当家捆完之后,心气还是不顺,皱眉问道:“这土地是会缠你脚还是长了刀子了,你的脚就那么站不住么?你就非得往树上钻,你怎么不窜上天呢?”
长鲸默默的听着数落,周围的几个长辈本来要劝解的,听大当家这么一来,大概也没事了,纷纷告辞给长鲸留面子,二叔三叔看这情况大概也没事了,便拍拍长鲸的头也告辞了。大家走后大当家又开始数落:“你知道那只犬马鸟多重要么?你知道那对鸟蛋费了多少人多少精力花了多少金子才护送到这来的么?你就这么给我碎了?”
长鲸弱弱的道:“我当时就觉得新鲜,看那鸟长的羽毛颜色十分新鲜有趣,就忍不住想近距离看看,谁曾想它竟经不住事,一看到我就自己噗嗤着翅膀摔下去死了,我也不知道那鸟窝不牢固,母鸟一扑腾那鸟窝就掉下去了,我还想抓住来着,没想到只抓到了一个边角,那两颗蛋就…就摔碎了。”
大当家反问道:“嗬,敢情我还该谢你不成?”长鲸识趣的闭嘴了,大当家气的在书房走来走去,不知道如何处置长鲸,长鲸咬着嘴唇看着到处转圈的大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