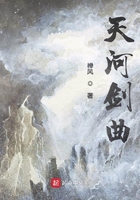话说二滚、铁锤指着秦耀先一齐问老白鹤:“鹤子叔,他这是咋了?”老白鹤瞅秦耀先:“他投机倒把还不老实,我们正批斗他呢!”二滚眼珠一转,将满面好奇的铁锤一拽:“走,斗争他去。”铁锤毫不犹豫:“走!”潘大炮他们一起望他二人。二滚、铁锤跑进屋,站在秦耀先左右,一声不吭,不约而同踮脚扳住秦耀先的头,一下接一下使劲儿往下按:“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
生就老实本分,浑身铁骨铮铮,却受此奇耻大辱,秦耀先想号啕而哭,想据理力争,想仰天喊冤。但不知为什么,却没吱声,依旧像一尊矗立的雕塑。眼见已到正午,二滚、铁锤气喘吁吁停了手,秦耀先仍死不吭声。蒋家朝觉得基本达到了目的,便要了却这场“批斗”。放下手中记录的钢笔,瞅着记录叫秦耀先,秦耀先不答。蒋家朝也不在乎,仍瞅记录,不无得意:“根据领导和群众揭发,你不仅投机倒把证据确凿,而且借跟艳二嫂上街之机散布资本主义言论,说什么不给社员自留地不对。”为了让秦耀先信服,遂问艳二嫂:“是不是?”艳二嫂瞟一眼目不旁视、雕塑般站立的秦耀先,忍了一会儿,才低头怯怯答应:“是。”蒋家朝又问秦耀先:“你听见了吧?”秦耀先不理他。蒋家朝碰了钉子,强按愤恨:“你不答应没关系,现在我以四清工作队的名义宣布对你的处理决定。”
文欣背着书包一路蹦跳回到家里,却见莫香春坐在门口发愣,取下挎的书包,焦急地问她:“妈,咋不做饭?”莫香春一怔:“你爸还没回来呢!”文欣搁了书包:“爸干啥去了?”莫香春不假思索:“在艳二嫂家开会。”文欣一惊:“啊呀!只怕潘大炮他们又欺负他。”拔腿就要跑:“我去看看。”莫香春怕他惹是生非,倏地站起来拦住他:“你一个小孩,千万莫去,我这就去做饭。”
再说蒋家朝将笔记本刷刷翻了两页,瞅着上面早写好的字低沉念道:“鉴于秦耀先一大肆投机倒把,谋取不法利益,二散布资本主义言论,蛊惑人心,三引诱青年妇女,四清工作队及队委会研究决定,给其罚款一千元的处罚。”
秦耀先一震,像要说话,瞬间却又跟刚才一样,一声不吭。蒋家朝恰像看见他这一微妙神情,合上笔记本,不无嘲讽:“秦耀先,你可别说没钱啊!”秦耀先心想:“算你说到,你要命吧!”仍不吭声。蒋家朝将合好的笔记本一拍:“没钱不要紧,就以你家门前那三棵榆树相抵。”
“使不得,蒋同志。”秦耀先突然像被刀戳醒,连忙大叫。“你不是不说话吗?”蒋家朝不无得意,“这么说你有钱?”“不!”秦耀先坚如钢铁,“你即使把我碎尸万段,我也没钱。”蒋家朝不阴不阳:“那你还叫?以树相抵吗!”“不!”秦耀先像要他的命,“那树万不能动,若能动,我家祖祖辈辈经历了多少苦难,还能等到今天?”蒋家朝奇怪:“那为什么?”秦耀先满面焦急:“那树已过百年,我爹临终前对我千叮万嘱:任死,也不能用它们换钱。要代代下传,直到交给国家,我正思谋向县林业局申请保护呢!”“哼哼!”蒋家朝冷冷一笑,正要说话,潘大炮指着秦耀先叫他:“蒋同志,莫理他,他一肚子《三国演义》,又给你演缓兵之计呢!”“哼哼!”蒋家朝对满面焦急的秦耀先又冷冷一笑,“你当我是阿斗哇!”扭头叫潘大炮他们:“散会。”
二滚、铁锤见再无热闹,将秦耀先的头又使劲一按,才撅着屁股,一溜烟跑了。潘大炮他们也纷纷站起。秦耀先痴了也似,仍动也不动,瞅着蒋家朝。潘大炮呵斥他:“快滚!待天晴了我们去放树!”秦耀先忽到蒋家朝面前扑通一跪,声泪俱下:“蒋同志,罚款我认,我慢慢还,只求你千万莫动那树,我真要申请国家保护,不信,天晴你跟我一道进城。”蒋家朝又“哼哼”冷笑:“我知你擅长下跪。”潘大炮像狗听到主人唆使,上去将秦耀先一把拽起:“滚!快滚!少在这儿给我卖可怜!”直把他搡到门外。
秦耀先顶风冒雨,踉跄走了。屋里的气氛仍然凝重。老白鹤肚子早饿了,想回家吃饭,问沉默的蒋家朝:“蒋同志,我们可以走了吧?”蒋家朝还没回答,跟他一样坐的仇仁海却说声:“慢!”冷冷叫他:“坐下,还有商议呢。”老白鹤他们只好又坐下,朝他投去疑惑的目光。仇仁海对蒋家朝一脸阴沉:“那树只怕不能等到天晴。”蒋家朝正要问他缘由,已悟出其中奥妙的老白鹤抢着大叫:“对对,不能等到天晴,免得秦耀先真进城找县上。”
所有人都望蒋家朝,蒋家朝愣了,将笔记本一合,指潘大炮:“你安排人,明天上午就锯树。”“好!”潘大炮顿时来了兴致,探头叫艳二嫂:“做饭去,今天中午我们就在你家吃饭,队里开支。”“好。”艳二嫂起身去了。“呵!”蒋家朝伸着懒腰打哈欠,问仇仁海:“怪累的,打会儿扑克吧?”仇仁海像不情愿,头朝旁边一扭:“那咋不行?”
秦耀先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满是泥泞的村前大路,走过一字儿排开,正炊烟徐徐的一户户人家,来到自家门前的大路上,面对路南宅基地上正嫩芽初上,躯干挺立,枝条摇曳的三棵榆树,不觉失魂落魄,趟着泥泞来到树下,竟初次看到似的,见那三棵榆树像孪生兄弟,均高约数丈,粗满一抱,间距几尺。不知是长在风水宝地,还是秦家世代悉心养育,虽逾百年,却仍树干挺拔,树皮浅薄,枝叶旺盛,毫无龙钟老态,既像正值壮年的热血男儿,又像功成名就的高雅绅士:伟岸挺拔,风流倜傥。日夜守护着秦家,守护着秦庄,为秦家祖辈炫耀,为秦庄世代美谈。秦耀先不由陡生感慨:“怪不得但凡上了年岁的每每谈及此树,无不啧啧而叹,民国二十四年发大水,我们村不淹,怕就是秦家那三棵祖传榆树庇佑呢!”
可是,有谁知道,这三棵古树传到今天,秦家祖辈付出了多少血汗,经历了多少磨难?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刀光剑影、明争暗抢。但秦家不畏强暴,披肝沥胆,护着三棵榆树闯过世代艰难险阻,饱受百年凄风苦雨,方才传到今天他秦耀先手下。
秦耀先望着想着,想着望着,眼前现出世代祖先为护三棵老树而苦苦抗争的百般情景,耳边却响起蒋家朝刚才的决定。不觉天旋地转,潸然泪下,蹒跚上前,将三棵榆树依次摸了,到最后一棵,竟两臂一张,身体紧贴跟他一样正淌着痛心而绝望的泪水——雨水的树干,眼前又恍惚现出昏暗的油灯下、冰冷的床板上,身体仅搭一床破棉絮的临终的父亲,干涸的两眼呆滞地望着他:“儿呀!那三棵榆树可是祖辈留下的啊!啥时再难可都不得拿它们换钱……”
“喳喳!”头顶骤然一阵幼稚的鸟叫打断了秦耀先的思绪。泪眼朦胧的他抬头一望,原来是终年垒窝于树丫的两只喜鹊为它们嗷嗷待哺的一窝幼鹊顶风冒雨觅食归来。双双刚落窝口,一窝幼鹊便竞相探头窝外,叫个不停。秦耀先眼前顿时现出树倒窝毁,一窝幼鹊惨落泥水啁啾不止,两只大喜鹊头顶盘旋哀鸣不已的惨景。不禁两拳擂树,泪如泉涌。正难过时,忽听“他爸,他爸”的叫声,抹泪一望,原来是莫香春手扶门框叫他。
秦耀先只好强忍悲怆,蹒跚而回。见他满身泥水,神情忧郁,莫香春心疼,忙从厨房里端来热水问他:“回来了咋不进屋,跑到树下风吹雨淋?莫不是他们上午又欺负你了?”秦耀先再忍不住,定定瞅她,将上午的事尽都说了。“啪!”莫香春盆落水泼,流了一地。热泪盈眶,颤颤问他:“那咋办?”秦耀先轻轻摆头,无言以对,眯眼望门外傲然风雨的三棵榆树,愣了许久,忽小声咕叨:“决不能让祖传古树毁在我手里。”
雨天早黑,人们也省略了晴天晚饭后村前村后走走转转,或到邻家串门聊天的户外活动,早早吃了晚饭,钻进被窝暖和。村里村外,只有沙沙雨声或雨声不意夹带的冷冷狗吠。
家人早已入睡,柴平生却只身坐在桌前,就着昏黄灯光,怀着天气一样阴沉的心情写日记:
“×月×日,星期×,雨。
“连天阴雨下个不停,春天播种、豆麦生长又遭寒冷,应尽力发动群众清沟排渍,以免夏粮受到损失。”
“群众反映的潘、仇二人贪污、私分的问题,蒋同志查得毫无进展,我又对这次库存粮盘存、秦庄的库存粮短少产生怀疑……”
“咚咚!”柴平生写得正紧,门外忽响起敲门声。声音虽小,但在这寂静的风雨之夜听来却分外惊心。柴平生停笔,屏息静听。“咚咚!”那低微但却惊心的敲门声又起。“是谁恁晚敲门?”带着满腹疑虑,柴平生掌灯来到堂屋,把灯搁到桌上,到门后嘴凑着门缝小声问:“谁?”敲门的也明显把嘴凑近门缝:“柴书记,是我……”“哎哟!”未等外面说完,柴平生便小声惊叫,小心开门。一阵寒冷随风扑进,忙叫:“秦先生,快进屋里。”
秦耀先、柴平生前后进了柴平生写日记的屋里。柴平生搁下灯,捡起桌上的东西,指着靠墙的一只板凳叫秦耀先:“请坐。”秦耀先低头望自己浑身泥水,不好意思:“不!我还是站着的好。”柴平生知他意思,满面和蔼:“跟我还讲客气?”秦耀先想了,再不多说,扭头望身后板凳,愣怕损坏似的轻轻坐下。柴平生问:“咋恁晚找我?”“柴支书。”刚坐下的秦耀先悲痛一叫,便起身扑通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柴支书,请千万救我的树啊!”“快莫这样。”柴平生一惊,紧忙搀他,“起来说话。”
秦耀先说罢走了,柴平生回到桌前续写日记:
“四清运动其实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怎能随便给群众定性罚款,还要殃及百年古树?这是秦庄四清运动的‘灾害’,蒋同志偏离了运动方向。”
写罢,咋像心里堵着什么,伏案沉思,耳边又响起他刚才跟秦耀先的最后对话:“他们啥时锯树?”秦耀先:“天晴。”柴平生:“天晴?”秦耀先:“嗯!潘大炮亲口说的。”“不!”柴平生拍案而起,“那三棵古树不仅是你们秦家的,也是秦庄的,更是国家的,谁都无权破坏!”
“嘟嘟!”潘大炮逼命般的哨声、吆喝声淹没了昨日的邪恶,惹出新的风雨。哨声、吆喝声里,风雨依旧不紧不慢,扯天拽地,天地一色,朦胧阴沉,像要挤压在一起。
潘大炮一路吆喝来到秦耀先家门前:“老秦!”潘大炮朝门口走着大叫。“哎哎!”又坐在屋里床沿上抽闷烟的秦耀先惦着柴平生的“尽量跟他们拖延时间”的嘱咐,忙不迭答应着出来。“给你说啊!”潘大炮独眼大瞪,“今天上午锯树!”“啥?”秦耀先似晴天响了霹雳,刚才的殷勤烟消云散,“你们昨天不是说等天晴了吗?”潘大炮厉声说他:“这是工作队的决定,还容你过问?”秦耀先深陷的两眼不由望向风雨摇曳的古树,顿觉它们像三个沙场壮烈的勇士相继倒地毙命。心如刀绞,正要央求潘大炮,莫香春忽从厨房里气冲冲走到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