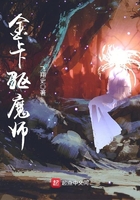50年前,长沙镖子岭。四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勾勾盯着地上的洛阳铲。
铲子里还带着刚从地下带出的土,奇怪的是,这一杯土正不停的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就像刚刚在鲜血里蘸过一样。
“这下子麻烦大喽”老烟头把他的旱烟在地上敲了敲“下面是个血尸嘎,弄不好我们这点儿当当,都要撂在下面欧。”
“下不下去喃?要得要不得,一句话,莫七里八里的!”独眼的小伙子说:“你说你个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就莫下去了,我和我弟两个下去,管他什么东西,直接给他来一梭子。”
老烟头不怒反笑,对边上的一个大胡子说:“你屋里二伢子海式撩天的,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翻盖子了,你得多教育教育,咱这买卖,不是有只匣子炮就能喔荷西天。”
那大胡子瞪了那年轻人一眼:“你崽子,怎么这么跟老太爷讲话,老太爷淘土的时候你她妈的还在你娘肚子里咧。”
“我咋说...说错了,老祖宗不说了嘛,那血尸就是个好东西,下面宝贝肯定不少,不下去,走嘎一炉锅汤。”
你他娘的还敢顶嘴!”大胡子举手就打,被老烟头用烟枪挡了回去。
“你这个当爹的也真是地,就知道打来打去,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地方咧,你自己做伢那时候不还是一样,这叫上粱不正下粱歪!”
那独眼的小伙子看他老爸被数落了,低下头偷笑,老烟头咳嗽了一声,又敲了那独眼的少年一记头棍“你笑个嘛?碰到血尸,可大可小,上次你二公就是在洛阳挖到这东西,结果现在还疯疯颠颠地,你个小伢子嘴巴上毛都没有,做事情这么毛里毛糙,嫌脑袋多是喽?”
“那到底是要得还是要不得嘛?”独眼的青年不耐烦的直挠头。
老烟头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看了看天,似乎笃定了主意,对大胡子说道:“那要还是要的地,等一下我先下去,你跟在我后面,二伢子你带个土耗子殿后,三伢子你就别下去了,四个人,想退都来不及退,你就拉着土耗子的尾巴,我们在里面一吆喝你就把东西拉出来。”
年纪最小的那少年不服气了:“我不依,你们偏心,我告诉我娘去!”
老烟头大笑:“你看你看,三伢子还怯不得子了,别闹,等一下给你摸把金刀刀。”
“我不要你摸,我自己会摸。”
那独眼老二就火了,一把揪住老三的耳朵:“你这杂家伙跟我寻事觅缝啰,招呼老子发宝气喃”
那年纪最小的少年平日挨过不少揍,看他二哥真火了,吓得不敢吭声,直望他爹求救,怎料他爹已经去收拾家伙了。他二哥得意了:“你何什咯样不带爱相啰,这次老头子也不帮你,你要再吆喝,我拧你个花麻*!”
老三吓了一跳,忙捂住自己的档部逃开。
这时候就听那大胡子大叫“你个二崽子罗嗦啥系?操家伙罗!”,说完一把旋风铲已经舞开了。
半个小时候后,盗洞已经打的见不到底了,除了老二不时上来透气,洞里的耳朵:“你这杂家伙跟我寻事觅缝啰,招呼老子发宝气喃”
那年纪最小的少年平日挨过不少揍,看他二哥真火了,吓得不敢吭声,直望他爹求救,怎料他爹已经去收拾家伙了。他二哥得意了:“你何什咯样不带爱相啰,这次老头子也不帮你,你要再吆喝,我拧你个花麻*!”
老三吓了一跳,忙捂住自己的档部逃开。
这时候就听那大胡子大叫“你个二崽子罗嗦啥系?操家伙罗!”,说完一把旋风铲已经舞开了。
半个小时候后,盗洞已经打的见不到底了,除了老二不时上来透气,洞里连声音都听不清楚了,老三等的不耐烦起来,就朝洞里大叫:“大爷爷,挖穿没有喃?”
隔了有好几秒,里面才传来一阵模糊的声音:“不知。。。道,你。。。呆在上面,拉好。。。好绳子!”
是他二哥的声音,然后听到他那老烟头咳嗽了一声:“轻点声。。。听!有动静!”
然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老三知道下面肯定有变故,吓的也不敢说话了,突然,他听到洞里发出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咯咯咯咯”的就像田里的蛤蟆叫。
然后他二哥在下面大吼了一声:三子,拉!”
他不敢怠慢,猛一登地拽住土耗子的尾巴就往外拉,刚拉了几下,突然绳子一紧,下面好象有什么东西咬住了,竟然有一股反力把绳子向盗洞里拉去。
老三根本没想过还会有这种情况,差点就被拉到洞里去,他急中生智,一下子把尾巴绑在自己腰上,然后全身向后倒去,后背几乎和地面成了30度角,这个是他在村里和别的男孩子拔河的时候用的招数,这样一来他的体重就全部吃在绳子上,就算是匹骡子,他也能顶一顶。
果然,这样一来他就和洞里的东西对持住了,双方都各自吃力,但是都拉不动分毫,僵持了有10几秒,就听到洞里一声盒子炮响,然后听到他爹大叫:“三伢子,快跑!!!!!!”
就觉的绳子一松,土耗子嗖一声从洞里弹了出来,好象上面还挂了什么东西!那时候老三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把接住土耗子扭头就跑!
他一口气跑出有两里多地,才敢停下来,掏出怀里的土耗子一看,吓的大叫,原来土耗子上什么都没勾,只勾着一只血淋淋的断手。
而且那手他还认得,分明是他二哥的。看样子他二哥就算不死也残废了。
这老三虽然被他二哥欺负的紧,但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很深,一想到这次可能真的出大事情了,脑子就一热,就想豁出去救他二哥和老爹,刚一回头,突然看见背后的芦苇丛里,蹲着个血红血红的东西,似乎正直钩钩看着他。
这老三也不是个二流货色,平日里跟着他老爹大浪淘沙,离奇的事情见过不少,知道这地底下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最重要的莫不是大惊小怪,而是随机应变,这什么黑凶百凶的,一梭子子弹打过去,打烂了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他收敛心神,也不后退,反而一步一步的向那东西靠去,一边匣子炮已经撰在手里。只要那血红的东西有什么动静,就先给他劈头来个暴雨梨花。
那血红的东西蹲在草丛里,毫无动静,老三走到三步内,仔细一看,顿觉得头皮发麻,胃里一阵翻腾,那分明是人!
他咬着下唇拔出腰间的长马刀,想去捅一下这东西,看看到底是什么,还没俯下身子,那怪物突然就一个弓身扑了过来,老三看到眼前红光一闪,再想避开已经晚了,电光火石之间,他双脚一滑,顺势向后一倒,同时匣子炮整一梭子子弹全部近距离打在了那东西胸膛上,那东西一下子被打的血花四溅,向后退了好几步摔进了草丛里。
这一边老三也顺势一滚,马上跳了起来,回手对准那东西的脑袋就一扣扳机。就听喀嚓一声,竟然卡壳了!
这老油匣子炮是当年他二爷爷从一个军阀墓里挖出来的,想来也没用了多少年月,可惜这几年跟着他爹爹到处跑,也没工夫保养,平时候开枪的机会也少之有少,枪管一发热就卡壳了,这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老三看着那血红的东西扭动也翻起身来,心里暗骂,刚才那股豁出去的劲道也没了,顺手就轮圆胳膊把枪给砸了过去,也不管砸没砸到,扭头就跑。
这次他连头也不敢回,看准前面一颗大树就奔了过去,寻思着怎么招它也不会爬树吧,先上树躲着去。
想着,突然他就脚下一绊,一个狗吃屎扑了出去,整张脸磕在一树墩上,顿时鼻子嘴巴里全是血。
这一下可真是摔的够戗,老三一下子觉得头昏脑涨,他咬着牙想站起来,却发现整只手都用不上力气,这时候后面风声响起,他回头一看,那怪物已经在几步之内,阎王爷来点名了!
老三也是个通透之人,看到自己死期将近,也不畏惧,只是苦笑了一声,索性就趴在地上等死。
刹那间,那怪物就扑到了他的背上,狠狠的一脚踩了下去,老三就觉得嗓子一甜,胆汁都被踩吐了出来。同时一阵奇痒从他的背上传来,他的眼前马上朦胧起来。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毒了,而且毒性还非常的猛烈,朦胧间,他看到不远处的地方,他二哥的断手从他怀里摔了出来,手里好象还捏着什么东西。
他用力眨了眨眼睛,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帛帕,老三心想,他家老二拼了命想盗出来的东西。
肯定不是寻常东西,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得把东西收好,万一我真的死了,他们找到我的尸体,也能从我身上找到着,那老二手也不算白断,我也不至于白死。
想着,他艰难把那帛帕死命从断手里挖出来,塞到自己袖子里。
这个时候他的耳朵也开始蜂鸣了,眼睛就像蒙了一层纱一样,手脚都开始凉起来,按他以往的经验,现在他裤裆里肯定大小便一大堆。
“中尸毒的人都死很难看,希望不要给隔壁村的二丫头看见。”
他混混着胡想,脑子开始不听他控制了,这个时候,他开始隐隐越越听到他在盗洞里听到的咯咯的怪声。
老三隐约觉得一丝不对,这声音怎么和刚才在盗洞听到的不一样…,可惜这个时候他已经根本无法思考了,他条件反射的想抬起头看一下,只看到一张巨大的怪脸,正附下身子看他。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里毫无生气。
50年后,河坊街西泠社,我的思绪被一个老头子打断了,我合上我爷爷的笔记,打量了一下对方。
“你这里收不收拓本?”他问我,样子古古怪怪的,似乎有什么特别的来意。
我并不在乎临时的生意,古玩市场大部分的交易都是私底下进行的,面上的也就是小打小闹,没多少钱赚,于是就敷衍他:“收,不过价钱收不高。”意思是,你没好东西就滚吧,别耽误大爷看书。
“哦,那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那家伙问道,一幅逛超市的样子。
我有点不耐烦,做我们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平日里清闲惯了,最讨厌伺候那些一知半解的客人,这古董的东西,每一件背后都有个故事,要真说起来,没有个把天还说不完,要每个客人都往这里来好我们介绍,我们生意都不用做了,不如直接开茶馆好了。
我刚要对他摆了摆手,说这里不负责介绍,隔壁还有很多家,请到隔壁去看看。
屋里又进来一个人:“小邪哥哥。”我一听面色一喜,喊我的小姑娘,是我妹妹叫吴雅。
几年前三叔因为某种原因,收养了他手下的女儿。
我听三叔和我说吴雅的父亲吴天,因为一次意外,为了救他而失去性命,临死前他把吴雅托付给三叔照顾。
三叔找到吴雅所住的地方和学校,老师却告诉三叔:“吴雅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来学校,已经报案了,因为吴雅不是本地人,也联系不上她父亲,这事就暂时放一边了。”
三叔立刻派人去找,最后在医院找到吴雅,听送吴雅到医院的人说,这孩子好像,下大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到,身体没有受多大伤,脑袋被摔到,一直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吴雅醒来,是半个月后,三叔离第一次见吴雅的时候,还是她二岁的时候,吴天带着吴雅给他拜年的时候,再次见到吴雅已经是十五岁。
吴雅因为脑袋受伤失去之前的记忆,三叔也没有说什么,就把她父亲为了救他而死的事情告诉吴雅,以后由他来照顾她。
等吴雅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三叔把吴雅带回杭州。吴雅四岁的时候,她母亲因病去世,唯一的父亲也因意外去世了。
三叔以收养吴雅的手续落户在他名下,吴雅小时候给三叔拜年的时候都是喊他三叔,三叔也没有让吴雅改口,还是继续喊他三叔。
我第一次见吴雅的时候,是我上大学放假回杭州,那时候三叔收养吴雅已经半年多,她也在杭州读高一。
家里人都知道吴雅的父亲因救三叔而死,她母亲也很早去世,尤其是奶奶很喜欢吴雅。
吴家三代单传就我这一个男孩,如今三叔又收养一个女孩,使奶奶非常高兴,我妈也高兴。
我突然多出个妹妹,那时候我在上大学,有关妹妹这个话题都是电话里听我妈说的。除了感觉到好奇,也没有什么。
等到我放假回家,在奶奶家里见到吴雅时,说实话,我觉得有个妹妹还不错。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带着这个妹妹在杭州大街小巷乱跑,家里人看我和这个妹妹关系越来越好,一家人都高兴。
时间过得飞快我大学毕业,在杭州开个古董铺,是三叔给我在杭楼外楼附近选的地方,店铺名字叫“西泠印社”,店铺里招个伙计叫王盟。
吴雅高中毕业,在家等着高考分下来,今天没事来店里找我玩。
我高兴的从座椅上起来笑着说:“雅儿,你今天有空来找我。”
雅儿看了一眼那个人说:“在家里无聊,三叔又不在家,我就来店里找小邪哥哥玩。”
然后拉拉我衣服小声的说:“小邪哥哥这个人是谁?买东西的吗?”
我这才看向那个人,他怎么还不走,那人有点尴尬的看着我和雅儿,却不出去,又问:“那我想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战国帛书的拓本?就是50年前,长沙那几个土夫子盗出来,又被一美国人骗走的那一篇?”
“你都说被美国人骗走了,那里还有。”我一听就火了“找拓本当然是去市场里淘,那有指定了一本去找的,怎么可能找的到?”
他压低了声音:“我听说你有门路,我是老痒介绍来的?”。
我心里想到怎么,难道把我供出来了?那眼前这家伙不会是个公安吧,我一下子有点慌起来。
对我身边的雅儿说:“雅儿,你去外面找王盟玩,哥哥这会忙,等忙完带你去楼外楼吃糖醋鱼。”
雅儿对我点点头,去外面找王盟,我听到王盟说:“小老板,来我教你扫雷。”
我看这眼前的这个人说话都结巴了:“哪。。。哪个老痒,我不认识。”
“我懂我懂,”他呵呵一笑,从怀里掏一只手表,给我“你看,老痒说你一看这个就明白了”。
那手表是老痒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他初恋情人送给他的,他把这表当命一样,喝醉了就拿出这表边看边“鹃啊,丽啊“的叫,我问他你老娘们到底叫什么,他想半天,竟然哭出来,说我他娘的给忘了。这老痒肯把这表给这个人,说明这人确实有些来头。
可我怎么打量这人都觉得面目可憎,不像什么正经人,但是老痒介绍的,还是要给点面子,况且是人家找上门来了,讲话都不让他讲完,可能会结下梁子。
我琢磨了一下,决定还是爽快点说话,于是直接一抬手:“这位爷,那就算是你老痒的朋友,找我什么事情?“
他露牙齿一笑,露出一颗大金牙:“我一个朋友在山西带回点东西,想你给我看看,那是不是真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