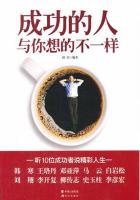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初隶属于广东省,海岛人民的饮食起居慢慢的和广东相接近。因广东经济的发达,两广地区海南都以老大哥广东为标杆发展自己的经济,广东的文化渗透辐射到周边地区。海南人民的称呼和问候语跟广东是一样的,上年纪的男人称“阿公”,上年纪的女人称“阿姨”更老的叫“阿婆”,当然一切男人均可叫“靓仔”,年轻女孩叫“靓女”可视长幼切换成“靓妹”“靓姐”。熟人就姓名中的名,最后一个字前加个“阿”字就好,男女通吃没人会说你错,礼貌而不逾矩。
语言也是神奇的存在,这些称呼无论用什么地方口音说出都还可以,当然用粤语“白话”说出来好听,各地方普通话说出也还各有特色。海南话和其它南方语言一样十里不同话,也如福建地区隔村不通言,更加晦涩难懂,完全没有口音语言文字联系,不光听不懂学不会,就连学舌也被指完全不地道,这种难只有教学的人知道,“小兄弟”教宿舍众逗比说吃饭“加魅”两字时,众逗比鹦鹉学舌了半天,“小兄弟”只是尖锐的说一句“这不是海南话”。众逗比看着“小兄弟”说“这不是海南话?”“不是”众逗比一哄而散,该干嘛干嘛去了,留下“小兄弟”一人,“小兄弟”认真的回想刚才说的每一句话,确定后说着“傻吧,逗比”。
同为福建人的黄毅和304室的林捷和陈金洪因地区不同完全听不懂各自的福建话。云南人柳和刘云、邹红洋可以听懂尹江和四川人钱可健、曹野曹顺平的方言,而四川人不大听得懂云南方言,鲁礼平赵德军的湖南话也是独立的存在。贵州人杨星、尹江的贵州话偏四川音。杨曾选、梁曙光的客家话,浓浓的梅州梅雨季节的淅沥沥的调性。
学院广东籍学生多,常常听到粤语和白话。柳的一位昆明女学长老乡英专的(英语专科),可以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可见当时广东在华南地区的重要性。
老窦这逗比无比喜欢和向荣讲白话,凡有机会就和“老七”逗个没完没了,丫的别人插不上话不说,问题是不知两广东佬在BB个什么,如果知道还可以反驳或喝断,反之则只有任由他俩自己聊死算完。但问题又来了,老窦是逗起来没完没了的,还不时意味深长的笑,这就是老窦的不对了,一直在床上啃书的白胖尹江在高床上必会狂吼“说个鸟语,烦不烦,滚”这就很那个了,你们懂的,就是很尬。广东人素质就是高,老窦从不和尹江计较,拉着向荣走开,恨眼继续粤语着,反正尹江听不懂。印象里向荣在四年间可能没和尹江讲话超过十句吧。白胖尹江怼所有人,包括怼自己。
学院里就流行或说病疫般传递着这个传统,这样如果想亲就来家乡话,自己和乡亲乐着亲着与旁人无关。虽然在同一个学院同个教室同个宿舍还是这样深切的体会着因地域人文语言的不同,让人与人之间终有抹不去的隔阂和无法消减的误解误读,无法填平的偏见和自负。四年后的园林90级的同学还是背着地区特性散落在某个世间的角落生根发芽,但地区性没有和解,就像对于外国我们是中国人,但对于四川自己却一定要说明自己是重庆人一样,这就是生下来就烙下的族腾永远不会磨灭,不会被稀释中和更不会被置换。这就是语言文化的归属感吧。
覃炜常在老窦和向荣聊的欢畅时加入他们,也说一口“白话”。还不了解情况时,柳一度认为覃炜是广东人,因为柳既听不懂广东话当然也听不懂广西广东话,在柳耳朵里它们都是“舌头没捋直”的白话。覃炜这屌真的真的太能装了,或许是误解太深,还是最初时被戏耍的太深痛,柳从不认为这是覃老大的能力,更不会认同这是才华。整个学院四年间广播里放的大多是粤语歌,尹江痛批一切粤语歌曲。柳却被洗脑了,高中时就喜欢听谭咏麟陈百强张国荣和梅艳芳等等香港歌手的歌,达明一派的《石头记》柳爱听的不行,常会卷着舌头唱。粤语歌柳是真心喜欢,音乐不应该再去区分言语。
语言真的有太多灵动和奇妙,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灵感和有趣。园林90级的同学四年中没有混号的一定要感谢父母取了个好名,让好事者无从下手。或是你一定去试着要改变自己了因为或许你已经是一个索然无味的人,没有可以取混号的借口和由头。丁板叫柳“小土”,而覃老大叫柳“BB”,覃老大很屌,这个混号取的更屌,叫“BB”的人不多,想来叫这混号的人也是很屌的一个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