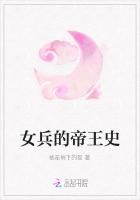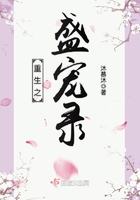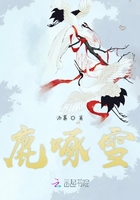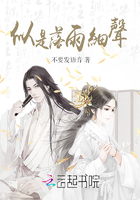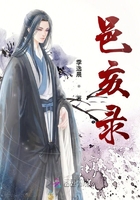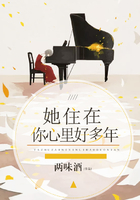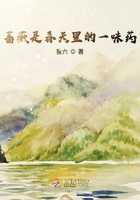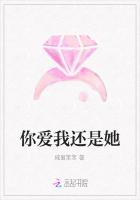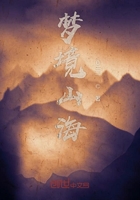他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却不知怎的,时间过得竟如此漫长。
自己将死于非命。
一阵突如其来的狂放不羁的笑声吓得他一激灵。
“哈哈哈哈……”
心中的好奇驱使他小心翼翼地睁开双眼。
面前,络腮胡夺了刀,还一边大笑着。一旁的刀疤脸甚是不服气。
众人不解。
络腮胡止了笑,一把将他从地上扯了起来。
“自我闯荡以来,从盗多年,见人识物之广,少有人及。贪财之人比比皆是,惜命之人数不胜数。我见其也如此慌张,便知纵识此礼节之人尚惧生死,况凡夫俗子。可其不卑不亢,宁持节而死,不弃义苟活,此举着令人钦佩。我不识文人之理,却也懂其言。本初意在羞辱,以灭文人之焰而助我辈之风,却不想为其所动,说来惭愧。”络腮胡向众人解释道。
“如此,莫再与他计较了。”络腮胡拍了拍刀疤脸。
“大哥说是,那便是。”刀疤脸强压着心中的不快,撇嘴道。
“我仰慕汝等气节,请愿结为兄弟,不知意下如何?”络腮胡仿着车夫方才的模样向他行了一礼。
“大哥,你糊涂了?”刀疤脸一把扯住络腮胡,诧异地喊道。
“此事与你无关。”络腮胡不予理睬。
他拍了拍衣袖,双手作揖道,
“我等非同路人,古语有云:‘道不同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先生好意,在下心领了。”
此话引来一番不满。
“我们老大好心与你结拜,你还胆敢拒绝!”
“臭文人装什么清高!”
“狂妄!”“不识抬举!”
……
他紧咬牙关,偏着头,一言不发。
络腮胡摆了摆手,众人随即安静下来。
“汝等讲真不愿听我一言?”
他摇头。
“也罢,你不愿与我等同流合污,自是文人高风亮节,待我与你放行。愿你不再与我等计较。”
说着,络腮胡又挥挥手,众人便让开一条道。
他再一次双手作揖,向络腮胡行了一礼,转身上了车。
“愿先生考取功名,造福一方。”络腮胡突然说道。
一阵惊愕过后,他用眼神向络腮胡示以肯定。
随着一阵阵马蹄声,络腮胡一众渐渐消失在路的尽头。
“方才也是有惊无险。”车夫感慨道。
他长出了一口气,整个人瘫软在草垛上。
“这道人我是初见。”
“初见?”
“我在此路来往数十年,不论是店面还是来往的路人,大抵脸熟,可此众着实面生。”
“也就是说他们方才来到此地?”
“此地以往也有不少匪徒,想必风水轮转,又换了批人。”
想来,这路上也非一帆风顺。即便在这太平之世,也免不了此等人事出现。
“若是以往,先生都如何处理?”
“散些钱财便是,权当破财免灾了。”车夫淡然一笑。
他摇了摇头,内心无限感慨。
……
“于此北上十五里,再向西行二十里路。”
他双手作揖,向车夫行了一礼。
“一路承蒙先生照顾,在此谢过。”
“哎,我等在此分别,日后可要多加小心。你等初出远门,背井离乡,路上皆有是非之人,万万不可轻信之。”
“先生也是,若是有缘,来日再见。”
车夫点了点头,一挥鞭,车尾扬起阵阵灰尘。不一会儿,车和车上的人影也消失不见了。
此行三十五里有余,须得加快步伐,方能在日落前赶到。
只是已值正午,烈日当头,行了短短几里,便已大汗淋漓,饥渴难耐。
移步树荫下,得以小憩片刻。
寻望四下,草木丛生,未见人烟,那便无处可匿。
他叹道,如此怕是计划有变。
只这一晃神,再定睛一望,恰巧不远处有一瓜田。
“此下里天气正热,不如买来几个瓜解渴,也好去去暑气。”他思索着。
远看瓜田葱绿,有灌木围绕;近看藤叶繁茂,有瓜数计,皆卧于垅上。田旁设一小棚,一老农侧卧其中,神色怡然。见有来者,便起身坐立。
“这位老先生。”
“你是……”老农对他上下打量。
“我乃赶考的书生,行路此地,尚觉饥渴,恰寻此瓜田,便前来寻些吃食。”他恭敬道。
“好说、好说。”老农点点头,笑道,“你在此等候片刻,我去寻一与你。”
老农缓缓走到田间,拾起一瓜放于耳边,轻拍数下,随后摇摇头,又拾起另一个。大约重复了四五次,老农这才满意地抱起瓜走了回来。
“此瓜正熟,肉脆而味甘,特意寻与你吃。”
他心生感激,连连道谢。
老农提刀开瓜,手起刀落,瓜应声而分。其内色泽红润,汁水四溢,瓜香弥漫,籽黑而粒大饱满,实属诱人。
面对这卖相十足的瓜,早因嗓中干涩而失了抵抗,这便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此一口,便知老农所言即真。此瓜果真香气浓郁,甘甜无比。只这般连连称赞。
老农在一旁笑道,
“凡食此瓜者,无不称赞。正值盛夏果熟,真乃祛暑解渴之宝也。”
他频频点头以示赞同。
“你此番是去往京城赶考?”老农问道。
“正是。”回答之余还不准口中作息,仍在埋头啃食西瓜。
“你可知此处是何地?”
“应是巴陵?”他稍加思索。
“古时此地乃巴陵,现改称岳阳。从此西北行二十余里,便得岳阳城。”
“我等信息闭塞,竟不知有此变故。”
“无碍,待你前往一探究竟便是。”
他点了点头。
“不远处有集会,待你食完此瓜,也可前往一探。”
“不知集会有何物?”
“我等口齿笨拙,无法与你一一道来,待你食完此瓜,于棚中歇息,避了这烈日,亲自前往查看,岂不更好?”
老农所言极是,不如听从计议,过了正午,再做打算。
……
日渐西落,他道别老农,稍作整顿便出发了。
应老农所言,步行片刻,果真人声喧闹。
观之有人,聚而围之,旁人不得入,只可远观。其内有竹杖伸出,约莫二丈有余,笔挺直立;竿上有数人,搔首弄姿(古义),莫有相同之势。
询问旁人可知,此乃百戏寻橦也。虽不得视,却闻之其下系一人手持长竿而立,数人缘竿上而戏之。
细细观之,竿下只一人,承长杆众人之势,稳如泰山,其臂不见青筋,应非蛮力持之;竿上数人,皆以耳解明月,头落金钿;红帽青衫,身轻足捷,绕竿四转,如履平地;倚附而落,上下蹁跹,翻身垂颈,住腰似歇;竿入青云,人不为惧,行舞随曲,袅袅如烟。
曲终而止,众人冥迷,殊不知皆已入其中。
待到此刻,如梦初醒,方知时间流逝,是以日落枝头也。
莫等下一出开场,这便匆忙赶路西行。
待越过城中,行至城西,已是弯月如勾,天色如墨了。
路上耽误太久,还是没能在日落前赶到。
他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你等是何许人也?已是月黑风高夜,为何留于此处?”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苍老的声音。
他回过身,一老者立于身后。
其身穿红袍,须眉尽白。
“我等是进京赶考的书生,路过此地,特想来城楼一探,却不想路上耽搁太多,误了时日,遂颇有遗憾。”他答道。
“如此,甚好。”老者点点头,“随我来。”
说完,老者朝城墙走去。
他喜出望外,连忙抬脚,随老者登上城墙。
“此城古时乃巴陵郡所置,晋时称‘巴陵城’,城头之上设一楼阁,唤作‘巴陵城楼’,后立岳阳城,此楼也更名‘岳阳楼’。”老者慢慢道。
随着台阶上升,楼阁的身形逐渐清晰,直至登上城楼,方才跃然眼前。
楼高十丈有余,廊柱雄立,飞檐如翼;盔顶月光相映,熠熠生辉。
“相传此楼古时乃东吴将军鲁肃阅兵之所,后文人迁客好其境,多来此地吟诗作赋,亦小有名声。楼头刻有‘一、虫、二’三字,字体秀丽俊美,然时月不详,已不可考究其源其意也。”
他仰头张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此夜已深,楼阁尚不能入,你且可远观之。”
虽不可近观,然睹其势,则仍为之所撼。
“只是不能入阁,便颇有遗憾。”他伫立于此,久久凝视。
“你可在此等候至天明,方可入阁一探。”老者提议。
“日程早已安排妥当,不应以今日未毕之事而误明日。我去往京城路途遥远,世事难料,难以捉摸,自然更应谨慎,提防变故才是。”
“所言在理,只是莫要气馁,虽不能上阁阅览一番,却也有极美之物,与之相比,难分伯仲。”老者安慰道。
“那是何物?”他顿时来了精神。
“莫要心急,随我来。”
他满心疑惑地跟随老者,走到城墙边。
一阵清风拂过,浩瀚的景象如画卷般展开。
“此乃,八百里洞庭也。”
【此章部分取自《寻橦歌》唐·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