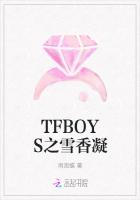北宋没有豪放派,南宋唯一的一个是他。
这当然是一个严酷的标准,而他样样符合——在任何一个时代,他都符合,哪怕每一个时代都在一个大标准上有着各自的微调。他硬是靠自己的操守和骨气,不用削足适履,穿得上各个时代的鞋子。鲁迅说过:“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他显然不是那样的东西,还正好相反。而如果还有一厘米的良知,在山河破碎时,知识人就做不到真正的“小径容我静,大地任人忙”。
插一句:回头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知识人,论操守和骨气,其实比两宋要差得多,更不要说比先秦之类。纵然操守骨气不缺,两宋又有几个格外豪放的?你要说东坡?唉,要认真论起来,东坡是旷达,哪里是豪放。豪放是铁,是钢,是秋风散关,不是“酹江月”。
他豪放了一辈子,将硝烟焦土当成了玫瑰花园去守持。
想来给孩子取名“弃疾”、“去病”的,大都是怕孩子羸弱不能长大的父母吧。可是,他们的孩子却都成为了豪放派大诗人或大将军,成为某一个或两个领域里的灯,光照千里——他又是豪放派大诗人,又是大将军;他是屈原、谢安、贾谊、马援、刘琨,更是廉颇、李广、祖逖、孙权和孔明——还在青少年时期,就曾带领五十骑直闯数万敌军的大营深帐中,刃如霜,马如龙,却金兵,封瀚海,取得叛徒张安国的首级而归。他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就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人,他(她)轻易地就获得了石头与月亮双重的品质。凭空想象一下他,就觉得他一定长得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嘴唇抿得紧紧,眉头中间有着刀子刻的思考纹,浩大的心事都堆在脸上,摆明了时刻心急如焚……如同一种高贵至极的树,一枝枝全往天上长,风来了,雨下了,雪落了,霜铺了,露掉了,雷劈了……但是,它也要坚韧不动。十年,百年,千年,也不开花,天长地久般绿了枯,枯了绿,怒发冲冠,斗志昂扬,不像个树。
它是不是记住了许多的事,跟杜工部的“诗史”一样?否则,如此倔强而不歇重复的躯干里留下那么多的年轮做什么呢?
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是宋词史上创作最多的作家,什么都可以纳入笔下三寸之地——就连骂儿子也可以写成词,而笔下的每一首词都埋藏着纷乱的深痛。《永遇乐》,《贺新郎》,《摸鱼儿》,都能从中看见一个倔强的影子,辗转在那个时代里,空有纵横天下的文韬武略,一身抱负却无法得以施展,最后在江湖风雨中渐渐两鬓斑白的那种言语无法表达的愤懑,报国的壮志就这样一点一点被蚕食,消失在山高水长的羁旅之中,只在中夜月明酸冷露寒的时候,轻抚着一泓秋水似的吴钩,踱步长叹,听着它发出不堪寂寞的的啸鸣。他说,“知我者,二三子”,无非指放翁、同甫和改之等有限的挚友,而除了放翁,其他两个都先后离世——就算人全的时候,他们相聚也很少,更多的岁月里他们只是遥遥致意。以前刚读到他写“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
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时年少无知,只觉得这拟人化的词写得好,拟人得好,生动,直白,笔调轻快,幽默洒脱。后来才觉出里面真是落寞到了极致——他恐怕笑的不是沙鸥而是自己吧。这笑中,又有多少心酸呢?只好“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了。“两三雁,也萧瑟。”“种花事业无人问,对花情味只天知。”“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哪一个字不痛着?
他的整个一生,时刻准备着出发,然而,最后只能原地踏步,任时间流去,一寸寸,老尽少年心。
看这一首少人提及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那些意思都有了: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饥鼠绕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蝙蝠翻灯,上下拍舞地作祟。他用这极不讨好的角色开篇,使情感的定位在乍读之下就无法快意——太晦涩,太阴暗,太诡异,太曲折,太孤寂。室内如此,室外还能怎样?松风起吹,急雨倾盆,破窗纸语,叫人百般酸甜入心,再不能入睡。
这首词在大诗歌的概念里是特异的。一首诗撇开意趣妙处不谈,撇开神笔丹心不论,首先要算得上诗,它就必须具备诗的基本特征,即意象存在的价值,至少也该有入诗的资本。中国的诗歌在唐代达到巅峰造极的境界,后代的人难以在此基础上再创辉煌。于是,文人们开始绞尽脑汁从侧道入手,为了追求诗的新异性,大大拓宽了诗的题材,我们最常见的诗歌有关于爱情的,思乡的,政治抒情的,爱国的,战争的,民生的,等等。从最早的《诗经》开始,就脱不开这些题材,且经典名篇无数。到了宋朝,一个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诗暂不论优劣,也定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可惜了宋朝,诗歌成了一抹暗色。我最不喜欢的江西诗派,在这个朝代大行其道,将诗颠覆成要么曲奥隐晦化,悖于常理,要么生糙口语化,美感全无。诗人们的视线开始从诗意美转向生存味。
这里说生存味而不说生活美有自己的理由。人的生存空间包括其内在的一切事物,无论美丑善恶,老弱病残,这些林林总总的总和,便构成了生活存在。生活美通常是与人有关的,与美相连着的,即使是悲伤,是绝望,它用诗的笔法去表达,加深的浓烈,也是一种悲剧美;撕碎的美,它依然属于美的范畴。后来出现的很多诗人推开了这层美,另辟他路,他们甚至热衷于描写苍蝇的生活习性,描写垃圾的难闻气味——这其实是不好的习惯,容易做作起来,有了邪气。然而在辛词这里,它们入诗而不讨厌,甚至添了一层别样的沉实厚重。越往下看,心越觉寒,最后竟有无力起身之感。反复读着,就突然被一种安静而森凉的情怀打动。好像即使在荒凉的夜,都能感受到千年前的那颗跳动的心。它的跳动近在眼前。
破败萧瑟如此,让人易忘老却的时光,只在寒凉中感受片甲的辛酸。然而他既给了我这样破败的残境,我便忍不住,跟随他的脚步,走进那个我们一定有所畏惧的世界。细碎的声音在昏魅的烛光中影影绰绰,一阵低沉的叹息声锁住了他望远的目光;压抑的呼吸,徘徊在无人的深夜,像唱失恋情歌的王子,狂歌悲风起。午夜最让人寂寞,所以夜里的歌声具有烫伤灵魂的力量,略带嘶哑的声音,越发震撼。
他在独处,独处中的人最易蔓生出孤独的无力感。寂寞和孤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生命体验:寂寞是世俗烟火的情绪感,是人皆有的源自于本能的感受;孤独则是超越一般情绪,升华为融于天地的深沉情感,它厚重到会让人感到齐天地、平日月的脱俗之境,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大境界。所以情歌唱得再好,还是寂寞,而此词一出,便倍感孤独。他的孤独,夹杂着被团揉成一小把的柔情万丈,在一片杂乱的声音中更显寂静。
忽而就懂了当年杜工部破碎又凝沉的哀伤——你看,我今天老是提到他,都只因为,他和他有太多相似之处,寥落干枯的风貌至今还刻在那个遥远的草堂。我想只有心地光明如雪而内藏深情的人,才会有不为一己之私的深痛。他们用疼痛成全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八百年也挡不住他出师未捷的疼痛。《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之》是他的伤口: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沙场,在书上是那么远的一个词。它是琵琶弦上拨着的徵音,是一挑过了年忘了摘下来的红灯笼,独自挂在屋檐下,晃啊晃……他以抗金复国为己任,聚义军,杀叛逆,策动万人,北伐,南下,几乎穷尽了一生——他从塞北开始走,走向沙场,却始终走不进沙场痛快杀敌;走向江南,却始终走不进江南进谏高宗,心血凝成、力主抗金的《十论》、《九议》被弃作废纸。四十年,没有一个可靠的位置来接纳他。
但他从来没想过做奴隶——那些选择做异国的奴隶的人,却不知道异国入侵者进城大部分是要屠城的,而女性多数是要被奸污的,男人选择做奴隶该是多么窝囊的选择!他不肯低头做奴隶。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在某些关键时刻,重大的选择应该源自一种最朴素的认识:正义。
在投降派把持的朝政中,他累遭政敌掣肘,不被起用,所以,当理想和现实发生尖锐矛盾时,他只有通过醉梦的形式表达自己杀敌报国的理想,真是应了其好友陆游的那句“报国欲死无战场”。整阕词里,前九句一气呵成,雄强无敌;最后一句却戛然而止,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否定了前面九句的理想——前面越是酣畅淋漓,后面越是悲剧重重。他把词语铺成一口深井,荒草掩盖,让人不备,一脚踏入。就像我为家人铺床许多年,没人再为我铺一次,今天早上,却梦到母亲为我铺床,暖暖软软,正幸福着,突然惊醒……这滋味,与稼轩同。不说了。
词中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有着无以言表的、茂长的精神力量美和崇高美——这个时代多么缺乏精神力量美和崇高美。
我们需要精神力量美和崇高美,就像我们已不再常去看月亮升起,而生活需要披一身的月色,如此,才能把故事静静展开。
李白有酒,杜牧有花,李商隐有梦……都可以暂避身形。与他们相比,他什么都没有,有的是和所有最普通的人一样,只是众多平凡里的一点虚弱的不凡,广大失望里一点飘忽的希望,如同身上一洗再洗的棉质衣物,觉得有了亲近,不可抛弃,而它们也忠实地跟随他,御风而行。
哪个朝代的哪个诗人不想归隐呢?他也是归隐的。那本应是他一生中最安静的时刻,累了的时候,他偶一为之,就手写下那些清甜小瓜似的词句叫每一笔速写都带给人无以言表的美好,譬如“晚云做造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譬如“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而他在田野上自由自在走来走去的样子仿佛伸手可及——他在那样的词里,活泼,愉快,仿佛只是一名在愁人的月光下醉酒的书生,坐着慢船去了一个并不在地图上存在的地方——一个桃花源,四面全是招展的树,很绿,一层一层,深的,浅的,掩映得一些低小的草房子仿佛有许多意味深长话语,闭口没说出来;许多不知名的鸟雀飞过,说着与人不相干的事。
那里当然仍旧存在着多么多的、每一样都有趣无比的农事,以及每一个古老朝代里失传的方言;没有吓唬人的刀兵和板着脸的政治,山坡上撒满一群被他驯养了的、无人认领的小羊似的汉字,充满喜悦和安闲。那是中国文人人人都做过的春秋大梦。
因此说,中国文人——或者说中国人——最幸福的状态,就是“谁要卿料理,山水有清音”这种完完全全置身世外的轻松。当一个人学着动辄将“天下”、“家国”这些沉重的名词拴在心间时,生命的过程就真的简单得如同一个普普通通的夏日黄昏,一不留神盹住,眯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许多看透了人生的人不都是这样吗?而很多时候,愈是挣扎,束缚愈紧,当绳索与血肉骨骼模糊在一起时,是否疼痛已不重要,麻木是最好的躲避场所。
在他心中,最心仪的诗人只有陶渊明。他爱陶渊明,但不愿做一个彻底的陶渊明——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看透过,盹住过,只不过,眯一会儿马上就会醒过来——他从未麻木,一颗诗人、将军的心该有的细腻敏感从来没缺席过。他对社稷的用情太深了,注定过不了没担当、只逍遥的生活,最强烈的想法是:打回北方去!为此,他生命的始终不曾真正有过一天安心安稳的日子,辜负了他多么恬淡的田园词。
就像他自己词里的戏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他几乎是不写诗的,因此,词就成了与他生命可以互相交缠悱恻的唯一温暖——虽然他是个一心盗取天火给人间的、燃烧着的普罗米修斯,但他自己是不温暖的。
所以,我们无法记住他走过的全部路程,却永远地记住了他一生的不温暖。虽然我不曾迎风饮酒,但是一点也不妨碍我在似是而非的睡眠中开出一间铺着夕光的酒馆,让时间在那一瞬穿越到遥远的某个时候,与“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的他,盐水花生黄酒青灯对坐,白发翁媪地,说一点热乎话。
[原作欣赏]
西江月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词人小传]
辛弃疾(1140-1207),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自号稼轩居士。南宋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现存词600多首,为流传至今词作最多的词人。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已被金人攻陷,祖父是爱国者,使得他从小就立志收复国土。还在弱冠之年,他就怀着满腔报国热情,抓叛匪,组义军,带兵南下追随朝廷,立下战功。然而由于现实原因,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一直到终老——时势对英雄的最无情,莫过于使其无所作为而终老。
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二安”。辛词在苏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其词题材之广阔无人能及。南宋后期,形成了以他的特色为标准的辛派诗人群。
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