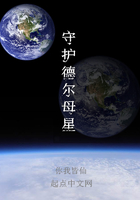生物有自己擅长的天赋。
鸟类会飞,鱼类会游,鬓狗很耐久。
是真的有耐力还有耐心,韩山凭双倍恢复力马不停蹄已经逃了近十四公里,六只鬓狗就足足追了十四公里。
途中韩山设计带它们闯进了一只烈火猿的地盘。
那猿猴实化内气能从嘴里喷出火焰,很凶悍,而且领地意识极强。
韩山此举算得上以毒攻毒,增添混乱寻找出路的法子。
烈火猿拍着胸脯长啸一声,错过韩山,挥动粗壮手臂径直扑向鬓狗。
“或许是因为我在树上,把我当成了只猴?”
没时间看狗咬猴,韩山一喜脚底抹油的同时饶有兴致猜了猜烈火猿没攻击自己的原因。
小艾:“亲,只是因为你看起来没鬓狗威胁大而已。”
没料到刚跑不远又追上来五只鬓狗,它们竟是留下一只拖住烈火猿。
落单那只是必死了,六只鬓狗打这三段高阶的烈火猿都够呛。
“尼玛什么深仇大恨啊。”韩山哭丧着脸,狗东西们抛弃一个同伴也要追杀过来。
树林愈加变得稀松,快跑到海边了,东边是开阳星最大的洋临丁洋。树与树间距越来越大,跑路难度从噩梦恶化到地狱难度。
脚下一个打滑没踩住,韩山险些坠下树,他甚至感受到鬓狗因兴奋加粗的呼吸。
须臾间,他在空中翻了个身,两只脚钩住树干,奋力把上半身甩到树冠里,这才脱离危险。
韩山敢发誓这是他经历过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一阵后怕,冷汗浸湿冬衣。
“跳到那座山丘上。”小艾开腔道。
前方是一座四米多高的山丘,韩山试探着踩在一根稍粗的枝桠上。
山丘长满了草,从树枝离得不远,跳上去倒是不难。
只是跳上去就没法快速上任何一棵树树,六只豺可在下边盯着,不会上树它们上个土坡还不是轻轻松松。
韩山越看那小山丘越像准备好的坟,坟头还提前长着草。
“你确定?”
“亲,小艾不会坑你呢。”
是吗......韩山翻个白眼,觉得某个知情不报害自己仓惶逃跑的人工智能没资格说这话。
“这是锻炼你呢。”
韩山:“......”七只鬓狗,奶奶的会死人的!
还有,老子的东西都没了!
睡袋,水壶,背包,各种工具都没了,值好多钱呢,好肉疼。
吸了口气,起跳。
一脚踩了个空,失重的感觉爬满全身,心脏捏紧。跳到的地方竟有个坑洞,隐藏在草中,就算凑近了细看都不会发觉。
洞口土沙松滑,韩山不得已掉了下去,人全部没入坑洞尚才稳住身形。
紧随着钻进一只鬓狗,韩山持剑狠狠捅了一下。
“嗷!”
似是戳中了菊花这般要害。
它发出尖利惨叫,连滚带爬跑了。
这洞口斜着有近六十度,通道不大,仅能容许一只鬓狗进出,倒是易守难攻。
应该是也意识到这点,它们把守在洞外,韩山听着零碎脚步,确定豺群没有离去。
鬓狗群有忌惮,韩山目前也处于窘境。
狭窄通道易守难攻不假,只是把退路给堵死了,出去就得同时面对六只恶豺,他现在几乎弹尽粮绝,跑如此远路早饿得前胸贴后背。
坐以待毙不是韩山的风格,思忖下决定向前爬。
不知通道是如何形成,可能爬着爬着就会见到一只蛇,或者一只大土拨鼠,但总比出洞送死强。
灰头土脸约爬行十分钟,眼前豁然开朗。
通道尽头别有洞天。
入眼约摸三丈见宽的溶洞,钟乳石一块块簇在石壁,洞内氤氲着朦胧光辉。
如梦似幻。
韩山挺直了腰,内心一阵悸动。
有种仿若血脉相连的亲切感,不自禁地就迈步子到深处。
蒙着让人看不清的那层不知是水汽还是何物,韩山只觉得似泡在浴缸里,毛孔舒张,和炼化精华时的舒适一般无二。
“能量都凝聚成液态了。”小艾说,印证了他的猜想。
眼前出现了一柄剑。
一柄黑剑。
剑锷高古,长约三尺,通体乌黑却散发出一种优雅。
剑格剑身游走着同种花纹,形如长蛇,下有四脚。
“这是蟠螭纹。”小艾罕见的透露几分惊讶出来。
蟠螭是无角之龙,她已经了解过这世界的古往今来,在这里古时亦有龙之瑞兽传说,不过形象没有一种是剑上这般。
见到剑的第一眼,韩山刹时变了脸色,讶然的脸上旋即有一股抹不开的回忆与悲伤。这剑他知道,而且很熟悉。
剑名崇阿,是他爷爷的剑。
......
韩山的爷爷叫韩秋明。
记忆里他是一个猎人,一个普通的散户猎人。那时候住在宁城边郊,韩秋明爱喝小酒,酒后就拉着小韩山聊天,说他年轻时候是车神,说他是武道大高手。
有时会说他有一柄好剑,一柄绝世好剑。
这时奶奶会假装生气:“又吹牛”,给爷爷端来米汤醒酒。
韩山为什么执着于剑?
很大程度受了韩秋明的耳濡目染。
韩秋明和韩山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说“剑乃君子之器”,可以说韩山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奠基是韩秋明造的。
崇阿是韩秋明的爱剑,韩山很喜欢这柄剑,因为它很美,因为它是爷爷的剑,因为“崇阿”就是山。
韩秋明从城外打猎归来,崇阿就成了小韩山的佩剑,他拿着剑在小路肆意挥舞,追赶蚊虫,顽劣了就砍砍野草野花。
“我孙韩山,有大帝之姿!”韩秋明笑眯眯看孙子玩耍。
“爷爷,大帝是什么,是皇帝吗?”
“不,大帝就是最厉害的人。”
“爷爷,我想和你学剑。”小韩山郑重其事说过很多次。
韩秋明听了就会正色告诉孙子:“时候未到,剑有双刃,一面攻击一面是守护。等你长大懂了责任的真谛,才真正配得上一柄剑。”他把剑看得很重,当作伙伴。
十岁那年是韩山最悲伤的时光。
也是宁城近五十年最黑暗的时光。那年,兽潮冲击宁城边境,长达五百公里的城市边际线边防军疲于应对,海城与江城的支援尚未抵达。
危在旦夕。
倘若电网被破坏,大批凶兽涌入,宁城损失会无法以金钱衡量。有识之士号召居民们自发奔向前线,第一批响应的是活在边郊的猎人。
新历95年11月20日,韩秋明与猎人们集会结束回到家中。
“我不去,又没人强逼着。”气氛凝重的家里,韩秋明突然笑了。
奶奶没笑,流了两行清泪。
第二天开始,韩山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爷爷。
后来他才明白,韩秋明回来是来告别的。
猎人是刀剑跳舞的高危职业,失踪或死在野外的不计其数,理应更明白与野兽搏斗的危险,知道生命的可贵。还小的韩山以为爷爷真的不会去,放心安稳地睡了。
岂知一别就是永远。
“爷爷......你还没教我练剑......还没有陪我长大。”
那年,韩山哭着鼻子咬着牙,开始学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