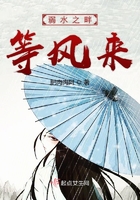午前事毕,连日来为着乔妃生辰的事,六局一司各院之中都是手忙脚乱,如今大事完毕,方才姑姑遣人往司乐司送了录事簿子,训过了话,众人都散了。姑姑走后,其他姑娘们都三五成群的往膳堂去用饭,因为姑姑嘱咐了午后停练半日,这会子,教坊也没剩什么人了,只几个洒扫的粗使丫头做着活。
“怎的去了这么久?”教坊外,二门上,这时候正站着一个女孩儿,一身儿新荷色宫装被风吹着,微微翻起衣角,如意髻上挽一支素银簪子,细瞧去,这女孩儿面目生的实在极好,这时候虽有些焦急神色,仍难掩其轻灵水秀。柳眉狭长,凤眼含波,映着晌午的日头,有些俏皮,更显秀致端淑,这时候,正颦着眉,一瞬不瞬的盯着巷子口。
“淑儿。”这一声却是身后传来的。
杨淑忙回头去看,是个一身儿碧色舞裙的妙人,身似蒲柳,道不尽是风流韵致,却不显妖媚。两弯月眉似是藏了许多心事在里头,端看那双杏眼,却又是温柔无限,直教人深陷在里头。双眉一颦,只作西施再世,浅浅一笑,梨涡含雪,连天光也黯淡几分。无怪乎惹得多少人瞧了她只一眼,便又是残恨,又是嫉妒,又是羡慕,又免不得有些个爱怜,这么个人偏是个任人欺压的软弱性子,除了她于沁心,这太极宫只怕再找不出这样一个温和敦厚的女儿来。
“叫你好等,那头徐掌乐新上任,总没个头绪,这才耽搁了许久。”沁心一面说,一面招手叫丫头们别锁门:“我去换了衣裳就来。”
“你快着些,”杨淑一面嘱咐,一面早又耐不住了,一跺脚,往里头来:“再晚只怕膳堂要上钥了。”说着亲递了衣裳鞋子来,瞧着她换衣裳的当口儿,自己先给她卸妆脱簪。
“这下可好了,今日定要好好歇息一番。”用了饭回到清安院,淑儿甩了外衫,直直跌进床上的软被里头。沁心倒好了一盏茶递过来:“先别急着睡,喝盏消食茶,坐着说会子话,不然晚间又该吵着不受用了。”
“姐姐,你这样细心体贴的一个人,将来可该找个怎样的夫家才好?”杨淑趴着,翘着脚接过茶喝了,眨巴着眼睛,好整以暇的看着沁心。
“你呀,又拿我打趣。”沁心伸指头戳了下她,一霎便红了脸,又怅然瞧着外头不知某处:“哪里想到那样远呢,我只要当好差事,别出什么差错,只盼着到了年限能给放出去了,旁的,再打算吧。”
“也是,你只管熬完了这些年也就完了,出去了,多少有了些体面,也能一家子亲热一回,”杨淑端坐起来,往桌子上放了杯子,就近坐下:“我又该怎么打算呢,照说,门上也算很体面的,只是大伯府上,我是再不想回去的。”
“若这么着,倒当真是件难事了。”沁心叹一声,瞧见杨淑眉头深锁,满怀愁绪的绞着丝帕,略想一回,方笑说:“淑儿,等出了宫,带你去我故乡如何?”
“姐姐故乡?”
“嗯,如今我家中只剩了我母亲和兄弟,你若去,他们必定欢喜,”沁心一面说,细细瞧着,见杨淑有些兴味,又说:“你若愿意,我去说和,叫娘认你做女儿,你也不必再回去那狼窝,岂不好?”
“姐姐若认真,我再欢喜不过!”杨淑顿时来了兴味,一翻身儿下了床。
“只是日子清苦,与府上不可同日而语。”
“能有多苦?我在那府上,连下人尚且不如,姐姐岂有不知的?”杨淑说着,又想起当日的境遇,不免黯了颜色,沁心也不知如何劝解,只对坐着叹气。
这头正说这话,只听外头只听外头砰一声:“这茶是谁拿来的!作死呢!”
“听听,她又在闹了。”沁心叹一声,倚着桌子,直揉太阳穴。
“这江兰心也太过了,总这么着。”杨淑往外头瞧去,只见,江兰心倚着门,抱着手,立着一双眉毛责骂洒扫的小孩子。:“她只管骂她的,咱们不去搭理她也就是了。”
“你们这些个瞎了眼的,没见过些好东西,爪子又不干净,比猫儿狗儿还不如些,待我明日找了姑母,再撵你!”江兰心只管指着那小孩子骂,日头斜斜地落在她衣裙上,像染了血一般。院子里早围了一帮人,也有看热闹的,也有暗暗为小孩子抱不平的,只是谁都不做声。
“好姐姐,消消气罢,她们是什么啊物儿?哪里值得姐姐你生气。”
这说话的是一向奉承着江兰心的苏子意,这会儿捧着一盏茶,堆了些不咸不淡的笑劝解着。
“姑娘的东西我并不敢动,我不过是管洒扫的,把屋子里院子里收拾个干净,旁的不多说也不多做。姑娘就是丢了什么,原不该责备我,不说这茶该不该姑娘喝,就是谁烹了茶送到姑娘屋子里,姑娘怪怨她也使得,只是这人不是我,姑娘也不犯那我扎筏子撒气。”这丫头若不是太不经事,倒也算个厉害的了,满院子里,哪有几个敢对江兰心横眉竖目的?
“瞧瞧,照我说,姐姐就该掌她的嘴,也叫她知道你的厉害!叫旁人瞧着,只当咱们多好欺负似的!”赵绮君一壁说,一壁冲西厢房抛白眼。这院子的西边,只住了于沁心和杨淑两个,不是冲她们,又是冲谁?杨淑待要发作,多少忍下了,没得为这没要紧的添事端。
“你倒不如打杀了我,可吓着我了呢。”院子中间,丫头索性扔了扫帚,喘着粗气瞪着对面的三个夜叉星。
江兰心冷哼一声,咬着牙连说几个好:“绮君,你瞧瞧,人家给咱们下马威呢。”
“照我说,就该告诉了江大人,打她一顿,撵到西厢房伺候那俩个不要脸的货!”赵绮君说着就要动手,全不见这头杨淑夺门而出,几步到了赵绮君前头,扬手就是一个耳光,直打的对面的人有些愣怔,这头却是反手又来一个。
“可清醒了?”杨淑冷笑一声:“午后阳火晴足,少不得有些糊涂东西叫日头晃了眼,瞧不清自己,自视高贵,只当是这宫里的主子呢。”
“贱人,你敢打我?”那人现下回过神来,扬手要反击,早被杨淑拦下了,扬手又是一记耳光:“都是一样的人,张口闭口贱人贱人的,我可是听不惯。”
“够了!”江兰心摔了杯子,往前来:“你若是再敢放肆,仔细......”
“仔细什么?司乐大人?”杨淑低头抹一把鬓角,这人莫不是有呆症?前日为了一点子小事跑去找江司乐出头,才被骂了一回,这会子就忘干净了?
江兰心自然是想到这一节的,紫胀着面皮,却说不出一个字来,咬牙跺一跺脚:“走!还站在这里做什么?”
“你别得意!”赵绮君捂着脸,恶狠狠地转身,重重地关上了门。
“你叫什么名字?”杨淑转身儿问那小丫头。
“我叫陆染香。”
“倒是个好名字,”杨淑上下打量这丫头,圆圆的脸儿,通身儿是石青色的宫装,趿着胭脂色绣鞋,挽个双丫髻,四色的绒线结了绦子垂在肩头。眼睛眨一眨,是说不清的轻灵英气,活泼俏皮:“往后就洒扫这边吧,虽苦了些,但我和于姐姐最不肯欺负人。”
“丫头,你就听她的吧。”沁心往这边站站,背对着正堂,朝那边努努嘴道:“你如今叫她没了脸,她那样的人,是决不能善罢甘休的。如今这院子里,多是奉承她的,若不然就是袖手旁观的,也就只有淑儿还能护你一二。”
“如此,”染香说着拜一拜:“多谢谢姐姐襄助。”
“不必,”杨淑扶她起身:“都是一样的,本就该这么着。”
次日起,染香被遣去洒扫西边厢房,不在话下。
且说这一日午后歇了晌,教坊众人皆不当值,或在园子里,或悄悄往后头去寻出宫采办的宫人,叫把自己攒的银钱往外头悄悄地采买各色货物。
未初,杨淑刚煎了驱寒化湿的药,伺候沁心服下,就有人来传话,叫司乐司的众人申正时往教坊,周司乐有话吩咐。
“姐姐,”杨淑洗过了药碗,进来说:“趁着时候还早,略打个盹儿,化化药。”
沁心点点头,往床上去歇着了。
要说于沁心这病症,实在与杨淑有些干系。还是杨淑刚进宫那年,当值时候没留神,把曲谱的架子扳倒了,被典乐大人处罚,大阴天里,叫跪在墙角地下。彼时因为清安院里头,除了杨淑都是奉承江兰心的,也没谁为她求情。只一个于沁心,因为与江兰心一样,是专攻古筝的,又比江兰心弹得好,早受了排挤,又实在喜欢杨淑的性子,便为她求个情,不想典乐大人迁怒,益发叫于沁心也并头跪着。偏生傍晚时候下了几滴薄雨,杨淑倒不见怎么样,于沁心却受了寒气,回来之后忙去找了太医院的吏目来瞧,虽开了方子,吃着药也渐好,只是她们二人原是住在西厢房的,墙背后就是一片树林子,树林子后头又有湖,因而这屋子是冬冷夏热得很,沁心的病,终究未痊愈,剩了半分病根儿在里头,每至立秋前后,总要吃一月的药才算完。
原说申正,众人都往教坊去。却见四位司乐大人都在里头正堂主位里坐着,两旁是四位典乐大人站着伺候,掌级则在门外廊下站着听吩咐。院子里这时候已经乌央乌央地站满了人,却是一点动静不闻。却说是为半个月后顾将军班师回朝和宫里惠妃娘娘生辰庆贺的大宴遴选演奏的宫人乐伎。
这实在是好机会若是能在这样场合崭露头角,必能的厚赏!杨淑垂着头,想了一会子,住的地方,实在该换换了,若是能得个脸,往姑姑那里去说话也方便些,到底西厢房住了这么久,实在也腻了。这么想着,便暗自拿定了主意。又看看沁心,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知在想什么。
听完吩咐回来,往膳堂用了饭,沁心说上一会拿的药到今儿刚好吃完了,这会不妨顺道儿往药局去瞧瞧病,再拿些药回来。杨淑原是要与她一道去的,沁心却拦下了:“你这会子不如先回去了,把地龙拢上,再把床铺铺好了,也不必回去时候还只是寒津津的。”
杨淑听了只得回来,收拾妥当,又卸了妆,换了衣裳,搬个凳子,就着廊下坐着,打眼一瞧,正房西间儿里头不知江兰心同苏子意和赵绮君说着什么,时不时听见极尖利刺耳的笑声传出来,满院子都听见。这里正想的出神,就见江兰心挑起帘子来,倚在门框子上,冷冷的瞧着这边,也不知在想什么,只一瞬不和孙地盯着,杨淑拿眼回她,她却打个激灵,冷哼一声,转身儿回去了。
天将黑时候,天突然阴了,闷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这夏末里头,一场风雷是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