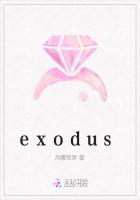●文/邵宝健
后来,甄之闲和树芳成了伉俪。婚后的生活,很和谐,很甜蜜。
甄之闲的老宅后院里,有一棵碗口粗的樟树。这棵树有灵性,只要他把手掌合在树干上,树梢的枝叶就会摇曳。这是他在无意中得到的体验,他从不把这秘密示人。他曾试过,是不是这种树类都有这个功能。实践的结果是:除了他家的树,别的同类树都没有如此神奇的反应。他百思不得其解。
时光倒流30年。甄之闲在读小学二年级时,有天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一棵尺许高的小树,树身还有擦伤。是别人无意中把它扔在这里,还是园林管理处的卡车掉落下来的,就不清楚了。反正他把这棵小树带回家,小心翼翼地把它种在后院的墙脚下。不久,小树复活了,枝头发青,有新芽萌发,他开心极了,蹦啊,唱啊。以后的日子里,他对这棵树自然倍加呵护。可以这么说,他是和这棵小树一起长大的。
30年一晃,甄之闲已经是个中年男子了。后院的樟树也长得高高大大,树冠呈蘑菇状,漂亮极了。他在市图书馆当管理员,工作一向尽职。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婚恋一直不顺畅,谈了几个对象都未能成功,有一个对象几乎发展到可以发喜宴帖子的程度,谁料,第二天又黄了。父母双亡后,他就一个人在老宅生活。他除了潜心工作,惟一的安慰,就是这棵树。他时常把手掌合在树干上,树梢就会摇曳生响,似乎在向他聊说家常。由于后院这棵樟树的陪伴,他的单身生活才不至于太寂寞。
这些天,他的心情郁闷得很。因为老宅所处的地段,已被市政列入拆迁范围。按照相关规定,他可以分到同等面积的新宅。这当然是好事啦。问题在于那棵樟树怎样办?他的新宅虽说是底楼,却不再有后院,新宅所处的小区由于景观限制,也无法容纳这棵树。有个在园林管理处供职的老同学知道了甄之闲的苦恼,出了个主意,说:“我知道你和这棵树有感情,这样吧,我出面叫花木公司收购这棵树,他们会善待这棵树的,你也能得到一定的补偿。甄君,怎么样?”
“那就拜托了。”甄之闲前思后想,也只好接受这个方案。30年的一棵樟树,换来1万5千元钞票。他拿到这笔钱,看园林工人把树掘起运走时,默默地流泪。
搬了新居的甄之闲,人却没有往日的精神了。他仍在位于人民公园南侧的市图书馆上班,骑了一辆旧“永久”,必经公园路。来来往往,他脸上的神情总是淡淡漠漠的,看得出,他的心里,还没有脱离失去樟树的悲凉。
半年后,公园路拓宽了,路旁栽了一排排年轻的樟树。他在夜间路过此地,会情不自禁地把手掌合在树干上。当然,不会有哪棵树响应他的爱抚。有一次,他在公园路的拐弯口,看到一棵新移植的樟树,很像他孩提时种的那棵树。他用手掌试了一下,嘿,这棵樟树居然向他打起招呼,树梢摇曳,哗哗作响。他兴奋得跳起来,眼眶也湿润了。这意外的发现,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他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多,人也变年轻了。
这个夏季,甄之闲照常骑着车在公园路上缓行,上班、下班。路东侧的那片旧宅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要不了多久,一个现代化的商住楼群将在那里现身。工地上的打桩声吭吭不息,好几座高架铁吊塔在忙碌。
这天晌午,当他骑车路过这个地段时,工地那边的一座铁吊塔突然倒塌,那塔梢朝他的方向扑来。他心一愣:这么快就结束啦?!随即连车带人倒在地上。与此同时,“啪”的一声巨响,大铁臂压塌了围墙,压断了围墙外的樟树的大枝丫,携着树身一起压向甄之闲。称奇的是,他正好倒在铁臂和树身的空当里,只是左脚腕被崩出的铁片擦了一下,削掉了一小片皮肉。他下意识地将手掌合在树身上,此树的梢头居然摇曳起来。旁人目睹这惊险的一幕,都说,多亏这棵树的抵挡,否则他的命早没了。
他去医院作外科处理返回时,人行道上那棵樟树的断枝仍和暴露根系的树桩相连,似乎在等候他见上最后一面。他向城建部门提出一个要求:他不要什么伤害赔偿金,只要这棵救他命的樟树的树桩和一根枝丫。有关方面自然答应他的要求。
他用枝丫做了根拐杖,出门的时候就带着它。那个树桩,他把它做了一具根雕艺术品,陈列在客厅里。这个状大如电视机的根雕,似龙像凤,姿态万千,叹为观止。
有趣的是,有一天,一个小偷在甄之闲不在家的时候,入室偷盗。小偷得手后,正准备撤退时,被客厅里的树桩吓得瘫倒在地。这个树桩居然像巨蜇一样,活动起来,坚硬的触须抓破了小偷的脸。甄之闲回家后,把无还手之力的小偷撵到附近的警署。
在甄之闲40岁生日的那天,婚介所给他物色了一位单身女性。两人一见面,都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位相貌清秀的女子在市档案局工作,没有婚史。她的名字叫树芳。
在湖畔茶室约会时,甄之闲问:“您名叫树芳,哪您姓什么?”
她莞尔一笑:“我姓树,名芳,单名。”
他也笑了,笑眼里匿着问:“树,有这样的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噢。”
树芳收起笑意,说:“我姓树,不错。甄先生,咱俩初次见面,我没有理由骗您。”
后来,甄之闲和树芳成了伉俪。婚后的生活,很和谐,很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