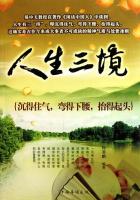1
说起来,姜家也不是根生在玉水的本地人。姜家在玉水住的房子是一所老宅,原是别人家住的,据说那家是富人,那个远方的矿也是他家的。房子是分了正房和偏房,或许还准备着再在院子里盖新房,所以院子格外地大,留了许多的空地,也不种树,院子里只有一棵老槐树,粗粗的,一个小孩藏到树后面也看不出来。大大的树冠,像一个房顶,老槐树被树冠压歪了身子,树下的荫凉多了一大片。树皮也很老,颜色深得都快成黑色了,冬天的时候,老槐树像要死了一样,到了春天,槐花把一个树冠都插满了,树变得年轻了,槐花的香飘得满院子都是,院子里盛不下了,就飘到大街上。院子的主人是有各种打算的,只是还没有等到他们再建新房子,就解放了,那些原有的房子就被分给了好多人家。筱芬家就是其中的一户,那时筱芬的父亲刚刚大学毕业,他在学校里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学生,政府接手了那座远方的矿,正需要真正的主人去掌管,父亲就带了母亲从外省来到了这里。
沿着滇缅公路一直走,过了一个坝子进到山里,又过了一个坝子进山,路是险到了尽头,人也坐车坐得够够的了,不晕车的也在翻着胃。汽车牛一样地爬到了山顶,忽然一股凉凉的小风迎面吹来,定睛一看,看到了山脚下的青绿,长方、正方的田野茂盛着黄的、绿的,在黄的、绿的正中,是一片浓浓的墨绿,墨绿掩映着一些房子,隐约有深灰色的瓦楞从墨绿中显出,这就到了玉水。
据说玉水所属的每一座大山的肚腹里都含有丰富的有色金属,因此,玉水被称为高原明珠。县城倒不是一个新城,老辈的人说老早就有玉水城了,老早倒不知道是早到什么时候了,当然玉水是有县志的,只是好多玉水人都没有看到。玉水是一个古城,是因为在玉水处处能够看到古的痕迹。从观音角那个十字路口延伸出四条街道,街沿的房子是有模有样的古典,房檐很夸张地飞翘着,瓦是青灰色的,现在是看不出青色了,就只剩了灰色,那些灰也不容易看见,被草覆盖了,还有一些花,主人从来没有在房顶上种过花草,花草是自己长出来的,长出了一定的规模,有一天主人有了兴趣,把那些花草清除了,再看那房子以为是别人家的了。房檐下的门脸没有了房檐的那一份福气,那些门脸规规矩矩地排列着,都用来做买卖。门脸规矩就规矩在那些木板上,木板是一块紧挨一块,严丝合缝,木板的排列是有严格要求的,于是,主人就在每一块木板上都做了标记,那是一些数字,或是黑或是红,都是粗大毛笔写成的,左一、左二……右一、右二……也有东一东二,北三北四这样排列着。到了白天,木板被主人卸了下来,放在一边。门脸里是一个个小铺子,家家都卖土杂,也有自己的特色,有卖甜酸角的,是这家的老人传下来的手艺,县城里的女孩也只是认了这一家,一分钱也能买到两粒,含在嘴里酸甜酸甜的味道能管大半天。也有卖米线的,家里有发酵、舂米、挤压等等的手艺,这样做出来的米线进了锅开三个开也照样有嚼头。
在门脸的旁边有一扇很窄的门,进了门穿过隧道一样的走廊,一抬头是另一番天地。这就进到了这家人的后院了,院子里种了树,是第一代人种下的,到了这一代人,树已经很茂密了,树冠挡了院子的半个天,不管是什么季节,墙脚下都生了一层阴阴的绿苔。冷不丁在一个房檐的瓦片上,还能看到一个久远的朝代镌刻下的文字。
街面是石块铺成的,大小也就一本书那样,有排列得很整齐的,也有歪的斜的。人走得多的地方,石块都磨平了,看不出是石块了,因为补上水泥了。东西走向的街面,有一条小河,也就两步那么宽,当地人叫它玉花江。玉花江的水又清又凉,居民出了门,弯下腰就能在水里洗洗淘淘,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城里的孩子在水里放了灯,幽幽的一团红就被水载着走远了。玉花江出了城就成了一条真正的江了,江面宽阔,水依然是清亮的,能看到水底的石头。在玉水城里的玉花江里放过灯的孩子,长大了都要到城外的江里去,那里的天地更大一些。
姜家夫妇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最大的是个女儿叫筱涵,第二个出生的是个男孩取名叫筱君,姜筱芬是最小的女儿,最大的女儿和最小的女儿整整差了九岁。三个孩子都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的。他们的父亲就好像是从这个院子里放出的一只风筝,他更多的日子是在远方的矿上,母亲就是长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棵树,她在这里养育孩子,并在她的房子里上班工作,她从街道上领回帆布来,裁剪出来,用缝纫机车好,做成手套,这些手套被送到矿上。这就是她的工作,她养了孩子,还依然像一个职业妇女一样,挣钱养家。
筱芬记事的时候已经看不出房子原来的样子了,几乎家家都在自己的房子旁边盖了偏厦。母亲回忆他们才搬进来的时候,院子是那么清静、幽雅,她说,听说院子的主人是留过洋的,自然是有一定品位的。母亲说,现在乱了,简直就是一个大杂院。也难怪,姜家的人口增加了,老冯家也由两口人变成了五口人,还有小兰家,老辈人没有了,又有了新人,院子自然是挤了。筱芬记事以后,母亲在休闲的时候就会跟她提起过去,像是过去的日子总是比现在的好一样。
筱芬小的时候院子还很大,比学校里的篮球场都大,院子的南面是大门,北面就是一些房子,西头住的是筱芬家,东头住的是老冯家,中间住了小兰家,就好像一个菜筐子没有放匀称,北面沉沉的,要把院子压翻似的。筱芬听大人说,这里原来住的资本家,其实就是小兰的爷爷。筱芬难以想象小兰家会是资本家,小兰的身上从来没有断过虱子,她总拣地上的东西吃,就连槐树上的毛毛虫都要抓了放嘴里嚼。筱芬从来不和小兰在一起玩,恶心。四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院子里是男孩多女孩少,筱芬还是不和小兰玩。姜家的两个女孩像金枝玉叶一样长着,和她们住的院子极不相称。
2
筱芬九岁的那一年,姐姐姜筱涵在剧团里出了事。姜筱涵当时正是州里剧团的台柱子,红得发紫,谁也没有想到十八岁的她未婚先孕,并且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刚刚出了满月,姜筱涵就远走他乡了。男孩留在了姜家。
筱涵走的时候,天上挂了一弯月亮,月光透过窗棂上那一层薄薄的纸,进了屋子月光也纸一样的薄了。筱芬看到了穿衣的姐姐,那只是一个影子,筱芬看不清姐姐的脸。姐姐像游戏里的剪纸,只是动着。后来姐姐拿起了放在床边那个头一天准备好了的提包,定定地站在了屋子的中间,筱芬慌忙紧紧地闭上自己的眼睛。再一睁开眼睛时,姐姐已经出了门。
院子里比起屋子里亮堂很多,月光厚了许多,霜一样地铺了一地。筱芬光着脚下了床,来到了窗户边,她把脸放到了最下面的一格窗棂上,目光追随着姐姐的身影。白惨惨的月光下走着的姐姐,像一个鬼。院子大得像一个篮球场,姐姐走得匆匆忙忙,就好像有人在后面追着。筱芬只是看着,一声不吭。
天亮后,筱芬见到了那个男孩,正在熟睡的男孩突然睁开了眼睛,筱芬吓了一跳,猛地往后退了一步,不曾想一脚踩在了一个铜盆上,原来那是给男孩把尿的屎尿盆。筱芬踩到了铜盆的一个边,盆翻了,盆底的一点尿倒了出来,尿被三合土水泥地吸了进去。踩翻盆的声音惊了床上的男孩,也惊了九岁的筱芬。男孩“哇”的一声,扯开了嗓门,那声音像挂在观音角的高音喇叭,筱芬夺门就跑。
筱芬还是和闻声进来的母亲撞了个满怀,母亲奔向床边,哎哟,造孽啊,造孽。越是怕别人听见,你越是嗓门大,我还能把你捂死了不成。说着抱起了男孩,转脸狠狠地瞪了一眼发愣的筱芬。
筱芬躲了母亲的目光,埋着头奔跑到院子里。早晨的凉风在她细嫩的脸上刮过,稀薄的阳光照在筱芬黄绒绒的头发上,筱芬感觉自己成了一片树叶。筱芬在一棵大槐树的后面停了下来,她用手抠粗壮树干上的树皮,她用食指和大拇指抠,用小指的指甲去挑,手指冷冰冰的疼,黑得没有了原来的颜色。筱芬的眼睛紧紧盯着树干,门牙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