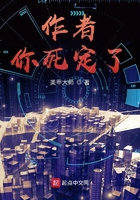“队长,你好像是将这小子的动脉血管给割断了!”那小弟惊声道。
“靠,这血怎么飙这么猛啊?这可咋办?我之前也没学过怎么止血啊!”
听那队长的声音显然有些着急。
二人又似乎在寒林身上琢磨着,只是他感觉不到究竟是在手腕处还是在肘腕处。
又沉默了小许后,那小弟道:“队长,我隐隐记得血液时代有个连通器原理,就是说两边的液体始终会保持一个高度!”
“既然这样,那我们可以把他另一个血管也割破,这样岂不就两边平衡了吗?说不定这血也就止住了!”
那队长一愣后,“嗯”了一声道:“有道理!还是你小子有点学识!”
此时,寒林真想跳起来给那小子一个大嘴巴子,特么学点东西哪儿都用。
况且还特么就学个知识名,这特么还不如“半路出家”的呢!
但你学就学了,别滥用行不行啊?
一个人虽然濒临死亡,但遇到气氛难当之事时难免也会清醒一些。
也许是过于激动的原因,但绝对不是回光返照。
寒林就是个例子!
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说不出话,甚至连呼吸都要停了。
终于,一切都静了!
……
也不知过了多久!
寒林隐隐感觉眼前有一道强光照射着他的眼睛,亮得有些刺眼!
这种光红通通的,甚至刺进了他的脑海中,让他很不爽。
他本来极舒服的睡姿此时竟无半点困意,甚至都不想在这种光下多坚持一秒。
他想睁开眼睛,但突然发现眼皮很沉重,以至于他费了很大劲才勉强将眼皮撑起。
当他缓缓睁开眼睛的一刹那,仿佛自己正直视着酷暑时的烈阳,刺得眼睛有些发疼。
他又不得不将眼睛合上,头也下意识地向侧偏了偏。
当他第二次睁开眼睛时,映入眼帘的是挂满琉璃般发光水晶珠的天花板。
他头有点痛,尤其是后脑勺。
脊椎也不舒服,浑身还乏力,即便是一双眼珠子来回游动都似乎耗尽了他全身的气力。
天花板很奇特。
一个个拳头大小发光的水晶珠在天花板上依次排开,很像是一个别致的图案,但寒林一时间并没有看出是什么图案。
也许是头疼,也许是他根本也没心思去观察。
寒林又转动着眼珠子,打量着眼前的陌生环境。
房间并不大,因为一张床已经占据了它大半的空间,即便这张床本身也不是很小。
正前方是一个石桌,应该是石桌,因为颜色很像。
石桌上放着一个地球仪般缓缓转动的发光晶球,是白光。
原来刺眼的强光便是由那里发出来的,只是当时寒林闭着眼,故而才觉得这光红通通的。
床是半弓式的,就像是医院的病床。
寒林躺着很舒服,只是他现在根本动不了,就像是骨头都散了架。
他很清楚自己确实是穿越了。
头很痛,但记忆并没有消失。
他很清晰地记得那个保安、那个马脸老头、那几个“智障”及那个和蔼的院长,当然还有那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副院长!
那些情景在他脑海中历历在目。
难道我真遇到高人了?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吱——”
寒林正兴奋之时,屋门被人推开了。
是一个修身俊朗的素衫青年,只是他的衣服很是奇怪,既不像道袍又不像长衫。
他脚步很轻,但走得很快。
也不知是屋子太小还是那青年的步伐太快,没两步便已走到床前。
这里的人的衣服为什么都如此奇怪啊?
寒林正这么想时,那青年便开口道:“我又何尝不是觉得你的衣服也奇怪呢?”
靠,这撞得就有点尴尬了!
只见那青年又道:“‘靠’好像是粗话吧?”
恩?
他莫非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可能吧?世间还有这么玄乎的事?
“我不仅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还知道你昨晚梦里都干了些什么,需不需要我也说出来啊?”那青年轻飘飘道。
寒林一惊,下意识道:“不不不,不需要!不需要!”
那青年微微一笑后朝着门外喊道:“小雷,你去叫一下教授,就说病人醒了!”
之后门外便传来一句应和之声。
那青年浮手摸了摸寒林的额头,缓缓道:“你还很虚弱,需要静养!”
“是你救了我?”寒林微弱的目光盯着青年问道。
那青年微微摇了摇头道:“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是我们教授救了你!”
“教授?”
“当时你气息很微弱,存活的可能性不大!也不知道我们教授用了什么方法,你竟然醒了!”
那青年边说着边缓步走到石桌前,在那地球仪般的发光晶球上摸了摸,那晶球瞬间又发出一阵阵墨绿色的微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萤火虫。
寒林有些好奇,但刚要开口时又被那青年打断道:“你体内没有精元,因此没法分解暗黑粒子来提供能量,它就是帮助你分解体内的暗黑粒子的!”
寒林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他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青年确实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暗黑粒子需要光?”寒林问道。
“只是你需要光而已!”那青年依旧是一副风轻云淡的口吻。
寒林听得很懵懂,但他并没有打算再问下去,因为他清楚一般带这种口吻的人嘴里是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
那青年一直把弄着那个晶球,似乎也没想着再解释下去。
少时,听得门外一阵轻轻的脚步声。
门里走进一长衫老人,一头白发清亮似雪,五缕长须无风自动。
颧骨高耸,眼窝微陷,一双深褐色的眼眸中似乎流露着岁月的沧桑。
脸上的皱纹丝丝隐显,又似乎讲述着其一波三折的陈年往事。
他的长衫依旧很奇特,既不像儒衫又不像长褂。
老人一进门,那青年便停下手中的“活”,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后立于一侧。
看样子,这老人定是那青年口中的教授了。
“感觉好些了吗?”那老人一走近床前便和声道。
“好多了!”
寒林也本想点头的,奈何他的头此时重如千斤,就如同粘在了枕头上一般。
“那就好!”
那老人点头笑了笑后便托起寒林的手臂开始为他把脉。
不时,那老人脸上的笑容浅了,淡了,甚至已经停了。
他的脸色逐渐沉了下来,就像是乌云遮住了晌午的艳阳。
良久后,他才缓缓道:“看来是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