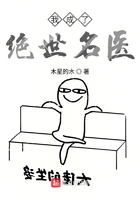维谷前几日一直沉浸在秋千单摆问题及空气阻力问题的庞杂算式中,今日猝然遭了这么多变节,他只觉身心俱疲,但也只能强自支撑。他已经是宗主,不能被肩上的担子压倒,宗主没有逃避的自由。
刚走进吕布将军府前院,就见花清夙、吕布和吕布的爱妻貂蝉三人纠缠在一起。
“我堂堂牧城将军,这点儿风寒算得了什么?别拦着我!”吕布低声训斥着貂蝉。
“夫君,那么多军士铁打的身子骨也熬不住这风寒的。你看宗主都快扛不住了,你不能再去城墙上受凉了!”貂蝉抱着吕布的腿,哭泣着说。
“吕将军,宗主嘱咐我务必要护你周全,你的身体不能有差池。你若有个闪失……”花清夙在一旁劝着。
“都给我闪开!”吕布一声大喝,挣脱了貂蝉的束缚。
“吕布将军,回房间修养吧!”维谷走到吕布身前,大声说。
“维谷你别管,你安心的和阿基米德弄秋千的方略,别的事儿你不用掺和。”吕布拍了拍维谷的肩膀说。
维谷伸出左手拇指,亮出了宗主指环。
吕布看见维谷手上的指环,一时间错愕了。
“吕将军,我知道,你觉得我配不上这个指环。但如今牧城危机,宗主病危托付给我,我没法推辞。我没什么资格命令你,但你是战神,你是青岚部落的信仰,是以你不能有闪失。”维谷声音并不高亢。
“正因为战士们看见我心里才踏实,我才必须让大家伙看见。”吕布的声音也很冷静。
“眼下军心不是最关键的,健康才是。”维谷说,“有了惊魂法网,夜魔一时间奈何不了我们。可若是几日之后,真的需要吕将军上阵了,你得拿出全胜的实力才行。”
吕布叹了口气。
“此次风寒,诡异得紧。吕将军,为了全牧城,我希望你能回房修养。你越早养好了,才能越早鼓舞军心。毕竟我听说,这次风寒,还尚无一人痊愈……”
维谷语气平淡,可他这话一出口,吕布热血激昂的心也彻底平复了。
“好!你也保重,你也不能垮掉!”吕布说着,又在维谷肩头用力握了握,转身抚了抚貂蝉的长发,便回房间休息了。
“花医师,我找你有事儿商量。”维谷说。
花清夙望着维谷,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笑:“那便进屋说吧,吕布将军府的议事堂总比这前院暖和些。”
吕府议事堂中,貂蝉为维谷和花清夙各倒了一碗茶,便回房间照看吕布去了。
这议事堂虽然暖和,但空气闷热,倒让维谷感觉喘息起来有些费力。
“造化弄人,没想到再见到你竟然是这般情景。”花清夙叹息说。
“我前几日一直闭关推演算术,对这风寒尚不知情。花医师,还请给我讲讲。”维谷皱眉说。
“哎……,此次风寒凶险得紧。似乎传染性强,发病也快。一旦发病便始终高烧不退,日子久了,人的体力便被熬枯了……”花清夙答。
“怎么会如此?那如何应对啊?”维谷问。
花清夙皱眉说:“最大的问题便是牧城之中药材稀缺紧俏。眼下我只能顾及上给你们守军的参将、先生、谋士用药,我和医馆中的学徒也要每日喝药预防被传染。学徒们只能四下奔走给尽量多的军士针灸降温。可僧多粥少,大部分战士和子民,就只能干熬了。”
“怎么能这样?”维谷惊呼。
“不然怎么样呢?即便是如此,眼下所剩余的药材也只够这几位参将和先生们服用两日了,再之后……,便要听天由命了!”花清夙叹息说。
“若如你这么说,那全城的人都要病死?没有别的法子了?”维谷问。
“有,隔离。”花清夙说,“你可知牧城城墙之上此时有一千军士已经连续五日五夜未曾换岗了,这其中也包括你们的参将白起、干城章嘉、法拉第、门捷列夫。”
“这?这怎么行?累也要累死了。在城墙上过夜,岂不是更要染风寒。”维谷皱眉问。
“怪就怪在,风寒和风寒不一样。城楼箭垛上的军士自然也挨冻染风寒。可他们的风寒不似城中的风寒严重,往往喝些热水,发发汗也就能好转。所以我敢断言,这城内的风寒绝不是普通的风寒,且具有传染性。所以索性这些守城的战士便不让他们回营,看似残酷,实则是对他们最有效的保护了。”花清夙说。
“可你刚才说,给参将们都用过药,可为什么公羊宗主的病逝没有缓解?”维谷问。
“这也要看不同人自身体质了。那个学者富兰克林,虽然染病比公羊博早,虽说症状也极重,却还不似公羊博和弗洛伊德那般重。公羊宗主虽然刚过不惑之年,但他身为宗主压力极大,身子便先垮了,弗洛伊德的病症也不比公羊博好多少。即便是两天后药不断,也未必救得回他们了。”
维谷艰难的点了点头,忽而又摇了摇头:“可不对啊。弗洛伊德前辈也染了病,可我试过他的额头,并不发热啊!”
花清夙摇摇头说:“那决计不可能,他额头滚烫,我半个时辰前也刚刚试过,才来吕将军府的。纵使出现第一例病情好转的,也不该是个老头子啊。”
维谷继续摇头说:“可我刚才试他的额头,确实不烫啊。”
花清夙眼睛一亮说:“真的么?”
维谷面上也露出一份欣喜,说:“当然,我们这便去瞧瞧?”
“走!”花清夙面带期望的站起身。
维谷也跟着站起来,却是重心不稳,趔趄了一步。
花清夙愣了片刻,眼中期许的亮光逐渐散去,她面色渐渐变得凝重,过了半晌才对维谷说:“你把手伸过来……”
维谷错愕的伸出了手。
花清夙伸出手指试了试维谷的掌心,她的神情呆住了。
见花清夙不说话,维谷有些迷茫,他越发的觉得这议事堂中的空气沉闷,令他呼吸急促。
维谷混乱的头脑中忽然出现一个闪念,思维断续间他仿佛想到了——他试弗洛伊德的额头不烫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那便是他自己的体温和弗洛伊德的一般烫。
“啊!”维谷长叹一声,只觉天旋地转,眼前模糊的光芒便消失了。
———
有的时候,人只有在睡梦中心思才清醒。
当你自闭视听,与世隔绝之时,你才能感悟冥冥之中之所念。
维谷的意识纷乱而模糊。一段段的记忆在他的脑中交叠闪过。闪过了莫甘娜与他切磋轻功的场景、闪过了他第一次登顶拒魔峰的场景、闪过了他第一次在宗主府列席参会的场景、闪过了他在工程院和基爷攀谈的场景、闪过了他和阿尔斯楞将军在城墙上侃侃而谈的场景……
而当这些画面一个接一个消失的时候,最后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剩一个倩影。
“雪鸢……,雪鸢……”
维谷在昏迷中念叨着。
花清夙将一碗驱寒的药汤为他灌下,随后想解开他的衣服,为他针灸。却见他迷糊中,右手却始终探入怀中。
为了帮他解开衣服,花清夙便把他的右手从怀中拽了出来。
却见被她从怀中拽出的右手里,握着一个锦囊。
花清夙好奇之下,想从维谷手中抽出锦囊一瞧究竟。
可不曾想她刚要把锦囊抽出,维谷却下意识的把手握紧,随即转醒,睁开双眼。
“你醒了!”花清夙说。
维谷睁开眼,意识却并不十分清晰,但他依稀分辨得出,眼前的花医师正在为他治病。
维谷一直以为自己头脑昏沉疼痛、浑身酸软乏力是连续七日推演算术过度疲乏所致,现在想来该是早就染了风寒了。可他非但没有及时医治,却仍旧没日没夜的推演运算,此时怕是已经病重难愈了。
他如今刚当上宗主,他不能倒下。可自己身体的感觉从来不会欺骗人,他已经难以凝聚自己的意识了。
仿佛在意识消散前,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努力让自己发音准确的对花清夙说:“你认识雪鸢么?”
花清夙坐在床前,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维谷却自顾自的继续说:“拜托你把这个锦囊送给雪鸢,我一直盼着有一天能把它送给雪鸢,可惜不能亲手送到了。”
维谷说罢这句话,便又昏迷了过去。
花清夙好奇的接过锦囊,将锦囊中的事物抽出,倒在手里。
是一串吊坠。
吊坠正中镶嵌的黑珍珠上雕着精细的纹理。
那俨然是一颗野樱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