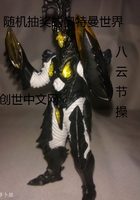带着无限的眷恋,项南踏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都是与华洁亲近的镜头。惟一的遗憾是那晚华洁躲闪了他的吻别,于是他的浓情郁结的双唇就空虚地一路南行,每晚吻着自己的胳膊而人眠。
项北在广州一家血库工作,每到晚上,偌大的一栋大楼里就只剩项北一个人,项南就住在那些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白天,项南要去一家期货公司打工。
项南原本对期货一无所知,培训了几天,仍是一头雾水。分到组里,组长澍韵的几句话就让他豁然开窍。期货与股票相似,低吸高抛就可以赚钱。不同的是期货可以先卖后买,高吸低抛也可以赚钱。
澍韵虽是组长,但其实比项南还小一岁,要不是有些暴露的打扮,她还挺像个中学生。期货比较难懂,但更难的是找客户。
公司明文规定,经纪人如果三个月找不到客户就自动走人。规定相当苛刻,但经纪人只要找到客户,特别是大客户,不管客户是赚还是亏,就能大把大把地捞进丰厚的佣金,一点风险也没有。
公司里常有经纪人从不名一文摇身变成百万富翁的。项南到公司的那个月,经纪人的月佣金纪录达到了十八万五千人民币,是年轻的澍韵创造的。公司所有的经纪人都以澍韵为榜样和动力。
看到一个并不很出挑的小女孩能创造这种奇迹,项南也变得热血沸腾,虽然他只是暑假打打工,也想创造一个神话。
但人生地不熟的他很快发现事情远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容易,暑假的广州,太阳毒过蛇蝎,马路上的行人各个神色匆匆,似乎有人在身后追杀一般,根本就没有人会停下脚步听项南讲什么期货。
一连好几天,项南都这样在各个马路口奔波,然后灰头灰脸地毫无收获地回公司。
入夜,项北加班的时候,他就特别想念华洁,给她写了好几封信,没想到居然还收到了她的一封回信。她的信如其人,永远那么矜持。对项南的称呼是那么严肃,一字不落,一字也不加,简简单单的就"项南"两字。
信中说道,"为了那古老而又古老,永恒而又永恒的主题,我那位一直就不开朗的女同学竟然傻得干出了这种事情......所以,我不得不在那位女同学家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可不是因为'寤寐思服,......"项南无暇多想华洁同学的事情,而是被华洁的端庄里的调皮所深深吸引。
第二天,项南照例打好卡去寻找客户,下电梯时碰上了澍韵。
"客户找得怎么样了?"澍韵关切地问,样子并不像一个领导。
"毫无方向。"项南苦笑着。
澍韵问项南去哪找客户,项南的回答让澍韵大吃一惊。
"你怎么能去马路上拉客户呢,你又不是小贩,再说有钱人谁会没事干跑到马路上去转悠。"
"那我怎么办,我这儿谁都不认识,你指点一下迷津吧。"
"三言两语说不清。这样吧,下班后,我带你去个地方。"
晚上,项南跟着澍韵来到一个酒吧。不大的椭圆形门口挂着两个红灯笼。灯笼底下站着一个笑容职业而又透着凉意的迎宾小姐,高挑而丰满的身体被一条乳白的旗袍裹住露出一身玲珑的曲线。检查了澍韵掏出来的卡,她举起手中的对讲机接吻一般讲了几句什么,门后钻出另外一个穿旗袍的姑娘,她伸出手把两人带进了大厅,而后又进了一扇门。黑幽幽的长廊的两旁立着许多鹰视狼步的小伙,都穿着清一色的黑色紧身背心。
两人跟着那姑娘钻山洞一般曲曲折折转了好几个弯,终于又到了一扇门前,立在门口的小姐费力地拉开门,澍韵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看得出,澍韵对这种环境已相当熟悉,项南紧紧地跟着。
门里是豁然开阔的天地,但仍然幽暗,像黑森森的一大片坟地,桌上的摇曳的红烛像鬼火一样缥缈,桌边顾客们的脸在红烛的映衬下面色惨白,而游动穿行烛火中的小姐们像《聊斋志异》里的显形的狐狸,身体特别地婀娜。
等项南在桌边坐定,他才发现这些小姐们穿得又薄又透。走进第二道门就一直胆战和冷却的血一下冲到项南的脑门,"这是什么地方,居然如此开放!"
"要点什么,两位?"小姐毫不在意自己几乎赤裸的身体,笑盈盈地问。
"来杯苹果汁,你要什么?"澍韵不动声色地问。
"水,水吧,矿泉水吧。"项南口干舌燥地说。
"什么服务呢?"小姐特意看了项南一眼。
"服务呆会再说。"澍韵回答。
小姐摇着臀飘走了。澍韵并不说话,也不看项南,似乎陷入一种怀念。项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不该和澍韵说话,说什么,也就这样飘浮一般地坐着,直到小姐送来了饮料和水,他才好像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双手捧着那杯加了冰块的水,不停地吸,像一个饿急了的婴儿突然回到溢着乳香的怀抱,他一口气几乎把杯里的水全部吸光,吸得胸腔和腹部急遽冷却像冰雪溶洞,但脸上仍然燥热。
邻桌的小姐一声不响爬上了桌,在小小的桌子上扭动身躯,两个男人的四只手在小姐的身体上恣肆地抚摸,手起之处却是一张张人民币,粘在小姐的光身子上。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这句话跃然项南的脑海。"不都是要钱吗,钱能满足各种欲望,不管这种欲望在本质上是多么地不同。"项南想着,眼神却一直被他们的一切行动牵引,小姐的胸脯终于被钱贴满了,像穿着一条奇异的胸衣,而落叶般的胸衣下像伏着一条蛇,游动着,像一条应笛声而舞的眼镜蛇,然而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在无声中结束。小姐撕下面膜一般撕下身上的钱,又弯腰捡起落在桌上的,把它们塞进短袜。
意犹未尽的男子对她耳语几声,她就把他们带到了门口,然后再踅身回到吧台。吧台前立着一长排姑娘,像小舟舷上待命的鸬鹚,五彩的射灯从各个方向交织在她们的身体上,把她们幻变成斑斓的热带鱼。Ⅱ巴台前的光与影在偌大的昏暗的洒吧里构成一个好看的浮在黑暗里光亮透明的鱼缸,里面的鱼频频变幻身上的色彩。项南都有些看呆了。
人在广州(2)
"怎么样,要不要叫一个?"澍韵靠近项南。
"别,别。"项南不由自主地摆手,可内心却非常地渴望,要不是澍韵在身边,他肯定会叫上一个。
"是不是因为我在这?"澍韵不动声色地洞察项南.的一切。
"没有,怎么会呢。"项南因被揭穿而有些发窘。
"你担心钱?不用担心。这儿的消费都会从我的金卡里扣掉。"澍韵仍鼓动着项南。
"不要,不要。"项南不知道澍韵为什么要这样,也不知道澍韵为什么要带他到这来。他坐立不安,浑身上下开始发凉,服务小姐给他带来的燥热渐渐退去,他不由自主地抖动着双腿,不知是在发抖,还是想从这徒劳的抖动中获取些许热量。
"既然已经来了,我们就应该享受一下,否则钱都浪费掉了。不过,你不要去碰她的身体,要碰要掏钱的,最低也是五十块一次。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澍韵一扬手,鱼缸里就游出一条鱼,熟练地爬上桌扭起来。
她的四肢章鱼的触角一样在他们的头上张扬着,项南却不敢过分地仰头,只是眼珠向上吃力地翻着,全然不觉眼睑被拉扯的疼痛。那小姐的四肢分分合合,或相互缠绕,或在敏感的区域做不接触的停留和抚、摸,纤细的手指把项南的欲望捻成了一根细细的丝,在她指引的身体上缠绕,也在他自己开始变得僵硬的身体上缠绕。
虽然周遭昏暗,项南还是觉得自己眼中已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欲望,他快速地瞟了一眼澍韵。澍韵却一眼的冷漠。项南收拾了眼神,低了下去。
小姐的一双白袜变得格外醒目,像两只小白鼠,又像一对缠绵的白蛾,翩然地舞着。也不知舞了多久,她突然跪了下来。
项南轰然地低下了头,而后又修复性地摆正,稍一扭头,就发现澍韵正在盯着他,鹰隼一样。
终于出了酒吧,迎面的一股热气让项南打了个舒服的寒战,从空调的冷气中回到室外的自然的热气的包裹中,项南觉得身体在回暖,体内太多的寒气被热风一点一点驱散,沿街走了好一段,他身体有些微微地冒汗,这才觉得全身真正舒爽,像一块解了冻的肉,终于柔和轻松,可以透口气,他有些贪婪地深吸了几口热气。
"你觉得她们怎么样?"澍韵突然问了一句。
"我觉得她们挺可怜的,被呼来唤去的,出卖自己的肉体。"在澍韵面前,项南机警地表示着对女人的同情。
"她们的确很可怜,但比起以前的生活,好多了。这些女孩大多来自农村,很穷很穷的地方,穷得根本没法想象。饿肚子那是常事。父母嫁女儿根本不是嫁,而是卖,谁有钱,卖给谁,但地穷人也贱,一两百块钱就可以买个女人。
到了婆家,就是用身体还债,白天在地里还,晚上在床上还。与其被贫穷折磨,还不如出来闯。人在贫穷的地方根本毫无尊严。"澍韵有些激动地说,
"不过,在这儿上班的女孩有她们的底线。男人可以看,可以摸,但她们并不出卖她们的灵魂。处女膜就是她们的灵魂和底线。守住这条底线,她们就能赢得更多的男人,也许不是所有的男人因此而尊重她们,但所有的男人因为这而更想得到她们,更愿看她们摸她们没有被玷污的处子之身。
她们反而比那些真正出卖肉体的能赚更多的钱。人总是要留一点尊严。太过尊严,是看不透这个社会也过不好日子,太看透了认为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也过不好。女人尤其如此。"
项南觉得这番话实在不像出自一个只读过高一就辍学的女孩的嘴,他隐隐感觉澍韵和这个酒吧有某种关联,但他不可能去问她。
"这个酒吧叫'楚楚酒吧',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大厅正门的酒吧对普通客人开放,正门左侧和楼上实际上是个会员制的俱乐部,楼上是给走极端的客人用的。那儿是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地狱,去了那儿的女人无法再回到人间,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项南不动声色但好奇地听着,心里面不时地生出疑惑:"她为什么要对并不太熟悉的我讲这些呢?"
项南的疑惑又被澍韵一眼看穿。
"项南,你不觉得我喜欢你么?别问我为什么,喜欢是没有理由的,只是一种直觉,说不清楚。我喜欢你什么呢?胆怯?害羞?有一点。虽然我看得出来你也好色,而你却良心未泯,心底还存着一份对女性的美好的情感。
你知道吗,我家就是农村的,很穷的农村,本来还不太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没想到河的上游建了许多个化工厂,把整条河都污染了,连井水都变了质了,河里的鱼都死光了,村民因为常年喝被污染的水,很多人得了癌症。我十六岁那年考到县里上高中,后来在学校待不下去了,家里实在太穷。一气之下,我就来到了广州。
刚开始,我不知遭了多少罪,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干,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脏什么是累。慢慢攒了一点钱,我去夜校学了电脑,开始到一些小公司应聘打字员。
工作的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处处我都碰到男人,他们都想从我的身上捞好处,有的想不花钱白占便宜,有的想花钱做交易,有的暗中动手脚,有的明摆着开条件。有的小公司招收员工,指明要年轻女性,他们根本就不是招员工,而是招情妇,有的甚至开门见山,说愿意做情妇就留下,不愿意的马上离开。
后来,我终于碰上了一个好男人,他是一家瓷器公司的老板,我开始进去打字,有时候我帮他指出一些笔误,后来他就让我做了他的秘书。跟着他,我几乎飞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但不管住多么高级的宾馆,他都会开两个房间。
他曾对我说过他也喜欢我,说没有男人不喜欢女人的,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和关公只是书里的人物。但他只喜欢和喜欢自己的女人做爱,而且这个女人不能因为喜欢他的钱而献身于他。
其实当时我真的爱上了他,爱上了他的真诚。虽然,他已经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但我能告诉他吗?我怎么说得清楚我喜欢的是他而不是他的钱呢?没钱连爱的资格也没有啊!
夜深星稀,珠江上吹来的风也渐渐变凉。项南弄不清楚澍韵和那个瓷器老板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弄不清她怎么做上了期货,弄不清她为什么要带他去那种地方,也弄不清为什么她要给他讲这么多的肺腑之言。
但他隐隐约约地感觉澍韵在同情他,在把他当作刚来广州的自己来同情和引导,教导他不要太遵守社会的规则,否则只能永远趴在社会的最下层,永远翻不了身。
她并不了解项南,这也难怪,项南应聘时撒了谎,说自己是高考落榜的农村青年。
项南的感觉第二天得到了证实。澍韵又带他去了另一家酒吧,到了门口,澍韵站住了。
"这个酒吧是专为女人服务的,里面的服务员都是男扮女装,顾客大都是富婆,当然,也有男的,有些变态的男人,你去看看,说不定能碰到好机会。我晚上还有事,就不陪你了,祝你好运。"说完,转身扬手钻进了一辆出租车,把项南单独撂在了酒吧门口。项南像被扔进了漆黑的汪洋大海,酒吧像一艘船,但是一个让项南感到比海洋更危险的地方。他在门口发了一会呆,最后心情沉重地回到了血库。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项南的期货终究是没做出一点名堂,只好每天在公司外游荡。但他越来越开心,因为他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华洁了,毕竟每天晚上吻着手臂睡觉的日子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