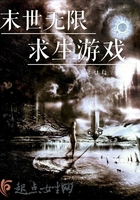闹钟响了七次,骆帝良喝了六碗豆浆,沙发间里仍然没有动静。
直到他吹着口哨,敲起了饭盆,吴鸣才被叮叮当当的声音吵醒,睁开了眼睛。
一睁眼,便瞧见左右两张俏脸,笑吟吟的看着他:“老公,早。”
卢静起身收拾“战场”,鱼蕊则东一件,西一件的给吴鸣套着衣裳。
卢静连忙捡过一件毛毯,裹在鱼蕊身上,狠狠拍了下她的小屁股:“都多大了,也不知道害臊,都给人家看光了。”
鱼蕊揉着屁股,瞅了瞅屋外的骆帝良,毫不在意:“嘁,看得见他也吃不着,怕什么。我鱼蕊这辈子,生是吴家的鬼,死是吴家的人。”
吴鸣冷不丁刮了下她的鼻子:“反了反了。”
“啊?”鱼蕊睡眼朦胧,完全搞不清状况,随便应了一句,继续忙着手里的事情。
“老公是说,你的话说反了。应该说生是吴家人,死是吴家鬼才对。”卢静一边叠被一边提醒她说。
“哦。”鱼蕊蒙头转向,并没听出前后两句有什么区别。
她没反应,吴鸣却急了:“哎呦我的小祖宗,我是说,你把我的袜子穿反了。”
结果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吴鸣的衣服是卢静给穿的,鱼蕊的衣服是吴鸣给穿的,卢静的衣服是人家自己穿的。
吴鸣出了沙发间,活动活动筋骨,一眼瞥见地上的包装壳,问:“凉凉,你这是在干什么?”
“喝豆浆啊。”骆帝良扬了扬手中的饭盆。
“靠,有你这么喝的嘛。”吴鸣用脚尖踢了踢那座空壳堆起来的小山包,一脸惊愕。
“豆浆滋肠润胃,有助消化,并且还有祛寒排气的功效。如果再叫不醒你们,我就要施展必杀技了。”说着,骆帝良提胯收臀,抬起了屁股。
“我去,别别别别,我错了我错了,凉凉哥,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睡懒觉了。”盯着他胀起的肚子,吴鸣仿佛已经听到某种“咕噜噜”的声音。那股躁动,呼之欲出。吓得他连连退出七八步,用手掩住鼻腔。
嬉闹片刻,吴鸣又问:“怎么就你一个人,萱萱呢?”
骆帝良端起饭盆又干了一碗,指指地板:“她去楼下健身了,与和尚哥他们一起。”
正说着,神和尚三人归来。
神和尚与谭晓换了套情侣款的休闲装,长袖体恤,纯棉长裤,限量版休闲鞋,妥妥的郎才女貌,般配。
慕萱也是一身休闲款的运动装,运动鞋,玲珑剔透,青春洋溢。
看到小夫妻俩的容光焕发,吴鸣不禁调侃起来:“嘿嘿,哥,你这也算坠落红尘了,恭喜恭喜。”
神和尚撇了一眼里间,当下明了:“同喜同喜。怎么样,这两位弟妹,你可还吃得消?”
吴鸣一阵语塞:“呃,还好还好。”
“是吗?”神和尚质疑一句,突然闪电出手,探出二指,直奔吴鸣的眼睛。
吴鸣条件反射的旋身,侧头。
神和尚变指为爪,顺势扣其咽喉。
吴鸣双腿较力,身体向后滑出。
神和尚欺身而上,步步紧逼。
无奈,吴鸣抽出腰间生存刀,一刀刺出。
哪知,腰眼上募的传来一阵酥麻,吴鸣顿感臂弯无力,指掌未松,刀却落了地。
“铛锒”。
一愣的工夫,神和尚的食指已抵在他眉心上。
吴鸣摇摇脑袋,又爱又怨的瞅瞅两个女人:“唉,英雄难过温柔乡。哥,我昨晚过于放纵自己了。”
神和尚在他头上狠狠拍了一把:“兄弟,你瞎说什么呢。男欢女爱本就是人之常情,你们怎样折腾都没关系。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要时刻保持警惕,要保持灵活的反应,保持充足的体力。她们爱你,你就该保护她们,不是嘛。”
“和尚哥,是我们一直缠着他,他才没睡好觉的。你就别骂他了,要骂就骂我俩呗。”鱼蕊屁颠屁颠的跑到神和尚身旁,挽住他的胳膊,不停的摇晃,哀求。
吴鸣换上一脸正色:“这不是责骂,是关心。正因为他关心我,我才拿他当哥哥。你们俩今后也要和我一样,听他的话,记住了嘛。”
“嗯,记住了,老公。”
谭晓拉了拉神和尚袖口,神和尚会意:“昨天咱们五个人表现不好,今天所有的工作由我们承担。凉凉和萱萱可以放假,自由活动。”
“哦。”
答应完,众人将他们两个往一起推了推,拉近点距离。他们知道,和尚哥哥这是在牵红线,竭力成全。
刚开始,俩人完全进不了状态。
骆帝良想帮吴鸣擦枪,吴鸣说你别来,这些枪只有经过我的手,才能发挥出最佳性能。慕萱想帮女人们煮饭,女人们说你快走,不然等下我们会挨骂。
后来两人彻悟,大家是在给他们制造机会。
饭都送到嘴边来了,难道不吃?约,约他娘的。
一步步,一行行,俩人下了楼梯,肩膀靠在一起,胳膊挨着胳膊,只差牵手的一瞬间,只差八字的一小撇。
晨风瑟瑟,伴着朝露,有点凉。吹散了秀发,拂过微胖的脸庞。
骆帝良脱下外套,轻轻为她披上。
慕萱娇躯一震,心中浮上暖意。衣服很暖和,然而更暖的,是他这个举动。
无人的街道很长,他们却不知该去哪边。放眼望去,满地皆是凄凉,实在不适合风花雪月。
绕了一圈又一圈,骆帝良停下挠挠头:“要不,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我是吃着粗茶淡饭长大的。”嘴上说着不去,慕萱脚下却加了急,直奔那间破屋。
店铺很精致,北欧式的格局,黑白灰的更迭变幻。即使大部分设施已然破败,东倒西歪,却仍给人以简约,典雅的氛围感和视觉享受。
智能咖啡机早已失效,好在店里备有手摇咖啡磨,咖啡豆保存良好,完全可以将就。
粗犷的胳膊旋转着纤细的摇杆,发出“咯吱咯吱”的悦耳声音,像金属乐,又像摇滚。
骆帝良肥胖的身体与那小小的咖啡机形成鲜明对比,看起来不大协调,甚至有些搞笑。慕萱“噗嗤”一声,被逗乐了,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节奏感不错。酒精炉在哪,我帮忙烧水。”
感受着近在咫尺的女人香,骆帝良陶醉了。他加快速度,处理好最后一捧咖啡豆。然后搀起慕萱的手,将她送回座位。那份小心,就像在搀着一位公主。
“女孩子的手,最好别用来干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会变糙的。”
说着,骆帝良风风火火的架好酒精炉,随便找个耐热的容器,加满水。
等水开的时候,他一把牵过慕萱的手,从防弹马甲里掏出碘伏和指甲护理随身包,小心翼翼的擦拭着那些被弓弦勒出的血痕,为她剪掉老茧,剔除死皮,嘴里面还说:“这些东西要经常剪一剪,保养好的话,不会留疤,永葆水嫩。”
慕萱居然破天荒的没有反抗,从小到大都没有人给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油然而生。身体有意识的不拒绝,不扭捏,任由他拉着自己的手,精雕细琢。
全身心沉浸在没有危机,没人打扰的宁静时光中,直到炉子上的水沸腾,发出“扑扑扑”浇灭火焰的声音。
慕萱舍不得抽回手,只是挑了挑下巴,提醒他:“水开了。”
骆帝良眼皮都不抬,一丝不苟的继续着手中的事情:“水可以再烧,你的手只有一双。”
不知怎的,慕萱感觉鼻子一阵酸楚,眼眶里有种咸咸的味道。
强压下莫名的感动,慕萱将另一只手搭到他手背上,微微阻了阻他的动作:“冲好咖啡再弄也不晚,我又不会跑。”
“嗯。”
骆帝良二话没说,风驰电掣一般搞定了咖啡,端来方糖和奶片,连同调羹、糖夹一并摆到慕萱面前。随后一屁股坐下,又开始了他未完的“工程”。
“你自己的呢?”慕萱问道。
“我现在有比喝咖啡更重要的事情,等下再说。”骆帝良应了一句,不容置疑的拉过慕萱左手。
没办法,慕萱只好独自品着咖啡,看着他的脸,听着他的唠叨:“碘伏能消毒清创,每天擦擦这些勒痕,很快就会消褪。这些死皮老茧年头有些长,需要一层一层打薄,让新肉取代它们的空间。不过这事急不来,一次剪太狠了会伤到皮肤。反正以后多的是时间,我慢慢帮你剪就是,保证让你的手恢复如初。”
“我从小就生活在丛林里,每天与弓箭刀斧打交道,有些老茧很正常。再说了,现在丧尸横行,少不了磕磕碰碰,更不可能有时间在意这些事情。”心扉一旦敞开,慕萱不再有芥蒂。
“没关系啊,你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这些由我来在意就行了。”骆帝良一本正经的说了句,马上又觉得不妥,改口:“呃呃,我是说,只要你有时间,我随时都可以帮你处理。”
骆帝良腼腆,慕萱则不然。身为丛林战士,她的选择只有两种,杀,或是不杀。爱,或是不爱。
“我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因为家族的某些变故,爸爸不愿意让我留在寨子里。所以说,我们以后相处的日子可能会很长。也许是三五年,也许是一辈子。呵呵,谁知道呢。你现在这么在意我的手,恐怕以后要辛苦喽。”慕萱讲的很直白,笑的像朵花。
这是表白吗?骆帝良一愣。
自己身为堂堂男子汉,居然先被一个女孩讲出了这种事情,丢不丢人?
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忽闻一声枪响。
“砰”。
子弹穿过门楣,射进店铺。
不知是对方有意为之,还是枪法太烂。这一枪并没伤到人,只打断了慕萱头上的吊灯。
“呼”。
几十斤重的大家伙倏然而下,如泰山压顶一般。
骆帝良像闪电一样弹起,踹开桌椅板凳,身子一横,将慕萱娇小的身躯完全抱在怀里,掩于身下。
“嘣”的一声巨响,吊灯砸在骆帝良背上,铁钎似的装饰物扎穿了他的肩膀,鲜红的血滴滴答答落到慕萱脸上。
“喂,你怎么了?”慕萱撑起身子,紧紧扶住他的身体。
骆帝良说不出话,一屁股跌坐下去,只是摆摆手,表示自己没事。
慕萱柳眉倒竖,当即摘下木弓,冲向店外。
转过身,皓腕忽被骆帝良抓住,豆大的汗珠顺着他额角淌下。他咬咬牙,拼着力气将她拉到怀里,躲在椅子背后。
骆帝良摇摇头,有气无力的说:“是,是,是丧尸狙击手。你的弓射程不够,千万别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