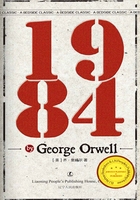“没事的,你很正常。”阿次扶阿初坐定,他感到阿初的身体在湿润的风中颤栗,他脱下外套,又迟疑了一下,因为外套湿漉漉的,他索性把贴身的棉背心脱了,给阿初穿上。自己再穿上那湿漉漉的外套。
风怎么会如此湿润呢?甚至带着一点新鲜的泥土味。
阿次检查过坚固的墙壁后,没有发现一丝的破绽,没有空心砖的踪影,他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门在哪里?
他的手上捏着粉碎的玻璃碴,这些碎碴子,不是玻璃镜片,而是水晶制作的饰品,也许是女人头上戴的水晶珠花。那么阿初所说的,宽而亮的镜子在何处呢?
阿次的眼睛从岩石上,回顾到水潭底。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水珠漾起了波纹,水面溅显花蕾,水是活的!静静的深水潭,粼粼涟漪,水底流淌着一条通往新生的门。
阿次站起来,因潮湿和寒冷,他打了一个冷颤。但是,他的心不冷了。
镜子,阿初口中的镜子,不在石壁上,他应该指的是水!二十年前的水潭,也许是宽而晶莹透明的。
阿次俯身就水,试了试水温,水温冰凉,表面浮有碎雪渣。
“你发现什么了?”阿初关心地问。
“镜子。”阿次回眸淡淡一笑。
“镜子?”虚弱的阿初,神情依旧很恍惚。“什么镜子?”
“等一下告诉你。”阿次脱掉皮鞋和外套。
“你干什么?”
“我去探探路。”
“你知道哪里水深水浅?”
“凭感觉吧。”阿次说。
“你是专业人士,你应该下判断,而不是凭感觉。”
“你是权威人士,你曾经从这里走出去。”阿次说。“是你的幻觉,引发了我的直觉。相信我,没事的。”阿次潜水而下,他的脚踩到了水草,水下静谧而又安宁,飘过一个岔口,他发现了水下的岩石洞口。岩石洞是天然的,洞里堆积的石块阻塞了水流的前行,成功地分流而下,洞里应该没有积水。他爬上岩石洞的天然石阶后,发现了血迹……
他看见了微弱的光亮和一扇开启的木门,阿次相信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出口。他深呼吸一次,两次,心态平和。石阶上的点点血迹,滴滴嗒嗒地引领着阿次走向木门,木门的把手上有一个清晰的血手印。血是腥的,证明有人刚刚路过。
阿次想,深不见底的谜底就要被揭开了。
自信敢于决疑。
阿次不急不缓地推开了门。
阿初坐在岩石上,看着阿次堆放在岩石上的外套和皮鞋,注视着水潭里不时泛起的浪花,他隐约感到内心的忧郁和恐惧,正无休止地在黑暗中放散,弥漫。
阿初一直很自信,他认为自己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此时此刻,他的心却向神灵祈祷,他感到神的威慑,他甚至想到自己父母的亡魂应该出来救阿次,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内心的懦弱,他怕失去阿次,也怕自己枉死在此!
人间和冥界只有一步之遥。
水面激荡起数朵浪花,他看见阿次浮出水面。阿初的心一下踏实了。
“怎么样?”
阿次浑身是水地爬上来,他甩了甩湿润的头发,口里呼出白色的气,从腰间取下一个白色塑料包。
“什么东西?”
“防水布。”阿次答,“特制的,给你用。”
“我会游泳。”
“我知道,底下太冷,你听我的,跟我来。”阿次言语简洁,语气却很有分量。
阿次把防水布拉开,像是一个透明的小睡袋,阿初在阿次的授意下,睡了进去。阿初没有跟阿次谦让,一切都仿佛事先演练过一样,阿初相信阿次有能力把自己顺利带出绝境。
阿次把自己的皮鞋和外套也塞进了防水布袋的下方,然后他涉水而下。阿次在水底全力托举着阿初,游向目的地——岩石洞口。
很快,他们到达了洞口的石阶。两个人爬上石阶后,阿次扶阿初小坐。
“我想,我也许找到了出口的捷径。”阿次说。
“谢谢。”阿初在喘息。
“谢谢逝去的亡灵吧。”阿次低头说。
“亡灵?”阿初的神经敏感地颤动起来,“你发现什么了?”
“可能,我发现了谜底。”阿次穿上皮鞋。
“在哪里?”
“在木屋里。”阿次说。
阿初站起来,很严肃,“你看见了什么?”
“一副骸骨。”阿次说。
阿初沿着石阶前行,走到木门边,他清晰地看见了血手印,血很腥,味很重,他推开了木门,里面很窄,很冷。他走进去,一步一个寒颤,只觉得四周阴霾重重,鬼影幢幢,不似人间。
逝去的光阴重现,黑色的帷幕撕裂开……
阿初看到有一张床,床头上挂着一件日本和服,大约是粉红色的,很喜气,虽然岁月的痕迹将和服的色彩磨灭,却依然有某种暧昧的欲念在上面流动。仿佛冥冥中有人暗示,暗示这件衣服的主人,是一个日本女人。
床下有一个被废弃的铁皮桶,桶里有一个空酒瓶。
“是日本清酒。”阿次说。
床上有一副凄凉的骸骨,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床上,阿初不知怎地,忽感一股分辨不清的莫名哀怨扑面而来,泪水夺眶而出。阿次不说话,他的心底大约描画出了二十年前的某个细节,他用手按住了阿初抖动不止的肩膀,说:“不要太难过。”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难过?”阿初哽咽。
“你猜测到了母亲遇害的真相。”
“说来听听。”
“这件和服想必就是母亲……母亲遇害时元凶所穿。一个居心叵测的日本女人,通过复杂的易容手术,悄悄来到上海。她蛰伏在慈云寺的地下室里,伺机而动。在这个阴暗、潮湿的洞穴里,她嫁给了她所爱的人。”
阿初的头抬起来,显然,他从自己所了解的事件中,没有解读到这一段细节。
“这件和服是日本少女的花嫁服,做工精致,色彩艳丽,粉色樱花代表春天,振袖代表少女,花嫁新娘装是日本女性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而她却把花嫁服丢弃在阴暗的洞穴里,她一定是在这里完成了她少女的心愿。她的情人却被她残忍地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你错了。留在这里的不是她的情人,而是我们的母亲,亲生母亲。”阿初情绪有些失控,他心中压抑、隐藏很久的痛楚骤然间引爆,悲苦之情一泻千里。“这副遗骨,是一名年轻的女性,她是被人用非人道的、极端残忍的杀人手段所杀害的!她是被虐杀的!她是被人腰斩的!这些变态的畜生,我要让他们付出这一生最惨痛的代价!”
阿初的瞳孔开始放大,几乎绽裂。
当阿次听到这副遗骨是一名年轻的女性,而且是被人惨无人道地杀害后,他的内心深深震动,无法平静,不管这女人是否是自己的生母,她都死得可怜、凄惨。
“二十年前的某一个夜晚,母亲带我夜宿于慈云寺,有人密谋、策划好了一套谋杀计划,她们一定是扮作寺庙的女尼,诱骗母亲落入陷阱。然后,这个日本女人在这张肮脏的床上,与她心爱的男人云情雨意了一番,她告别了这个男人,去冒充另一个女人,进入这个女人的家庭。她剥下了母亲的衣服,从里到外,她脱下和服后,就彻底伪装起来,她穿上母亲的衣服,踏上归家的路,夺取这个女人所拥有的一切幸福人生。包括她的孩子、她的骨肉。而我们的母亲被他们残忍地杀害在这永不见天日的黑暗巢穴。这就是真相。”一直困扰在内心深处的谜团,霎时得以揭开。然而,阿初和阿次的心态再次向“怒”与“疑”之间互动、挣扎。
“这只是臆断、猜测。”阿次说,“我们需要证据,更需要先从这里走出去。”
阿初冷笑。阿次知道,由于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相差太远,所以,他们面对过去的悲伤投影,不免会掺杂着自己的感情色彩。
“她刚来过。”阿次把话题巧妙转移到“女鬼”身上。
阿初不说话。
阿次继续说:“你觉不觉得这里空间很高,声音很空,房间的形态也很畸形。地板是木头的,为什么墙也是木头的呢?我们就像走进了一个烟囱。”
忽然,阿次头顶感觉到了小水滴,他抬头望顶,顶高而黑。
“江南多雨啊。”阿初喃喃自语。
阿次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阿次说,“怪不得,如此潮湿,却没有一丝霉味,空气很新鲜,知道了,花非花,雾非雾……鬼非鬼,树非树……”
“想好怎么从树心里爬上去了?”阿初问。
“想好了,距离树干并不高,大约九米,徒手就能攀上去,我背你。”阿次提出建议。
“你行吗?”阿初仰望着密匝匝的奇特的枯树干。
“你肯吗?”阿次眼睛里习惯地挑衅。
阿初开始脱外套,阿次明白,阿初想减轻自己身体的重量,换而言之,阿初在为自己减轻负担。
“不用脱了,上面冷。”阿次说,“来吧。”
黑暗深处,阿次背着阿初开始徒手攀援,阿初的气息不均匀地低喘,阿次隐约感到阿初有恐惧感。“不要往下看。”阿次温情地提示。
“你不要讲话。”阿初说。
阿次低声笑笑,信任和真诚在彼此的患难中互相渗透到对方的心中。就在阿次接近树干的时候,他听到了树干的抖动声,这种抖动和风声无关。
他敏锐地嗅觉准确做出了判断,头顶上有人。
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阿次的头……
阿次机械地抬起头,他看见了母亲接近扭曲的一张脸。
小山缨子笑起来,森然地笑起来……她的笑声远比她的哭声更可怖,活在地狱中的小山缨子重新闻到了她渴望闻到的血腥味。
“阿次……”
“妈!”阿次的声音很恳切。但是,他已经将阿初转移到胸前。摸出腰际的铁钩,死死插入树皮深处。“妈,我是你带大的,你不能这样对我。”黑暗中,阿次的口气像是在哀求。
这两声“妈”,让小山缨子的手颤抖起来。“阿次,不要怪我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似乎情不自禁地喜欢过你,疼过你,我送你去日本留学,就是希望你能成为半个日本人。我这样疼爱你,你不珍惜,是你,是你自己来寻死路的。黄泉路上,不要怨我。”
在小山缨子说话的时候,阿次已经成功地让阿初紧紧地挂在铁钩上。
“妈!你疯啦!”阿次说。
“我不是你妈,你妈在下面。”
“我不信!”阿次拖延时间,为自己脱困做准备。
“你不信?你不信,你会骗我来?”小山缨子在喘。
“我没有!”这一句理直气壮。
“你骗我来也就算了,你还想炸死我。”
“我差一点也被人炸死!”阿次抬头逼视母亲,“我差点被活埋了。”
“是你干的!我养了你二十年!”
“你养了我二十年,你还拿枪对着我的头?”
“你想活是吧?”小山缨子阴冷地说,“我给你机会,你把那个人扔下去,你把他扔下去,我让你活。”
“我要不肯呢?”
“你去死吧。”小山缨子握紧了枪。
“我死之前,要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求你告诉我!”
“不要求她!”阿初怒吼。
“你看看,你想救的人,他利用你,他害你,他是一个魔鬼。你信任他,不然你怎么会背着他往上爬?你就跟你那该死的大哥一起去做鬼吧。”
“思桐!”阿次大叫。
枪声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