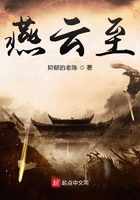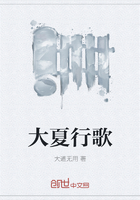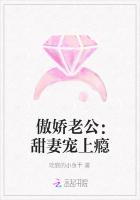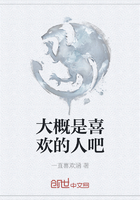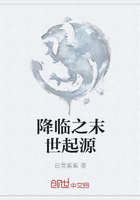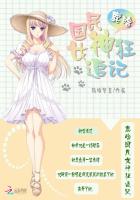毛南族是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历代居住在打狗河畔的群山之中。瑶族在西边与他们隔着打狗河相望,水族、布依族在北部与他们比邻而居,壮族、汉族在东、南两面与他们接壤。毛南族与这些兄弟民族都往来频繁,和谐相处,在日常生活中,相辅相生,共谋发展。
第一节商贸交往
一、商贸交往
毛南族虽然地处偏僻,但着名的黔桂古道就是从毛南族人聚居地之一的木论地界横穿而过的。这条古道曾经是中国西南交通的要道之一,被誉为大西南的“丝绸之路”。几百年来,古道上商旅往来,络绎不绝,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条古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就是从这里走出乡关的。这条古道对于毛南族与其他民族的商贸交往,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毛南族很早就与外界有着割不断的商贸往来,据《宋史》载,咸平(998~1003年)、庆历(1041~1048年)年间,“抚水州蛮”屡向宋朝进贡器甲及方物。嘉佑(1056~1063年)之后,“月赴宜州参谒及贸巨板,每岁州四管犒,及三岁,听输所贡兵械于思立砦,以其直偿之,递官资迁补”。《宋会要辑稿》载,治平四年(1067年),广南西路安抚司言“今后宜州、安化州蛮将板木入中,依元定价支赐,不得退嫌,合支酒食盐面等,并破系省钱”。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宋代,毛南族先民就开始与外界进行交易了。在官府与毛南族先民进行“通贡”的同时,汉族商贩也经常把食盐等日用品贩入毛南地区,换取当地少数民族的土特产品。经过“通贡互市”,宋廷回赐锦袍、银带、匹帛及其他器物,因而不断把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知识传播到这块“边徼”之地,既增强了边远地区和中原王朝的联系,也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对于当时毛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历史上,毛南族与兄弟民族商贸的交往主要表现为大量引进外界的商品和技术,输出本民族的产品。引进的商品包括食盐、日用百货等,引进的技术主要是制造技术;输出的产品主要有铁制品、棉纺织品、竹编制品、银器饰品、矿产品等。
(一)铁制品。近代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毛南族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从而促使手工业商品的生产进入繁荣时期。据《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年),毛南族的泗水村就以打制铁工具着名。又从中南乡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获悉,毛南族从事打铁业已有300年的历史。特别是在100多年前,曾有湖南铁工匠来到毛南山乡打铁。他们不但能打制农具和武器,而且产品工艺精良,很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本地工匠经拜师学艺或私下偷学,大大地提高了打铁技术,使毛南族铁工匠打制的工具和武器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至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从事打铁业的已有六七十户,其中有五六户已从农村举家迁到圩镇,专门从事打铁工作,实现了同农业的分离。而绝大多数的打铁户依然与农业相结合,农忙时耕种田地,农闲时开炉打铁。他们打制的铁产品种类,主要是铁锹(踏犁口)、刮子、锄头、斧头、柴刀、镰刀、菜刀、耙齿、禾剪等。这些铁制产品外形美观大方,淬火技术过硬,经久耐用,在本地区及周边民族地区都很有名气。据《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后区(清朝咸丰年间,思恩县分为中、左、右、前、后区,后区是毛南族的主要聚居区)下疃乡之下依村人,制造家用刀、锹、耙、普通镰刀及细齿镰刀等农具最精美,昔商人运往河池、东兰各地发售者颇多”。从中可知,毛南族地区的铁器销路很广。少数技术较高的铁匠能打制锯片、土枪(火药枪、拉八、猎枪)等。除上述铁制产品外,毛南族铁工匠还能打制适合取水难地区特殊的取水工具小口锡壶、锡桶以及家用的锡盆等。而打铁所需要的钢材、生铁等原材料,则从宜山、怀远等壮族、汉族地区输入。可以说,毛南族地区的铁器产品能得到迅速的发展,最终扬名桂西北,一是靠毛南族工匠的智慧,二是要归功毛南族工匠与周边兄弟民族工匠在技术和原料上互动的结果。
(二)棉纺织品。繁荣程度仅次于打铁业的手工行业是纺织、染布和缝纫业。纺织作业是无需他人相助,一人即可从事各个环节的劳动。故纺织是毛南族最为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在民国以前,毛南族地区绝大多数家庭都种棉花,他们将自己种出的棉花用于纺纱、织布,有当地木匠师傅制作的纺纱车和织布机。农闲时期,几乎所有的成年妇女都能纺纱、织布,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走进哪一个村屯,都可听见机杼声响。用木制的纺织机织出的土布幅宽一尺二寸,厚重结实,经久耐用。到民国年间,比较富裕及纺织技术较高的人家,织出棉布的质量上乘且数量多,除供家庭人员缝制衣裤外,还把剩余的布料投入市场。随着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在圩集中出现了染布业和缝纫业。染布业是自染自用的,均分散在各村屯,有这一手艺的人也只是极少数,方圆几里内也只有一两人而已。而代他人染布的作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下南圩集有两间。他们为当地的民众代染纺织的土布,按布的重量收取染费。在染布的基础上,还出现了“染画”印染业,把毛南族所喜爱的“狮子滚球”“双凤朝阳”“双龙戏珠”“麒麟送子”等象征吉祥的图案印染在背带、被面和门帘上,以此种工艺印染出的布制品深得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喜爱。
缝纫业在毛南族地区是规模较大的手工行业。缝纫业在毛南族地区出现较早,据《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民国初年,各处大圩场开始逐步采用少数车衣机(缝纫机)以代人工……毛南、水源、洛平、洛阳、麻村各村亦各有缝纫机数架,日事工作”。这些车衣师傅都以代他人缝制衣裤、床上用品为业,每套衣裤或每张床单收取若干手工费。另有少数车衣者,散居于毛南族地区的各个村屯,可人数极少,他们在自己家中为他人缝制衣裤。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仅下南六圩从事缝纫业的就有十七家之多,其中有十六家是毛南族人开设的。他们在为本民族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为周边的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的人民提供服务。
(三)竹编制品。毛南族人多有善于编织竹器者,毛南族的竹器编织以花竹帽最为着名。据《思恩县志》记载,毛南族地区的中南、下塘的三百峒、茶峒等村有百分之四十的人编织花竹帽。他们利用农闲、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进行编织,所编织的花竹帽做工精致,经久耐用,是妇女一件很好的装饰品。直到现在,该产品的实际功能虽已经丧失,但仍然是毛南族人赠送客人的礼品,而来到毛南族地区的客人,也都以得到一顶“顶卡花”为荣。
(四)银器饰品。毛南族的银器饰品也颇具盛名。银器制作在毛南族地区虽只有两三家,但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制作技术也较高。据调查,毛南族妇女所佩戴的银器饰品,清代前是由湖南银匠打制销售的。后来,毛南族的一些心灵手巧的铁工匠从中学会了打制银器的技术,而且革新了传统制作工艺,所制作的银手镯、银项圈、银麒麟、银环、银筅、银锁和“五子登科”帽饰等银器饰品非常精巧,吸引了本民族及其周边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人民。
(五)石雕产品。历史上,毛南族的石雕工艺独步桂西北。由于毛南族聚居地都是大石山,石多土少,因此毛南族人很早就大量地利用石头。他们不但利用石头建造房屋、修造坟墓、修建公路和桥梁,而且很多生活用具也都用石头制成,如石磓、石碾、石凳、石槽等。这些日常生活用具都雕刻精美,堪称艺术精品。有的能工巧匠还受聘到外地从事石刻生产,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石刻艺术品。一些石匠把自己刻制的各式生活用具拿到市场上出售,受到各族人民的青睐。
(六)陶器。毛南族的陶器也是很有名气的。据《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在仪凤乡,大多数家庭都能制作陶器。在仪凤、上光等村,有的全家从事陶器生产,产品有陶盆、陶碗、陶鼓、陶缸等。这些陶器做工精巧,形状工整规范,而且表面还涂上釉,使所制的陶器品表面光泽透亮,硬度更高,畅销“三南”境内外。
(七)土纸和沙纸。毛南族地区遍地生长着的沙树,枝繁叶茂,它的叶子是菜牛和猪的优良饲料,树皮则是造纸的上好原料,因而毛南族有生产土纸、沙纸的传统。据《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后区之头沦村亦擅造沙纸,且较之葛家、上北(思恩县产沙纸之地)为优。纸质以沙树皮为之,足供全县之用。宜北、河池边地均用之”。由此可知,当时毛南族地区的沙纸不但质量上乘、产量高,而且远销“三南”境外。土纸产于下南的仪凤,沙纸产于中南三圩。其纸质纯白而柔软,有韧性,除可供写字用外,又是毛南族及壮族、汉族人民于清明节供奉祖先时最佳的祭祀用品。
(八)酒饼及酿酒业。酒饼也是毛南族有影响的商品之一。酒饼是酿酒的必要原料。毛南族制作酒饼的原料全部是用产于本地的中草药配制而成的,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用酒饼酿造的米酒芳香而味纯,酒精度高,喝醉的人不会头疼或有其他不良反应。下南乡的上纳屯、中南的南昌屯都以制酒饼或酿酒而闻名。
(九)矿产品。在清朝中叶毛南族地区已经出现人工采矿产品。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下南干峒就设立有炼铅厂,且明确规定该项产品必须向朝廷交纳课税,可见其冶炼规模已经不小。据记载,当时除课税铅之外,余铅积存尚达164万余斤。而到民国时期,政府曾招雇毛南族农民数十人当矿工,在中南乡的干孔村开采水银,至今仍保留有矿坑、矿砂和冶炼水银火炉的遗迹。在波川一带的石灰岩溶洞中,储藏有丰富的硝矿,不少毛南族农民前往采矿熬硝制成火药,对外出售。硝制品有塘硝、白硝。硝是制黑色火药的主要原料,塘硝还是施于玉米、稻谷植株最好的碳肥。
总之,近代以来,正是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技术的革新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使得商品贸易得以快速发展。最终,毛南族和周围苗、瑶、壮、汉等民族人民在生产、生活资料方面的交换活动不断地扩大和繁荣。特别是在外地商品及“洋货”逐步输入的情况下,毛南族地区形成了许多市场,这些市场的圩日实行传统的农历轮转制。“每月三十日,天天有圩赶”是毛南族地区圩集众多的写照。近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地区的商贸交往,主要是通过这些众多的圩集来完成交换和流通的,也有汉族、壮族商人把毛南族的土特产品运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二、圩场
由于环境和历史的局限,毛南族的圩场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萧条到繁荣的过程。直到民国初年,毛南族地区才有众多圩场形成。据民国22年(1933年)《思恩县志》记载“县地边鄙,商场冷落”。又民国26年(1937年)《宜北县志》亦有“县属边僻之地,交通不便,处处圩场至属微小”“圩场中卖品仅猪、牛肉、白米、棉布、鸡鸭而已”的记载。当时全县上规模的圩集有思恩、明伦、牛峒(今川山乡四圩)、洛阳二圩、毛南六圩、常洞(今吉祥)、梁洞四圩、达贡(今东兴)、水源一圩、喇门(今水源三美)、温平、寨国(今大才)、安顺九圩(今大安)、驯驻九圩(今驯乐)等。而在毛南族聚居的中心区域,真正属于毛南族籍的圩集有中南的三圩、下南乡仪凤的五圩、上南乡的八圩、下南乡波川村的九圩、下南乡堂八村的十圩。以上圩集的圩日是传统农历的轮转式圩日制,即初一赶水源的一圩,初二赶洛阳或木论的二圩,依此类推。圩日,四乡的民众可根据自家的需要奔走于各个圩场。或将自家所产的铁制品、纺织品、印染品、银制品、竹木器具、白硝、黑火药、花竹帽、缝制好的衣裤、石器具、陶制品、土纸沙纸、烟叶、酒、酒饼、桐仁、中草药等,拿到圩集上摆卖,获取钱币后,买回自家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具用品,或将自己生产的商品,与周边来赶集的苗、瑶、仫佬、水、壮、汉族商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到了民国后期,由于匪乱纷起,社会秩序不稳定,毛南族聚居中心区域荒废歇市的圩场很多,如下南仪凤的五圩、上南乡的八圩、下南波川村的九圩、下南堂八村的十圩,荒废歇市至今。至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人民经常赶的主要圩场有以下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