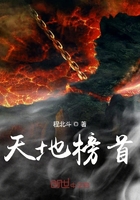过去的日子不可留,新来的日子使人愁,尚在年幼的耿子建虽说苦恼了很长时间,但新式的家庭生活倒使得他日渐开窍了许多。他还搞不懂什么是幸福生活,父亲脸上的笑容就是他幸福的全部,可又不太像,二大爷也好像跟着笑,老哥儿俩的笑容一样不长久。这个兼并重组的家庭首先需要磨合,那些不可避免的尴尬一下子都冒出来了。
第三天,耿玉崑亲自赶车去了一趟五里桥,把那个瘦得皮包骨头,手脚布满暗绿色的疤痕,因呼吸艰难常常被憋得泪流满面的男人接来了……
“齁巴”不仅尴尬也最可怜。这些年,为了妻子和孩子能摆脱窘困,他不仅提出过离婚还寻过短见。喝了一次卤水没死成,孩子们对他看得更紧了……耿氏兄弟的所作所为令他感动不已,耿玉霖叫他“哥”,把他安顿在温暖的西屋,吃饭时让他坐在中间,愈是那样他就愈感到不安。玉霖叫他哥他也答应,同在一个屋檐下,叫就叫吧,可每次都像在他心头上搓了一把盐。
那年秋天,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不容乐观了。经年累月大量服药,肺病没治好反倒把肾、肝、胃都吃坏了,现在又出现了并发性心力衰竭等症状,痰里不断有血,胸腔内发出空洞的声音……他再次想到了自我了断,可转念一想又觉得对不起耿家兄弟。现在,奄奄一息的心情反倒复杂起来,有解脱的快感也有深深的眷恋。
齁巴在极其苦闷中又煎熬了半年,那天下午,他觉得胸腔涨鼓鼓的厉害,“哇——!”地吐出了满口的污血,之后无比清醒,他知道这次是真完了……
子建饲养的小羊又生出了一只小羊,每天临睡前,他都要给这个刚刚做母亲的山羊多喂一捆青草。“赛虎儿”是面瓜家养的母狗下的头窝崽子,雄性,虎头虎脑的,还没断奶便由面瓜抱来献给了子建,是子建用山羊奶喂大的,现在已经成年,只要一见到子建,它便毫无理由地、快乐地、傻乎乎地摇着尾巴围前围后的乱跳。
自从这只羊羔儿降临到这个世界,子建每天清晨都能听到母山羊的召唤,看到小羊羔儿眼里闪着莹莹的蓝光,带着初生的喜悦快乐地奔跑过去曲下身子,探寻着母羊的****儿,而母羊则温柔地掉过头——这哪里是一只羊啊,分明是一只温顺的母鹿,它也确实长着一双母鹿般美丽的让人怜爱的大眼睛。母山羊嗅嗅自己的****等待羊羔来吸吮,羊羔儿跪在母羊身下伸长脖子,用头抵两下乳房,细长的后肢欢天喜地的打着颤,短尾巴快乐地摇着、抖动着,随着血热的、可爱的乳汁流入口中,它那新生的躯体抖动起来。每当这时,子建的神情便异常专注,赛虎也像懂得他的心思扑伏在主人脚边,用羡慕的眼光打量着幸福的小羊羔儿。
子建的身材貌相与父亲愈来愈相像,整个五官该鼓出来的努力鼓出来,该深陷的尽量陷下去,鼓出来的额头宽宽阔阔,鼓出来的鼻梁笔直挺拔,深陷的眼窝儿里藏着一双不算大的眼睛,但很有神——这一点,他继承了刘翡翠的遗传。
耿玉霖是个整脸子人,他不像耿玉崑那么会稀罕孩子,他总是把喜爱藏在心里,往往在儿子不注意的时候,专注地瞅着既像自己又像翡翠的儿子,儿子的血脉里终归流着他和翡翠的血,有时他觉得儿子实在不像他,更多是像翡翠。翡翠的聪慧在儿子身上有着更多的体现,尤其是看到他那两只白皙敦厚的耳朵,简直就是从翡翠身上拓出来的,可他却说不出亲热的话,也做不出疼爱和亲昵的表示,他几乎没有抱过儿子,更没有像耿玉崑那样把他架在脖子上逗他咯咯笑过,他已经察觉出儿子和他之间存在着距离,也曾试图找回他们之间的那种父子亲情,但却一直也没有如愿。现在,儿子已经到了上学读书的年纪,他就更没机会说抱就抱过来,说亲就亲一口了。
小学校坐落在河南岸公路边上,院墙四周笔直的钻天杨树闪闪发亮的树叶挡住了直射向操场上的烈日,校舍残破不堪,但对于子建他们却充满着莫名其妙的吸引力。
正是雨水旺盛的季节,缺乏日照的蒿草下面散发着腐烂的霉变气味,一些微小的不知名的昆虫,在潮湿的草丛里享受着只有它们自己能够体会到的安逸。面瓜突然惊叫起来,猛地蹿出去一头撞在单杠上晕了过去。
子建跑过来看究竟,面瓜坐在地上,指着墙跟底下的一条裂缝让他看。一条蛇的小眼睛在墙缝里闪闪放光。这条花脖子毒蛇慢慢地爬出来了,大约出来有一尺,它的头左右摆动着,摆出随时随地要发动进攻的姿态。
赛虎儿和子建同样兴奋,紧张地匍伏在地上注视着这条毒蛇。这种俗称“野鸡脖子”的毒蛇很具攻击性。它又爬出来一尺多,子建举起木棒,它好像意识到处境危险,立即把头钻进墙根的另一条缝隙,想把尾巴尽快调过来。赛虎儿一跃而起,快速咬过去,蛇的身体紧贴着地面和土墙构成的直角,这一口没咬着,当蛇尾调过来时,赛虎冲过去把它拖了出来。“啪”一声,子建的木棒打在地上折成两截,这条毒蛇昂起头刚想反扑,被赛虎儿咬住了七寸。面瓜见没什么危险了,才捂着额头躲闪着过来查看。子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挑着死蛇炫耀着,一甩恰巧落在了乞月儿的脚下,把她吓得“哇哇”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