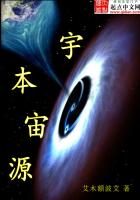土地改革,是决定中国农民命运的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土改前,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为甲粮户做长工或为乙东家做佃农,遇到灾年走投无路之时被迫吃粮当兵甚至落草为寇,土改后,中国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崭新的社会制度,带来了崭新的希望和崭新的生活内容。土地,犹如农民的灵魂。他们捧着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欢天喜地像过年一样,他们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从内心里深情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民主政府万岁!”
有道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近百年来,乌白两家如同太极阴阳调整着东荒地的平衡。驼龙血洗东荒,制造了东荒地甲子惨案,乌子玉因为二儿子乌常荣当了土匪含愤而终,乌家先行败落,经过土改白家也跟着败了,东荒地固有的格式被彻底打破,东荒地从此进入了另一个历史时期。
乌家的败落,催生出来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乌常荣的儿子,乌四郎倌儿。东荒地的老百姓经常用一句口头语来形容乌四郎倌儿父子:根儿不正,梢儿不正,结个葫芦歪歪腚儿。
乌子玉抑郁而终,不久,乌常懋哥几个便把家分了,分家后乌家哥几个都断绝了跟乌常荣这枝的来往。四郎倌儿一副天生的闲人骨头,整天游手好闲招猫逗狗,成了一个人嫌狗臭的屎盆子。没出几年,分到他们娘儿俩名下的田产房宅大部分都被他输掉了,他妈被活活气死,剩下四郎倌儿一个人更没了收管,只身住进村东头一间废弃的土屋里。
四郎倌儿住的屋子只有一个小窗户,屋里光线昏暗,即使是大白天也看不清屋子里的情形。屋里有半铺土炕,炕上放着一张瘸腿小饭桌,一床棉被,油渍麻花地看不出本色,棉花套子滚成了一个一个的疙瘩。炕上跳蚤成球,每次他光着身子钻进被窝儿,都会听到兴奋的跳蚤撞击他的皮肤和被子啪啪作响。爱开玩笑的人编笑话嘲笑他,说:某年除夕,一对饥寒交迫的老鼠夫妻拖儿带女的去给他“拜年”,转了一圈儿,临了连一粒粮食也没看见,结果这对老鼠只好含着眼泪走了。所以,他家根本没人去更不用上锁,只在风门上象征性的别一根草棍儿,回来时扒拉开就可以进屋。
四郎倌儿昼伏夜出,白天装病躺在炕上蒙头大睡,待太阳落山了他才来精神,四处寻赌耍钱,不到后半夜决不回家。每次回家,掰一根葵花秆点着当火把,深一脚浅一脚地哼哼着小曲儿,招来一路狗咬,一觉睡到第二天晌午,外面的喧腾世界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好梦,后来架起的广播喇叭,吵得他不得安生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幸福的家园……”这个清脆圆润的学生腔儿出自耿红柳的嗓子。四郎倌儿卷曲着身子捂着耳朵,用最淫亵的语言把耿红柳和她的母亲、奶奶、祖宗十八辈甚至五服以外的女性逐个问候了一个遍。
这小子就是这么牲口,他问候的许多女性姓乌,跟他有着亲疏不等的血缘关系,可他不管这一套,他有他为人处世的原则:谁搅扰他的美梦,他就对谁不客气……很明显,从那时起,四郎倌儿白天就无法安睡了。他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以往这会儿他还在梦里,现在被大喇叭吵醒,他的肚皮提前咕噜咕噜叫起来,这让他很苦恼。
四郎倌儿的人生信条是,吃了今日就不去管明日,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虚的,只有吃到肚子里的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月补助的救济粮,又不例外地被他换成挂面和鸡蛋改善了生活,用余下的一捧粮食换来几吊小钱儿早就被他输个精光。
四郎倌儿知道,这个时候去找村长耿玉崑想办法只能白遭一顿数落。有心上山刨些草药卖给供销社,林子里又闷又热,山路陡滑,小蠓虫还直想往眼里钻,迷眼睛不说还辣得淌眼泪,再说,辛辛苦苦把那些破草根子刨回家又洗又晒,还要受供销社那些鳖犊子压等压价的闲气,到头来换不来一壶醋。这个愚蠢的念头刚一萌生,就被他扼制了……
在四郞倌儿名下,还剩下一片山林和两亩薄田,山林撂荒着,那两亩地他也不爱种,索性租给了旁人。不过,这对他来说倒是件幸事,划分成分的时候被认定为小土地出租者,政治上享受着上中农的待遇,但真正有田产有家业的上中农又耻于跟二流子为伍,每逢他觍着脸向屯子里的上中农央告帮忙时,他们会扭过头去朝地上啐一口:“呸!送子观音瞎了眼,咋生出这么个猪狗不如的懒东西……”所以,跟这些人借粮是不可能的,想到此,气得四郎倌儿直骂:“妈的嘞,迟早有一天老子要共你们的产!统购统销,折产归公,看你们到那时候还神气不!”此时此刻的乌四郞倌儿,是典型的叫花子咬牙——发穷狠。
村头的大柳树下,是闲散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长者们聚会的地方。他们在树下晒着太阳,讲今比古谈论逸闻趣事,回忆着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展望着年景盼望有个像样的收成,孩子们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一旦四郎倌儿手中拮据没了赌博的本钱,就成了柳树下惟一的年轻人。
四郎倌儿在长者的圈儿外敞怀露胸地掐着虱子,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长者们平时虽然为人厚道,但对整天围着他们转的二流子也不免口尖舌利起来,他们会动不动拿四郎倌儿说事儿:
“新社会了嘛,当然不能眼瞅着有人挨饿……可真要是给那些老弱病残的困难户发放救济谁都没意见。可就那位,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五大三粗的一粒儿粮食不交不说,反倒长着一张嘴捞集体的救济,啊呸!”
一旦有人提起这个话茬儿,准有敲边鼓的:“那谁家的老孩子从小叫爹妈惯得没边儿,横草不过,竖草不拿,东游西逛闲得牙干口臭,还尽想吃香喝辣的,长大了也强不哪去,还不得和那位一个德行!”又有人咂着嘴:“啧啧,可不是么,干部开会煮挂面,二流子也在家里煮挂面打荷包蛋——你算老几,也配?”
四郎倌儿尽管时常被生活所困扰,但他似乎总能沉住气,早已经习惯了自轻自贱,听到这些连挖苦带损的话,非但不生气还挺凑趣儿,装出一副可怜相儿:
“哎!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儿哇,走几步就上喘,不值得爷儿几个总把我放在心上,你们就当我是个屁——放了我吧!……不过,现在的干部啊,日子过得可真是不赖……”他轻而易举地把闲话的目标转到干部那里去了。
虽然多数时候,人们并不把四郎倌儿当作正经的发言者,但有时候从他的风凉话中透露出来的信息也不能不使这些老人们皱眉头。你必须得承认,这小子的眼神和鼻子确实比他们好使。
当时,有几类人是满嘴新名词:一类是区里下来指导工作的干部,一类是青年团员,一类是那些青年积极分子,再有就是像他这样的二流子。乌四郎倌儿喜欢凑热闹,从而掌握了大量的流行语汇,而那些时兴词儿也给他带来了好处,每次申请救济时,可以用这些新名词表表态:
“今年就这么的了,身子不好……等来年我把病养好了,我一定勤奋劳动,积极投身到火热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去,用实际行动去支援抗美援朝……还有那啥,那啥保家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