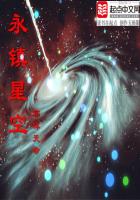又是新桃换旧符。白家大院内张灯结彩,显眼的墙上、门上都倒贴着“福”字,取福来到的寓意。临街大门上贴着一副“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大幅对联,影壁上贴了个大大的“春”字,新贴的春联鲜艳夺目,好一派红红火火的鸿福盛景。
黄喜子刚刚遛完马正在给马饮水,关七爷领着白桦拜书馆的先生回来,一进院门看见拴在院子里的两匹马和放在地上鲜亮的鞍韂觉得眼生,一问才知道是五爷回来过年了。五爷白继臣跟关七爷从小玩到大,两人感情很深,听喜子一说,高兴得一溜儿小跑儿着去了上房。
客厅里,梅先生正陪戴延年围着炭火盆喝茶说着闲话。梅先生告诉关七爷,五爷去了东厦屋看小少爷去了,他只好悻悻地告退出来,从喜子手里接过竹扫帚给马刷起身子。两匹军马在他的扫帚底下快乐地颤抖着皮毛,饮马剩下的半桶温水撂在地上还在冒热气。关七爷拎起水桶刚要进马厩,见五爷跟在四爷身后走过来,扔了水桶迎上去。
戴延年的菊花青通体炭青,点染着酷似霜花的斑点,白继臣的坐骑通体如同黑缎子涂了油脂。两匹高头大马蹄如海碗,结实得能踏碎一切。见到四爷从身边走过头颅扬起,四处侦听的耳朵像转动的雷达,从鼻孔里喷出一股股热气,绕着拴马桩不安地踏着冻土……庄稼人生性喜爱牲畜,队伍上饲养的牲口虽不能拉套驾辕,可看着它们那股子龙性劲儿,白四爷联想到两个兄弟冲锋陷阵的威武模样,心中欢喜,丢下五爷和关七爷,匆匆奔了上屋。
宽敞的客厅,方砖铺地,黄梨木镶大理石的八仙桌桌面上摆着红木架的缂丝绣屏,德国造的镂花自鸣座钟两侧是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长颈瓷瓶和一棵南海的老珊瑚树,八仙桌正上方挂着一幅六尺宣的“五子拜寿图”,拜寿图两边挂着书写着三十个大篆体的洒金“寿”字条幅,戴延年身着微服,坐在雕花的太师椅上,优雅地用碗盖拨着盖碗里的茶沫儿,俨然是一副巨商富贾的作派。
看上去,戴延年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沉稳干练了。漆黑的上髭修剪得甚是整齐,腰杆儿挺拔笔直,裤脚扎着窄条绑腿带子,足蹬一双千层底礼服呢面棉鞋,深栗子色团花对襟软缎棉袄的兜口与纽袢上斜吊着怀表的镀金链子。以往戴延年总是身着笔挺的军服,佩带奉军的上校军衔,今天这身便装打扮让四爷看着眼生,可好像更觉得亲近了许多。
梅先生见四爷进来,忙站起身来。四爷抱拳当胸身子微微前倾,问梅先生:“敢问,这位老客儿是哪一位呀?——啊?”
梅先生疑惑地看看戴延年,又看看掌柜的:“这位不是……”
四爷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把梅先生笑得直发毛:“我的好兄弟呀!你可回来啦!”
梅先生手捻胡须,看着他们笑着摇摇头。戴延年听见爽朗的笑声,抬头看见四爷站在面前,忙放下茶碗将嘴里的茶叶吐掉,站起身来抱拳还礼:“几年不见,兄长一向可好?”
四爷跨上前去,紧紧握住戴延年的双手,忙不迭地说:“好好好!这可真是,清早喜鹊叫,必有贵客到啊!我说这喜鹊咋叫得这么欢呢,真是想都不敢想,原来是你这位贵客盈了门啦!快请坐,快请坐!自家兄弟再弄那些俗套的礼数就见外啦!”戴延年笑了:“看看看,还说自家兄弟呢?兄长把我当贵客,这不是见外是什么?”
四爷摘下四喜帽子递给梅先生,在梅先生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来,真诚地说:“咋能说不是贵客呢?你带队伍一走,一晃儿就是五六年。哥哥这些年可没少惦记你。就连做梦,我都想你啊!”
梅先生给四爷泡上茶,见五爷进来,忙搬过一张椅子请他落座。白继臣冲梅先生笑了笑,感慨道:“几年不见,七哥见老了!”白继臣现在是戴延年的副官,一身戎装显得愈发英武俊朗,他感叹着关七爷见老的话,解下精致的马刀和驳壳枪,连同武装带一起挂在靠墙角儿的衣帽架上却没有落坐。四爷说:“可不是老了呗,能不老吗?……铜打铁铸的人也得老啊!”
覃氏领着凤春儿进来,凤春儿手里托着一个点心盘,覃氏替她提着一只茶壶。凤春儿将几碟福源馆的点心、糖果摆好,又为戴延年、四爷、五爷和梅先生续了水。覃氏和戴延年简单寒暄几句,带着凤春儿告辞奔厨房充任指挥去了。
戴延年重新落座,从贴身口袋里掏出用黄绫子包裹着的《金刚经》,打开放到桌子上:“这是给夫人的见面礼,聊表兄弟一番敬诚之意吧!——别的东西夫人也不稀罕。”
四爷将金刚经捧在手上,信手捻看了一页,念道:“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好好好,这个好!”他并没有过深地去理解这句话所表达的含义却连声称好,尔后包好递给梅先生:“烦舅老爷给太太送过去吧,告诉太太,戴将军来家过年啦!”
梅先生正欲转身出去,戴延年拦住他,说:“还请先生代我转告嫂夫人:挎枪之人,禅堂之上有菩萨,冲着了罪过不合适,我就不去当面请安啦!”
自从跟随戴延年参加东北军,白继臣还是第一次回到东荒地,不知自家这几年都有哪些变化,心里惦记着,遂对戴延年和四爷白继业说:“你们哥儿俩先唠着,我随舅老爷到各房去转转,等做好饭了再回来。”
梅先生见掌柜的没有别的什么吩咐,便和白继臣出去了。戴延年弯下腰打开脚边的柳编提包,俏皮地说:“剩下的可都是咱们这些凡夫俗人的东西啦!”
四爷客气道:“回来就回来呗,还带啥东西呀?”嘴上虽然这么说,可还是探过头来看稀罕。戴延年将一些胭脂、香水、丝绸布料之类的东西摆了一桌子:“这几匹塔夫绸和扬州官粉,是送给小姐夫人们的。”又拿出几卷儿用红纸裹着的银元和一个精制的木匣儿说:“来的仓促,也没有什么准备。这棵参和几块大洋就当是我送给新嫂子和小侄儿的见面礼吧!”说着,又把个捆扎得方正结实的牛皮纸包放在四爷面前:“这云土是送给哥哥的……”
四爷揭开木匣,掀开红绸布不由得倒吸一口气:“咝——”为难地说:“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这这这,这礼太重啦,哥哥我不能收哇!”戴延年解释说:“这不是长白山的野山参,这是棵高丽参。这种参药性温和,可畅通血脉、明目益智、驱气散闷、行气活血,可入药,能泡茶,还可入膳……你我老兄老弟的,何苦还要说什么礼轻礼重的话呢?再说,可就生分啦!”
四爷听他如此说,只好收下人参和烟土:“你把这些大洋快收起来,我不要。等你把钱攒起来,日后给我娶房弟媳妇回来,比你送我金山银垛都高兴!”见四爷态度坚决,戴延年只好把大洋收回柳条包去。
四爷探出身子把烟袋伸向火盆,吐出一口烟雾,借题发挥道:“你别怪我刚一见面就数叨你,你也老大不小了,也不知道你这个光棍儿要打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儿。”戴延年听罢朗声大笑起来,笑够了,方才一本正经地反问道:“像我这样的人还成什么家呀?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俩肩膀抬着一张嘴,独立大队,人走家搬,想走就走,想睡就睡……哪天死了,大不了臭块地。”
四爷不爱听:“大过年的嘴上没有个把门的,咋顺嘴胡咧咧?兵荒马乱的,别净说那些不吉利的丧气话……光棍儿单身你倒是轻手利脚了,可毕竟枪里弹里没人记挂,连个疼你的人都没有,你说哪点好?常言道,家常饭粗布衣,知疼知热结发妻。有了女人,热汤热水的不说,晚上也有个给你暖脚焐被窝儿的。我就不信,你还能总年轻,就没有个老得动弹不动的那一天?你总这么拖着,算咋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