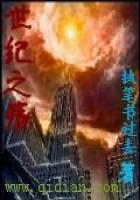还不到中午,耿玉崑便一再催促二娘,让她赶紧拾掇跟他去车站接子建两口子。食杂店老板还没见过这老两口一块出来过,觉得新鲜待问明缘由,忙把板凳和茶水摆在树阴下,招呼老两口坐下来让他们边喝茶边等。
耿玉崑愈来愈频繁地揉起了眼睛,不时仄起耳朵倾听,嘴上的小烟袋已经熄灭,口水顺着烟杆儿往下滴落在鞋面上。他的脑子里已涌满了许多东西,场景、情绪、幻象在午后的阳光下合而为一。
汽车停在站点上乘客依次下车,二娘搀着耿玉崑热切地迎上去。
戴筠感到眼前的场景画面感很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耿玉崑。她见过这样的老人:在电视里见过,在画报刊物上见过,在稠人广众的场合见过。这位老人,让她想起了罗中立那幅著名的油画。
耿玉崑饱经沧桑的面孔花容绽放,他用腋窝夹着拐棍儿老远便伸出了臂膀,高兴地说:“可算到啦!”耿子建紧走几步搀住他,把戴筠介绍给大家认识。
戴筠见一位穿戴利落的老太太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便冲着她笑笑。耿子建说:“这就是咱二娘!”戴筠问候道:“二娘,您身体可好哇!”二娘连声说好。见戴筠把手伸过来一时却没了主意,慌手慌脚地不知所措,仰头去看戴筠的脸,想伸手去摸又觉得不妥,举到半空扑打起戴筠的衣服来,不住声夸奖:“看看我家天赐媳妇这模样儿多体面,皮儿白肉细水豆腐似的。再瞧瞧这美人痣长得也俏皮……只可怜老三这个短命鬼,他要是还活着该多高兴啊!”
女人的眼泪总是比话要来得快些,耿玉崑见老伴儿流眼泪连忙制止,说:“你这老婆子,刚见面就哭天抹泪儿的让孩子们心难受。快快快,回家,麻溜儿回家!”其实,二娘的眼泪有一半是因为看见戴筠嘴角上的美人痣勾起了她对耿红柳的怀念。旋即二娘又喜泪涟涟,忙不叠地说:“对对对,快回家!……二改子,快跑!回家告诉你爸、你爷,说你子建大爷和大娘来家啦!”
戴筠见二改雀跃着跑了,悄悄掐了耿子建一把,问:“二娘说那孩子叫我什么?”耿子建解释道:“叫你大娘,就是伯母,东北的叫法儿……”戴筠只是笑,耿子建知道妻子又在作怪。
耿玉崑说:“听说你们要回来,你二娘和你那些姊姊妹妹的把该预备的都预备妥妥的啦。光是被褥就晒了好几遍,该浆洗的也都浆洗了,这两天比两年都熬人……”二娘说:“你看你二大爷现在学的,老来老来还倒学起编瞎话儿了,自个儿盼侄子不肯说还生要编排别人。”耿玉崑胡子翘翘着:“我咋说瞎话啦?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实情?”耿子建朝二娘挤挤眼睛,说:“我知道,我二大爷向来不说瞎话儿,都是真的!是不是呀,二大爷?”大家说笑着,簇拥着下了马路。
耿玉崑在戴筠的搀扶下行走,虽不习惯却乐意享受着这难得的亲情,扭脸跟耿子建搭话:“才刚儿那孩子,你兴许不认识。”耿子建问:“谁家的?”二娘说:“是长贵的二小子,叫二改。大的叫大改,大号叫徐改革,这小子叫开放。大改可是个搂钱的耙子……”她忽然狐疑起来,问:“应该跟你们一趟车呀,昨天下晌去给牛马行市场送鱼……咋没见着这崽子下车呢?”
耿玉崑说:“我好像看见他下车了。不知道今儿个是咋的了,鬼嗖的,像是怕见人。”二娘说:“八成是见不得生人!”耿玉崑说:“他见不得生人,谁信!”
耿子建想起来了,那个在候车室跟人拌嘴的年轻人,心里说:是啊,那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车站的空地上,摆着卖李子、海棠、香瓜还有蘑菇和干鱼之类的小摊子,见玉崑接到了子建两口子,都热情地围过来打招呼,耿子建也跟他们寒暄。那些不认识子建的小摊贩们都放下生意打量他们,耿子建友善地跟他们点头打招呼。正在寒暄之时迎面又走来了几个人,二改在前头引路,徐长贵、牟二邋遢把耿子建手中的行李接过去,相互握手拥抱起来。
耿家两扇黑漆大门洞开,一个扎着羊犄角辫儿的小女孩,探头看到耿子建他们走近,忙跑回屋去报信,等在屋里的人都涌出门来迎接,也有忙着架火烧水没出来的。
二娘掀开锅盖见铁锅里的水烧得翻开,对正在切面条的长贵媳妇说:“行,还是老规矩——上车饺子下船面。先下碗热面给他两口子垫补垫补……别忘了多打几个荷包蛋。完了刷锅预备饭,今儿个我留大伙儿一块儿热闹热闹。”
说话间,大改和二邋遢媳妇一前一后进了院子。大改换了件质地很好的西服,脖子上还系了条鲜艳的领带,只是头上的那顶帽子和脚上的名牌运动鞋叫人看着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
大改走在前面生怕弄脏西服,奓开两条胳膊提着只竹筐。竹筐里装了一条足有十斤重的鲤鱼,黄灿灿的鳞片比鹌鹑蛋还大,头尾翘在筐外。二邋遢媳妇还是平常装束,左肘挎着鸡蛋右手拎了半铁桶豆腐,腋下还夹着一捆大葱。他们身后又跟来几个孩子,挤在院门口看热闹。
戴筠换上了宽松的衣裤,衣袖挽到肘部,刚刚洗过脸用手帕扎起了打湿的头发,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扑伏在脑后。脚上的皮鞋也换成了软底软面的布鞋,清爽爽地伫立在众人面前。孩子们缩手缩脚想进又不敢进,戴筠拍手招呼他们,见被叫的孩子反而向后退,就说:“都进来,阿姨给好吃的!”胆小的还是很拘束,胆大一点的扭扭捏捏进了屋。
戴筠唤了一声“子建呀!”却没人应声,她拉开提包拉链抓出小食品分撒给孩子们。
长贵媳妇把鲤鱼收拾干净截成几段放进大盆里,又给灶膛添了几块柈子,长贵媳妇的动作连贯有序,说话不耽误干活儿。
她边干活儿边打量戴筠:“他大娘呀,你长得和相片上不太一样!”戴筠先自一愣马上回过味儿来,知道这声“他大娘”是指孩子叫的,是在跟自己说话,忙说:“没有照片上的好看。”长贵媳妇忙说:“那可不是!起先看到你相片大伙儿都夸,天赐娶了个电影明星……今儿个见到真人儿,比相片儿还耐看,说话也好听!”
戴筠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只好冲她笑笑。长贵媳妇并没察觉出戴筠难为情,继续赞叹着:“听说还恁有本事,手下还有好多的人为你做事,还尽都是有学问的……同样是女人,你咋能够做成那么大的事情呢?同样是女人,城里的和乡下的就是不一样。哎!同样是女人……”
戴筠被她说得愈发不好意思起来,撕开一条香烟准备招待客人,却发现满屋子皆是孩子,男人们嫌室内窄小吵闹到屋外去了。外屋,姑娘媳妇们抱柴禾切菜的,也有抓鸡杀鸡的。
男人们都待在老棠棣子树的荫凉下,有坐在木墩上或爬犁架子车辕上的,有随便蹲着或站着的,手里都夹着红塔山香烟。
耿子建蹲在他们中间,吸烟的姿势有点生硬,夹着香烟的手还握着分剩下的烟盒,指间飘出的青烟熏得他泪眼汪汪的。他挥走眼前的烟雾,继续与兄弟叔伯说笑着。人们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吸烟,不紧不慢地讲述着地里的粮食收得够吃,感激风调雨顺,感激现今的国家,感激现今的农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