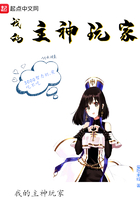傅卿云和安国公赶到客房的时候,傅冉云正衣衫不整地缩在一个婆子的怀里哭泣,鬓发散乱,她哭的很小声很压抑,是那种生无可恋的哭泣。
傅卿云讽刺地勾了勾唇角,傅冉云是真哭了罢,毕竟她成功爬炕的男人与她期待中的人差太远了,堪称云泥之别。
傅卿云朝定南侯行礼,语气严肃:“父亲。”安国公也拱手行礼。
定南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说道:“卿丫头,你和安国公来了,你们看看该怎么办罢。不管如何,这次是我们定南侯府有错在先。冉丫头,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头疼地扶额,大房没有主母,他不得不亲自出面处理,审问清楚真相后,他都没脸面对傅卿云了。
傅冉云如此做,跟当年小林氏的做法何其相似,同样是妹妹破坏姐姐的幸福,把自个儿送到姐夫的炕上,事后却又表现的那么楚楚可怜。只不过他这个女婿是好的,比他幸运,没有中招。
傅卿云问明经过,意外地看了眼跪在一边没有存在感的地锦。原来地锦的娘重男轻女,生了三个女儿,第四个就是地锦还是女孩,于是想淹死刚出生的地锦,是小林氏无意中经过下人房时听见婴儿的惨叫,救了地锦。地锦懂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心中一直惦记着小林氏的救命之恩,想要报答,是她主动找上傅冉云想帮傅冉云的。
傅卿云暗嗤,地锦可恶,傅冉云也不无辜,地锦一个小丫鬟可不敢策划这么大的事。
定南侯也注意到地锦,冷冷地说道:“这个丫鬟在书房里不好好伺候,偏偏生出这般歹毒的心思,害了姑娘,又害了姑爷的弟弟,来人,把地锦拉出去重打二十大板,发卖了罢!”
很快便有下人把地锦拖了出去。
傅冉云哭求道:“父亲,地锦只是想帮我出家庙,女儿也不想在家庙里虚度光阴,这才出此下策,干出这种不要脸面的事来,求父亲要责怪就怪我一人,不要迁怒地锦。”
傅卿云淡淡地低头俯视着傅冉云,说道:“父亲岂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迁怒别人的人?地锦敢把注意打倒主子头上,就是大不敬,何况把主子的清白都弄没了,更是死有余辜,父亲没有打死了她已经是看了妹妹的脸面。”
傅冉云哭声一顿,脸色苍白如纸。
定南侯哼道:“好好跟你姐姐学学,什么叫明辨是非!”
傅卿云叹了口气,定南侯终究是舍不得傅冉云这个女儿的,听他的口吻还是想饶过傅冉云,并让淳于家给傅冉云一个名分。
傅卿云转而开口说道:“父亲,二妹妹的事相当棘手,她是婚前失了清白,本就没有妇德,这事又是她不对,故意做下的,说句公道话,二妹妹不堪为淳于家的儿媳妇!”
傅冉云猛地喘了口气,定南侯脸色讪讪的,淳于沛意外地瞧了眼傅卿云,唯有安国公镇定如初,似乎知道傅卿云接下来会说什么。
傅卿云没有看众人脸色,接着说道:“除此之外,沛二弟已有婚约,定的是聂家的表姑娘,这是皇上亲口下旨赐婚的,没有别的可能。如此一来,难道真的要让二妹妹给沛二弟做妾不成?”
说完,她像是因傅冉云的丑事而羞于见人,扭过了头。
傅冉云不敢置信地望着面前的一群人,一口老血涌到嗓子口,给这个恶心的人做妻就够恶心了,做妾?那真是暴殄天物!傅冉云不甘心,死也不甘心!
定南侯也才想起来的确有过这回事,脸上阵青阵白,只觉得半辈子的脸面都被傅冉云丢光了,正要开口,傅老夫人扶着杜鹃的手急匆匆进来,冷哼道:“做妾?我们傅家的女儿从没有做妾的,谁要做妾,就不许姓傅!”
言罢,傅老夫人骂着“不成器的”,提起拐棍打在傅冉云身上,打得傅冉云吱吱乱叫,跟狗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躲避,十分狼狈。
傅老夫人发了狠,当即命人把傅冉云扔出定南侯府。
定南侯到底不忍心,想要求情,傅老夫人沉着声音说道:“子不教,父之过!你这个当父亲的教养出了这种女儿给家族丢脸,你还敢包庇她,替她擦屁股?她有这个胆子做下这等祸事,还不是仗着你那一份不忍心!赶明儿个你就去宫里觐见皇上,家里的事你别管了,去边疆戍边罢,免得你长久待在府中,变得跟娘们似的优柔寡断,心肠软!”
定南侯被老母责骂,顿时脸红,喏喏地不敢言语,傅四夫人就在一边说风凉话:“老夫人是念佛的,这些年清心寡欲,能把老夫人气成这样,可见,二姑娘做的事连佛都气得跳脚了!”
定南侯一听,知道傅老夫人不是开玩笑的,生怕把傅老夫人气出个好歹来,当天就在傅老夫人的催促下进宫,求了去戍边,出了宫,就叫来安国公。
安国公知道定南侯的为难,主动说道:“泰山大人,我和卿云会好好照顾傅二姑娘的,不会让她吃苦,请您放心。”
定南侯吸了口气,下定决心说道:“冉丫头这次的确过分了,我不怪你,也不怪你弟弟,只是她到底是我女儿,血浓于水。既然你家二弟已有婚约,那就随便给她个通房或者姨娘做就是,唉,说实话,我本来怜惜她,经了这件事,我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了。”
这话安国公听过就罢,不会当真,当下安抚两句,翌日就送了岳父出京。
傅冉云被安排在淳于沛的院子里,安国公和傅卿云商量后,找来淳于沛,两人在书房里谈了半宿的话,安国公另外在京城豪华地段为淳于沛买了院子,把房契给了淳于沛,淳于沛才答应搬出府去住。
傅冉云以尊重淳于沛正妻为由,没等傅冉云使出别的幺蛾子,就把傅冉云弄到庄子上去住,淳于沛无所谓。
日子平静地到了年底,腊月十八是淳于沛和聂曼君成亲的好日子,而傅冉云和淳于沛的丑闻也过去了一段日子,京城很少有人津津乐道淳于沛是个戴绿帽子的王八乌龟了,正好聂曼君为聂姑妈戴足了三年的孝。
喜宴是在安国公府办的,给足了淳于沛脸面。
成亲后的第二日,聂曼君给傅卿云奉茶,阴阳怪气地说道:“大嫂,傅姨娘是你的妹妹,住在庄子上不像话,还是早日接进府里来住罢,这样‘我们姐姐妹妹’一家人多亲热,你说,是也不是?”
傅卿云颦眉,聂曼君果然还是对此事有了芥蒂,正要开口,旁边的安国公重重地放下茶杯,沉声训斥道:“你怎么跟你大嫂说话的?嗯?”
聂曼君吃了一惊,缓缓地转过目光,随即清淡地移开,恭敬地福礼道:“是弟媳不对。”又顿了一下,她的肩膀小幅度颤动,哀哀地哭道:“嘤嘤嘤,大表哥,你以前从来不会跟我说重话,傅姨娘不知廉耻,难道我连讽刺几句的权利都没有了?我心里很难过……嘤嘤嘤……”
以前安国公懒得理她,根本就没跟她说过几句话,好罢?
这次不仅傅卿云皱眉,安国公也皱眉了,淳于嘉嫌弃地瞪了眼聂曼君,觉得聂曼君像个神经病,新婚的第二天就哭,谁家媳妇会这样?淳于蘅莫名其妙地盯着突然哭了的聂曼君,不知小脑袋瓜子想到了什么,他偷偷地把聂曼君刚给的红包塞进自个儿的荷包里,还用一只小手捂着,生怕被聂曼君抢回去了。
傅卿云看向淳于沛,淳于沛昨天喝得烂醉如泥,此刻正瘫坐在椅子里像是事不关己,傅卿云心生厌恶,所有的极品都集中到一家了,早早打发了他们,以后她在一旁看戏就是了。
于是,傅卿云索性顺着聂曼君的话说道:“二弟妹,你别哭了,新婚第二日哭不是好兆头。既然你这么想让傅……傅姨娘来,我今儿个就派人去接她,你们早日团聚,你也能有个说话谈心的姐妹,这样你就不会难过了罢?”
聂曼君傻傻地抬起眼望着傅卿云,晶莹的泪珠儿挂在睫毛上。
安国公握拳咳了一声,掩饰去唇边的笑意。
傅卿云喝了口茶,不等脑残的聂曼君想出反驳的话,接着噼里啪啦说道:“唉,看到你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是我思虑不周,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跟傅姨娘亲热了,这才没接她来。二弟妹是聂姑妈手把手教导出来的,管家也是能手,想来对家庭有自个儿的安排和期待,不像我这么漏洞百出。看到你这样思虑周全,贤惠大度,我很欣慰,可以放心地让你们住到外面去了。明儿个你们回门,我吩咐下人帮你们收拾行李,索性你的嫁妆还未拆封归库,就不拆了,直接送到新宅子里就是,后儿个直接就可以搬走了。”
聂曼君愣了好一会子才反应过来傅卿云的意思,她才进门一天,傅卿云就赶她走!
她嘴巴张开正要说什么,傅卿云便笑着又堵住了她的话头:“你既然没反驳,那就是同意了。昨儿个我招待了一天的客人有些累了,先回院子休息,你们小俩口也会去睡个回笼觉罢,这是自个儿的家,没必要拘束。”
说完,傅卿云朝安国公一点头,扶了扶郎的手出了景春堂,韩嬷嬷抱着回头好奇张望的淳于蘅跟在后面,淳于嘉忙不迭地趁机溜了,她可没心情看聂曼君的那一脸哭丧相。
聂曼君欲哭无泪,对上安国公的视线,乞求道:“大表哥,我……”
安国公起身说道:“我今儿个进宫有事,有什么话找你大嫂说。”说完也走了。
聂曼君回身质问道:“二表哥,我们为什么要搬出国公府?”
淳于沛懒懒地打个呵欠,轻蔑地说道:“聂姑妈在世的时候就说好了,我们成亲就会搬出国公府,她没告诉你么?”
聂姑妈死了,聂曼君跟着成了弃子,淳于沛怎么看怎么觉得聂曼君那张娇柔的脸是一副倒霉相,他哼了一声,出了国公府,直接去春晓别院,独留下聂曼君捧着受伤的心口蹲在景春堂哭泣,宁嬷嬷扶着聂曼君的胳膊温声安慰,在无人看见的角落,脸上却露出一丝诡异的笑意。
当天,傅卿云以马车坏了需要维修为由没有接回傅冉云。
第二天聂曼君回门,淳于沛一大早没了人影,安国公千方百计找到他,押着他送进聂家的大门。
第三天,傅卿云以强硬的姿态把淳于沛的行李和聂曼君的嫁妆装上马车送到新宅子。整个国公府在过去的两年里被傅卿云整顿得唯命是从,淳于沛曾经尝试收买,可惜都没有成功。所以,这次除了聂曼君陪嫁的人阻拦,其他人都在搬行李,但聂曼君陪嫁的那几人怎么拦得住整个国公府的下人?
聂曼君看见嫁妆都被运走了,当日聂姑妈交代过,可以丢了男人,但一定要守好嫁妆。聂曼君无法,只好抹着小眼泪坐上马车去追她的嫁妆了,到了新宅子一瞧,傅冉云已经拎着行李早她一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