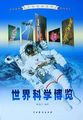萧鹰与王封仅仅在这里停留了七日,黎九也仅在此训练了七日。
从第三日开始,黎九便被独独拎了出来,增加了三倍的训练量,他终于也是一改轻松的姿态,与其他人一般每天累得瘫倒在床。
面对阿鸣三人的担忧与疑惑,黎九只是笑着摇头,阻止了他们要去和陈铜诉说不公的念头。他心里明白,这是萧鹰与王封对他的考验,为了目标,他必须坚持。
阿鸣三人也逐渐习惯了黎九的训练量。他们虽然识字不多,但看得出来,那些对他们来说天方夜谭的任务才能够将黎九逼到极限,而平时于他们而言只能勉力支持的训练对黎九来说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看着黎九双腿打颤,踉踉跄跄地掀开帐篷的帘子走进来,没走两步便滚倒在床。却也只躺了两个呼吸便艰难地翻身而起,将双腿掰至盘腿姿势,便闭上了眼睛,不多时,淡淡的红光在体表游走。他潮红的面庞也逐渐恢复了正常,而他的呼吸至始至终都是平稳的。
对于这一切,阿鸣三人都无法理解,正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陈大人独独把黎九挑出来一般。而一点明悟在心中浮现,黎九终究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
罗罗与邓子早早地就睡了,对于黎九,他们想不通,便也不必要去想,每天的训练量那么大,不紧着休息,难道还要每天想同样的无解的问题么?
阿鸣也躺下了,却经常看着打坐的黎九,一看就是许久,夜深才缓缓睡去。
黎九常打坐完毕,看着熟睡的三人,默默地钻入被窝之中。他和他们逐渐地远了,而他明白自己与他们之间的沟壑,这并非情感带来的疏远,而是彼此并非同类人时天然的分界。
道不同如何为谋?
他们出身小城小镇,参军以得荣养家锻炼,他们的道路多半就在这军中呈现,虽然辛苦,但也简单充实。而自己呢?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师父临死那焦急悲怆的眼神,那巨大阴森的骷髅头,还有月下的满河荷花与少女的面容。
这些都是他必须承受的。
尽管阿鸣三人的真诚情感对他来说颇为触动,但这小小少年心中早已经有了坚持的轮廓,他必将向那个方向前行。对于这份感情的短暂,他虽叹惋,却绝不会因此而停留。
只是,他想为他们留下些什么。
七天的时间一晃而过。
第八天的凌晨,天尚未蒙亮之时,三个人便从这边城悄然离开,三人的身影很快便没入了黑暗之中。
伴随着清晨铃声的响起,阿鸣三人便迅速从被窝里滚了出来,熟稔地将被子一抖,而三张纸张分别从被子上飘飞下来,落在褥子上。
他们见状都是一愕,却并不拖延,抓起自己床上的纸张便塞入怀中,迅速叠好被子冲出帐篷集合。
对于空荡荡的黎九的位置,他们习以为常,黎九向来比他们早出门,毕竟有特别的任务。而急着出门的三个少年却忽略了,这一次非但黎九不在,就连他的被褥也消失了。
休息时间,三个少年聚在一起打开了手中的纸张,都是一怔。上面画着几个小人,摆着各不相同的奇奇怪怪的姿势,一个又一个箭头将他们连在一起。纸张底端写着一字“九”——黎九初来之时教过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奈何他们嫌“黎”字复杂难学,最后只习得一个“九”。
他们对比着相互的纸张,每张纸上面画的小人儿姿势也不同。
“这应该是阿九给我们的吧?”阿鸣翻过纸张背面,见空空如也,又看回正面,挠了挠头,“这些姿势是什么意思呢?”
“箭头应该是顺序,这些姿势……我曾和阿爹一起出去的时候看到武馆的人练习,摆的姿势和这个有点像。”邓子说道。
罗罗若有所思:“难道是阿九给我们练武功的方法?”
“是了。”阿鸣兴奋地一击手掌,引来罗罗和邓子的注目,他双眼发光,“我之前不就说了么,阿九每天打坐身上又有红光,实在很像以前说书先生说的那些个武林高手。”
他们每天都聚在一起,少不了聊天,也少不了聊聊黎九的神秘行径。
“他一个小孩子,做得什么武林高手。”罗罗嗤笑一声,仔细看着纸张,“不过确实像练武的姿势。”
“回去问问阿九不就知道了么。”邓子大咧咧地道。
而三人夜晚回去,终是发现了已经空空如也的黎九的位置,他们奔去询问长官,却得知黎九已经离开。
一时之间,三人都是猝不及防,又怅然若失,只看着手中纸张久久无语。
而此时的黎九早已经跟着萧鹰二人踏上了去往京城的路。
恒平城位于雍朝的最东南端,即使以雍朝较为便利的交通道路,要抵达雍朝中部偏北方的京城即便快马加鞭也要走上半年之久,而这是指的陆路。恒平城径直向北过往两个城市,到豫州的南江城,便可见到一条大江,名为太江。太江一端从西北的回州山脉流出,半绕京城,一端直通东部海洋,中间贯穿三个繁华的大城市,是一条极繁荣的运河。
萧鹰便定了这条路线,穿过两个城市,沿运河抵达京城。王封并无异议,黎九却疑惑了,走陆上直线尚且要半年,如此绕弯子岂不是更加费时?
途中在一间酒肆坐下休息时,黎九提出了这个疑问。此时他们才到达恒平城的最北端,在出城之前暂且恢复一下体力。
萧鹰一如既往地沉默不语,王封两指捏起酒杯,将酒液一饮而尽,这才对黎九说道:“你这个想法是没错的。但我们这京城却不可以常理度之。我实话告诉你,此番绕路,约莫三个月能抵达京城。”
黎九更加疑惑了,为何绕路却更省时间?
王封没有立即解答,而是连饮下两口酒,随后看着黎九道:“你想一想,什么样的状况会导致这种情况?”
“这说明走直线会比绕路更加困难。出入城池的关键在于手令,这对你们来说却不是什么难事。应该是官府之外的缘故。”黎九思索道,“除非有漠视官府的难缠势力,或者地形缘故。我只能想到这两个了。”
当初与师父奔逃期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各种地形。那些艰险的山崖又或者茂密的丛林,都很难通行,这也为他们提供了藏身之处。
王封赞许地点了点头:“就是这两个,不过主要是地形。”他不再卖关子,将酒杯摆在黎九面前,道:“假设这个是京城,周围的是其他城市。”他碟子里的花生米略抓了一把,洒在酒杯的周围,比作城市。
“按说通过这些城市可以直接抵达京城,但我雍朝的京城周围地势险峻,是一道天险。连绵丛山不绝,陡峭异常;中间千沟万壑,最深的一处沟壑深不见底,无人敢于探测,坠落者永不复回。这天险直接将京城与众多其他城市隔绝开来,去到天险附近耗时毕竟不算太长,但穿行却十分困难。且不说找不到路线,即使熟知路线也要谨慎万分,里面实在是凶险得很。”
黎九一惊,未曾想京城的地势竟如此神奇。
“而绕路走运河,是最便捷的路了。京城三面被峻岭包围,独独留下一条通道,那便是运河。这是常人能前往京城的唯一道路。”王封缓缓地说道。
“如此,消息传至京城岂不是很不方便?若只通过运河这一条路,岂非很容易被截取?”黎九皱眉道,“为什么要把京城设立在这么一个地方呢?”
萧鹰瞥了他一眼,这小子反应倒是不慢。
王封闻言笑了,笑容中掺杂着几分神秘,他压低声音道:“消息的传递,你入了萧家军就明白了。至于京城的缘由我倒是可以与你讲述一二。”
“这就与历史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