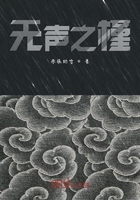却说韩林胃口大开,放开肚皮一顿胡吃海喝,自从误服仙果后,韩林胃口便大了好多,这满满一桌子菜,吃了个一干二净。要说此间菜肴,做的真是精致鲜美,美味可口,色香味俱全,鱼肉鲜美,入口即化,浓汤香醇,回味悠长,韩林以前何曾吃过,吃相不免难看了一些。
待吴奇兴回来,身后跟了一个三十许的中年人,跟吴奇兴有七八分相像,看到此番景象,心中不屑,越发认定韩林是骗吃骗喝之辈。吴奇兴心直口快,惊讶道:“韩贤弟真是异人也,竟然一人能吃如此多饭菜。哦哟,海量海量!”却是他见到歪倒在窗边的三个空酒坛。越发觉得韩林不凡。
只听那跟吴奇兴有七八分相像的中年人冷言道:“这位小兄弟倒是肚大。不知祖籍何处啊?家中可有老小,吴某可赠千两路费,以供小兄弟支用。”
韩林心道:倒是个冷脸儿的,当面直接撵人,这要是个脸皮薄的,恐怕就受不住面子拂袖走了。当下嘿嘿一笑,顺杆儿爬,道:“不劳兄长费心,小弟,居无定所,与二哥一见如故,方才听闻,二哥府上多是些能人异士,心中忍不住欢喜,想到二哥府上叨扰一番。”
“哼。谁是你兄长!”那中年人见是个没脸没皮的,当下冷哼一声,拂袖离去。
吴奇兴为人宽厚,见闹得这般尴尬,忙施礼赔罪,诚恳道:“贤弟,勿怪,勿怪,我这兄长也是个面冷心热之人,并无撵你走之意。对了,听闻,贤弟决定要来我府上,见识诸位豪杰?贤弟,酒饭足否?不如我们这便回府?”
韩林自无不可,两人上了马车,吱呀吱呀的驶向城外。韩林惊讶中,听吴奇兴解释,城内人烟混杂,不利于修行,便把外府开在城外火云山下。
来到这处外府,韩林始觉吴氏之财雄势大,这片庄园连绵起伏,不下数千亩,几乎覆盖了整片山麓。景色空悠,小河蜿蜒,竹林清风,雾霭飘拂,好一派田园风光啊。韩林一眼看去便喜欢上了这里。
当下,吴奇兴便把韩林安置在一处环境清幽的小院内,此地背靠青山,一条小石路穿过清幽竹林,通往远处的主宅大院,院子背后还有一条小溪蜿蜒流过,注入濉河支流。环境清雅,景色宜人,更难得的是偏僻清幽,无人打扰。
于是韩林就在此地住了下来。当夜,吴奇兴大摆筵席,宴请众宾客,替新来豪杰接风洗尘,原来,除了韩林,还有三名豪杰也在这几日间前来投奔。期间,不少僧道佛尼,各显殊异,互相抨击辩论,你踩我我踩你,争风吃醋的好不热闹。
最惹人注目的当属一僧一道一儒一尼姑。当先一肥头大耳胖和尚,笑眯眯,开口闭口,尽是些似是而非,闻之欲醉的禅机佛理,听得韩林云山雾罩。
而那长眉老道,白发皓首,看起来颇似有道高人,只是听他开口,众人便心里咯噔一下,心说,这老贼割肉好狠!只听他慢声慢气的言语道:“贫道,新来感悟,欲炼制一丸丹药,须得黄金千两,明珠百颗。万望二公子鼎力支持,若得仙丹,服之,可飞天遁地,一圆二公子之仙梦。”
那儒士笑而不语,风度翩翩的样子,倒是那冷面尼姑,丝毫不给老道面子,讥讽道:“秋云道长,前些日子,不也要炼丹,才支取了数百两黄金、两支玉如意、一箱宝珠,仙丹还没出来,这便又要炼丹啦?”
那老道城府深,不动声色,仿佛对尼姑的讽刺,毫不挂心,只淡淡回道:“只因,时节不对,缺了至关重要的一道药,便功亏一篑,每每思及,老道也时常觉得愧对主家。”那胖和尚不乐大师笑呵呵的打圆场。
吴奇兴见手下宾客又生龌龊,忙表示些许钱财,都是求道必须,心诚则灵,所有宾客,一应支取。当下宴席展开,介绍新来的豪杰与他人认识。其他人见韩林不过是一个弱冠少年,便生轻视之心,韩林只笑眯眯装作天真懵懂状。如此这般三四个月过去了。
韩林来到此间已数月有余,今天,恰好闲来有暇,跑来听这些人胡吹乱侃。这帮人,终日不事生产,只是吃喝耍乐,争相在吴奇兴面前展示妙法。辩论道法禅机,听来听去,尽是些老生常谈,开始的时候,韩林对这些千奇百怪,闻所未闻的鬼异杂谈,听得津津有味,着实大开了眼界。日子一久,发现翻来覆去,说的就那两三件事儿,翻过来覆过去的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听得韩林都能倒背如流了,只觉得满心乏味,而且细细品味,品出不少言语漏洞。嘿嘿,越发觉得这群人夸夸其谈了,来此数月,也不见过丝毫仙家妙法。倒是跟着他们耳濡目染的学会了辨识不少那种古体繁写小篆。
这一日,听闻堂中新来了的一个和尚,慈眉善目,宝相庄严,一派高僧的模样,宏声宣讲,血道神胎的手段。只听这厮说:“……如此这般,精选上品肉身,用灵药浇灌,仙草喂养,待养熟了,便抽取血肉精魂,熔炼成血道神胎,可增寿元百年,肉身强悍。刀枪不入。”
听得众人眉头直皱,当下感觉到自己地位受到威胁的不乐大师,愤然勃发,做佛门狮子吼状,怒斥此人宣扬邪法,乃邪魔妖道,要主人家赶出去。不少依附于他的宾客也都摇旗呐喊,一片喊打喊杀之声。
韩林听得有趣,虽说此法邪恶,但乃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讲出具体法门的宾客了。倒是斜歪在墙角似假寐状的老头子,似模似样的点头道:“就这家伙还略懂几分法术,可惜是害人的邪法,这血肉神胎看起来美好,实则遗患无穷,此法炼制起来极其残忍,有伤天和,服用神胎之人,虽得百十年寿元,却也不过是苟延残喘,修为难以寸进,道根尽毁,此生仙道无望,若此生未渡过劫难,这种种因果甚至会纠缠到来世,不得安宁。自此,天劫难度,遗患无穷。”言罢摇头不语。
其实此老也是道听途说,他都尚未入道,如何知道的这么清楚,不过是从小听他师傅唠叨,耳濡目染,知道了一些罢了。即便如此,可是韩林对此一无所知啊,只觉得此老深不可测,言之凿凿,合情合理,自己受益良多,听得如痴如醉。
因此便心生亲近之感,主动与他结交。常跟着他跑前跑后,渐渐明白了此老的尴尬。
原来,这老者唤作花子苗,来府中五六年之久了,初来之时,意态狂傲,贬斥这个,驳论那个,骂他们都是坑蒙拐骗之辈,这可了不得,断人家财路啊,你不坑,你不蒙,你来这干啥?大家都是一路货色,你还想吃独食儿?
当即犯了众怒,群起而攻之,他死不悔改,每次听那些人夸夸其谈,胡吹乱造,就气得吹胡子瞪眼,偏生口才不好,身手也不咋地,说也不过人,打也打不过人,每次都闹笑话,久而久之,大家就都当他是一老疯子,没事拿他逗乐子,而能言善辩之士,更乐于拿他当踏脚石,向主家展示一番道法精湛,以期获得主人家赏识。
如此一来,老头在府里混的就很不好,韩林见到他时,浑身脏兮兮,邋里邋遢,沉默寡言的样子,磕磕巴巴不善交流,每逢府中大摆筵席,坐而论道,便被那些夸夸其谈、口绽莲花之辈驳斥的体无完肤,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他一急,越发结巴了,引得主人家不喜。若非为了维护礼贤下士的好名头,早被赶出府中了,不过吴家家大业大,也不在乎这老头一口饭吃,于是便留在府中。
韩林看他可怜,便时常跟他聊天,也不与外面那些人深交。老头因此看韩林很顺眼,尤其是韩林说那些和尚道士吹的云山雾罩,天花乱坠,却不见丝毫佛光妙法,只知道夸夸其谈,听一听就罢了,谁还真信啊,谁信谁傻子。
老头听了大感知音,经常弄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教韩林瞎鼓捣。老头对于繁写古体篆文,极为精通,很多《火元经》中的偏僻怪字,他都认识。还能举一反三,说出很多道道。韩林对他颇为信服。之前,韩林问遍府中宾客,要么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要么,云山雾罩,瞎说一通,要么,就干脆驳斥韩林写错了。韩林自然知道不可能错,是这些人水平不行罢了。
从那以后,韩林就不太跟那些人交流了,而吴奇兴也忙于应付群豪,一个月里也跟韩林说不上几句话。韩林则乐的清闲,没事儿就跟花子苗闲聊,听他胡吹海侃。至于他说的那些,飞天遁地,餐风饮露,韩林是表示怀疑的。
这一日,韩林路过主宅去找花子苗聊天。走到一片灌木旁,听到对面有人声传出,原来是吴奇兴的兄长又来与他抱怨,府内宾客花费太大,昨夜那秋云道长卷了数千两黄金,一箱南珠不辞而别。吴奇兴不悦道:“道长留书说要云游天下,寻找仙草,为我炼丹嘛,他都留书作别了,怎得能叫不辞而别呢?”
韩林听的眉头直皱,留书作别,是因为他以后花没了钱,还能再回来。为了留条后路,吴奇兴不傻,他会看不出来?恐怕是不愿意相信罢了。
吴奇兴的确不傻,相反他人品俊雅,文采风流,出口成章,却偏生对求仙问道,已成疯魔。家里一门心思让他读书科考,他狡辩道:“功名利禄,财宝佳人,于我而言皆如浮云,不得长生,终究虚妄,凡人一世不过百年,恍如白驹过隙,匆匆而逝,红颜易老,白发渐生,百年一过,化为一抷黄土,管你绝世英雄,倾城佳人,皆是如此。兄长,不要痴迷于庸庸碌碌的科考,粪土般的金银,来跟我一起求仙问道,我们御剑云霄,逍遥自在,焚香抚琴,把酒临风,岂不快哉?”
他兄长气得浑身发抖,挥袖怒道:“没有这些在你眼中如粪土般的金银,你以为你府中这些宾客还跟你在这胡吹海侃的瞎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