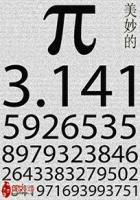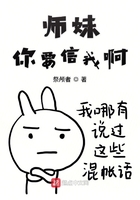女佣端茶进来,“夫人很快就来了。”语罢离去。
喝了口茶,我走到书册林立的书架前。
书架上的书跟我原本预期应有的书差不多。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作家的精装全集一应俱全。其它大部分则是伏尔泰与雨果的作品。
正在读着书皮上的文字时,夫人出现了。
再度见到了那谜样的双眼。再度在那名女子的眼中看到向谁倾诉般、与嘴里所吐出的简单词汇相矛盾的神情。看着这般光景的同时,顿然领悟自己的前来不是被高乃依或拉辛所吸引,而是为了那双眼睛。
对于自己与夫人进行的对话,我已然毫无记忆。记忆的消失肯定是因为不曾在这方面耗费过脑力。不过妙的是,脑海却一点也不空虚。虽然忘了对话,却仍然记得只言片语。更贴切地说,忘得了言语,却忘不了那声响。那声响如同几个单字紧贴在耳根一般,不断地发出声音。
记忆里唯一的内容是夫人的举动。脑海里全是她身体的律动。为何能够伫立,为何能够端坐,为何纤纤玉手能动也不动地、几乎象征性地合在膝头上,既是如此,为何那同一双玉手又能够敏捷地取来女佣端来的红茶,然后又递回去。
声响与律动的记忆,虽然在顺序上不甚明确,却清清楚楚地残留在脑海里。
这儿有件事颇怪。自己是记得夫人身体的律动的,然而对其静止的状态相当地朦胧模糊。即便只是那张美丽的脸蛋,也非靠形状,而是靠表情烙印在记忆里。对那双眼睛也一样。在故乡时,曾被某个老伯问道:“牛的牛角与耳朵是哪个在上,哪个在下地贴在一起呢?”这么简单的问题连我也明白,马上答了出来。老伯便道:“不是很多人都能像你一样马上就知道的。”看来,每个人对于形体上的记忆都是十分缺乏的,不是单单对女人的脸而已。
对于夫人的穿着又记得多少?自己对这个实在没把握,相反地,记忆却追溯起夫人的话语。自己无意间看到夫人的短外褂,夫人便道:“很怪吧!上了年纪还穿得这么花哨,我把以前的外出服拿来当做便服穿了。”听到这番话,始觉了然。其实自己从不觉得过于华丽,甚至总认为,世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能比和服上的美丽色彩更能和夫人的美貌相互调合的了。
又开始拐弯抹角了,真懦弱。
打开弃之已久的日记,执起笔,我到底所为何事?难道不是为了写下自己的阅历?为何自己有勇气去做,却没勇气写?还是并非真的有勇气做,而是不得已擅自做主?这样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跑出根岸大宅的铁门时觉得热血沸腾,还有种不明的舒畅感,一种精气十足感。那时的自己与平常的自己是两回事。平时的自己与当时的状态相比,甚至还有种血脉中流动着冷血动物血液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