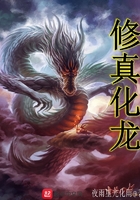红玉听了甲乌的大叫,嘴角扯起邪魅的笑,眼中黑红交替涌动,原本束着的长发竟然无风而舞,骇人得很。
午后的阳光有些烈,照在她几欲变形的脸上,反增添了些狠毒冷绝。
她冰冷着脸,抬起手祭出一柄雪亮的宝剑,纵身就向连城攻了过来,剑气凌锐,杀意翻飞。连城,你杀我父亲,我必要你为他偿命。
已生心魔的连城岂会把这点小把戏放在眼里,想他万年修炼,岂是她一届小小女子可以挑衅的。稍运了灵力广袖一挥,红玉便如断了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
连城生来便是太子之尊,万年潜心修炼,修为不是一般的深厚,只不过他不喜杀戮很少动手罢了。如今他这酝酿了满腔怒意的一挥,生生将个红玉威压得口吐鲜血、神智昏沌,犹如一只破碎的布偶,只在地上痛苦痉挛。
对不起,父亲,此生是女儿害了您,来生,女儿定会好好听您的话,好好侍奉您,此生再见了。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头看向那道玄火,父亲早已魂灵俱灭,一丝痕迹也没留下。
身体的痛苦远不如心痛来得锥心蚀骨,她终是无力支撑,复摔于地面,头与地面相触,发出声慑人的闷响。
她缓缓地将自己翻过身来,面对着天空,目光空洞而无神,连城轻描淡写的一挥,将她整个人都击垮了。
看,天空还是那么蓝,云还是那么白,窜入鼻中的花香还是那么浓郁,但也许以后都再也看不见了吧。
红玉在最后一瞬,心生无限悔意,如果没有连城,是不是她会和父母在一起过快乐自在的日子,便不会受此锥心之痛呢?如果她听了父亲的话,好好的寻个人家嫁了,而不是痴心于妖王,是不是一切便会安然如初呢。
然,世事没有如果,只有因果。
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将于今日终止了,悔又如何,恨亦不能如何,不如算了吧。
连城,此生错爱是我,但愿来生不再相见。
自古多情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
可我如今方醒,还是太晚了。
红玉心如死灰,终是痴心错付,悔之晚矣。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她在意识丧失前的最后一丝清醒里,耳边传来一个清冷狠戾的声音“护法府众,一个不留。”
是连城!红玉在心中模糊的想,母亲向来温婉与世无争,你竟也不放过,何其狠心。纵我红玉有错该死,有父亲相陪不够吗?母亲何辜!府众何辜!你竟要我全府性命,何其冷酷。
罢了,终是我有错在先。
我要归去,我要归去!
连城以壮士断腕般的果决诛了护法全府,其狠戾冷酷的作风震憾了整个妖族。一时间,妖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无人敢拭其锋芒,妖界的法令律例空前绝后地执行得纯粹而彻底。就连从前一直不肯归顺妖界的巨蟒一族,也闻风而动,北面称臣。连城的权威史无前例地达到至尊顶峰。
此时的妖族王上连城,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了一名冷冽狠戾的王者,仿佛一柄刚刚出鞘的利刃,触之必伤、忤之必亡。
却说那天族太子燧凤,只差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啊,就可抓住离生的手,免她跌入送仙台。哪怕他再快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就可以继续和离生在这天界的安然日子,然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哪怕。
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留在身边相伴几日的离生以这种离奇的方式再次离开他,燧凤有些崩溃了。
此前不在身边,自己最起码知道她在哪儿,天上地下寻着气息去找就是了,后来有了冰刃,找到她就更如同探囊取物。
可如今,她从那送仙台下去了,必会被掩了记忆和灵力,没有了昔日气息,这六界八荒,要到哪里去找才好啊,自已努力得来的一切,在父母的糊涂干预下,又回到了起点。
火神殿下憋气地仰天长叹。
此时的他异常怨念他那多事的父母。你说好好的,干吗就非得来这逼婚一出儿啊。如没你们擅自唱的这出儿,那自己就能陪着她好好地去送共融一程,离生也不会跌入那无法逆转的送仙台。
再说,同时跌下的还有那紫冰仙子。但凡天界仙子下凡,都必有上神圣谕,且必得有上生星君依据圣谕所述、拟好性别、生辰、家势、运道、年限等具体条陈方可。这紫冰此番一无所有的被推下去了,究竟运道如何、还回不回得了天界啊。
燧凤觉得头痛无比、脑中一团乱麻。本来一个上神历劫而已,个把月就回来了。现在倒好,搭了两个下去陪着的。离生还好些,毕竟不属这天界,虽然下世会受点辛苦,但保不齐哪个机缘巧合就恢复原身了。可这个紫冰究竟是天族中人,无令自行去了下界,成了凡人,万一没能与那水神相遇,那得猴年马月才能回归仙位啊。如若不回归,那自己又将如何与那月老交待啊,一想到那月老可能因丢失了紫冰仙子而发作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他的头痛得越发剧烈。
头痛欲裂的火神殿下只好偷偷和天帝天后禀明此事,一番讨论、争论、辩论后,燧凤自请下界,去寻找不知所踪的离生和紫冰仙子,将她们带回来,重续仙缘。
自此,火神燧凤开始了新一轮的漫漫寻妻之路。
前路漫漫,未有归期。
梁国国都抚风城有个柳家,世代从商,家底殷实,就是人丁不旺,传到这一代,仅有一个女儿,百万家财不知将归于何人之手。
柳家老夫妻俩中年得女,宠爱非常,却不幸在柳家独女柳如是十七岁那年,身染重疾、双双驾鹤西去,只把一个女娃留了下来掌管整个柳家。
虽说这女娃芳龄十七,但因甚少外出,见过她的人是少之又少。外界只听府内丫头说那小姐生得是天香国色、文武双全,直把个柳家经营得有声有色、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纷纷好奇的很。
十七岁的女娃早已到了议亲的年龄,身负家财万贯,又传言貌美无双,柳家小姐柳如是几乎顷刻间成了京城权贵公子们争相求娶的对象,王公贵胄们纷纷托了媒婆上门提亲,各种名贵礼物流水似的送入柳家大门,无形中将柳家的财富又往上堆了一堆。
这其中就有个当朝相国林元的独生公子林中歌,据说曾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墙头目睹了柳如是的天人之姿,从此坠入情网一发不可收拾,那叫一个日思夜想、昼夜相思啊,生生将人想瘦了几圈儿。
话说这林中歌林公子,生得简直是色冠京城、风流倜傥,在京城四大高富帅中名列第二,缀号倾城公子,容貌倾城之意,但也有人称他为二公子。
如此人才招得多少京城豪门女子倾慕爱戴呀,哭着喊着哪怕给他做个妾室也心满足意足。可惜这林公子眼高于顶,愣是一个也看不上,还振振有词地将这些恨不能整日介贴在他身上的痴情女子说成庸脂俗粉、俗不可耐。
老相国本以为这矫情的儿子怕是此生难得娶上媳妇儿,都要从旁支过继个孙子了,哪想如今这清高的儿子有了心仪之人,也算林家后嗣有望了,这诚然是件好事儿,身为父亲,无论如何也得帮衬帮衬才对。
虽说这柳家小姐乃商贾出身,钱财颇丰,但与相国家的门槛儿相比,实是门不当户不对。奈何人家有钱啊,更主要是儿子看上了,这便把门户之见的门槛生生给压低了。
林公子一副非柳如是不娶的痴情姿态,茶饭不思、一日比一日更加清减。
相国心疼儿子因相思把自己弄得人比黄花瘦,且这柳小姐财色两全实为京中贵族的抢手人选,还需先下手为强。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相国着急巴火地着人托了京城最有名望的李媒婆择了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去柳府提亲了。
李媒婆一身鲜红的衣装、摇着蒲扇走头里,后面跟着一长溜抬着贵重聘礼的府丁。别提心里多得意了,这是她的媒婆生涯中,第一次给这么高的门院儿办事,光说那赏钱就够她花用一年的了,想到这,将那蒲扇挡住血红大口,更是笑得猥琐得意。
来到柳府门前,李媒婆亲自上去将门拍得啪啪作响,却无人来应。不由怒意横生,好你个柳府,竟敢如此怠慢于我,看我不回了林相国,胆敢藐视夫家,以后你嫁过去自有你的好果子吃,眼下先不与你理会,成就好事才是真。
敲了足有半盏茶的功夫,柳府的门才从里面打开。一位生得皮白大眼的年轻男子不耐烦地看着她“又来提亲?不允。我家小姐年纪尚小,不劳费心,请回吧。一天来八十趟又被赶出去八十趟,还来,烦不烦”。
说罢就欲甩门回转,然李媒婆何许人也,那是在捧高踩低、呼来呵去、冷言冷语中挣扎出线的媒婆界灵魂人物,岂能被这么一个年轻男子轻易给赶出去呀。
再说,自己今天这可是代表相国府,就是自己不要脸了,也不能丢了相国的脸呐,否则自已还如何在这京城媒婆行业中混饭吃啊。
李媒婆有了相国府这个靠山,自是不把柳家看在眼里了,生生忘了自已此前来过多次是如何的低三下四、低眉顺眼,此时闻听开门人的话,粗腰一扭,香扇一摆,“哟,青管家,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今天我可是受林相国所托前来提亲的,聘礼都直接带来了。任你柳家小姐如何美貌如花,嫁得林家公子也是她祖上积了德的缘故。快快让开,待我进去亲自与柳小姐详谈。”
开门的这位叫青铜,是柳府的管家,听说是个钢铁直男,一根筋地就只听柳小姐的话,谁也憾动不了,凭一已之力硬是将这柳府大门守得滴水不漏、密不透风,十七年来,柳家愣是连个贼都没招过。
可就是这么个优秀得无与伦比的管家,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能文能武,进得厅堂也下得厨房,却心甘情愿地携如花美眷、子女成群地固守着柳家,那叫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话说这李媒婆一番没轻没重、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话一出口,青铜即刻怒了,也不答话,只从门后拿出一柄硕大的扫帚,披头盖脸地就往她身上拍。丫的李媒婆,不想要命了是咋地,敢这么说我家主人,你也配。我家主人连天族太子都不嫁,你一破相国在我这炫耀个毛线啊。就不允,看你能奈我何。越想越气,越气这手上便越发没个准头,只把个扫帚拍得虎虎生风,披头盖脸,毫不留情。李媒婆本是个胖得看不出腰形的泼辣女子,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灵活地躲着从各个刁钻角度拍过来的扫帚,然终是受了一身肥肉所累,不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发乱衣皱。终是体力不支,被一扫帚拍倒在地,杀猪一样嚎叫,且这叫声颇具穿透力,直把这一条街的人都给唤来了。
众人转成圈地站着指指点点的看热闹,却没有一人前来相劝。这柳家很是仁善,没少帮街坊邻居的忙,所以吧,大家伙很是敬重柳家。但李媒婆没这待遇呀,她一张破嘴说和这家说那家的,误了多少痴男怨女情无归处啊。所以,有了她的热闹,大伙是不看白不看。更有甚者,还特地去小摊上买了两把瓜子,按这李媒婆胡搅蛮缠、装疯卖傻的战斗力,没有一个时辰这事完不了,边吃边看才是最自在呀。
只可惜威名在外的柳家大管家青铜根本不给众人机会,一顿神拍将这李媒婆拍出柳家大门范围后,咣啷一声将大门合上,临去前只留下一句“再敢来,看爷不打断你的狗腿。”
李媒婆等着大门合严了,噌地从地上窜起来,一蹦三尺高地跳脚撒泼,奈何柳府大门严丝合缝,根本没人搭理她。周围嘲笑她的人声愈发大了起来,只好摸摸鼻子,讪讪地带着她身后那一众人等按原路折回了堂堂相国府。
来时趾高气昂、不可一世,回时灰头土脸、丧打油魂。这可如何是好,把个相国府的事情给办砸了,老相国不会拆了我的骨头吧,李媒婆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觉胆颤心惊、双腿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