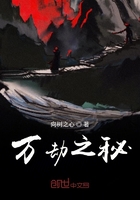少年吓的不轻,昏了三日,期间澹台倒是来过一次,但远远瞥了一眼便离去了。
将军的心思一向猜不透。
没几日,军营中来了些不速之客。
泽海匆匆赶来,“将军,六扇门的人来了。”
澹台皱了皱眉,“他们办事的效率倒是快。”
军中有纪律,并非是不能处置士兵,而是有人存心找茬。
“段捕头,什么风儿,把您吹到我这小小的军营来了。”
段捕头也是人精,“澹台副将,别怪我这不请自来,实在是皇上由命,我这个当差的,不得不听啊。”
澹台木兰也不掩饰,冷哼道,“看来,本帅这位置坐的,让大人不是那么的舒心啊。”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若说没别的心思,才有鬼。
“哟,副将,您这话说的,怎么会呢?我就是例行差事,例行差事罢了。”段捕头笑眯眯的回道。
正所谓,笑嘻嘻,笑眯眯,不是好东西,说的就是这段无怅,曹旭麾下的人,有着汴京第一捕快的称号,但这里头儿有多少水分,那就不得而知了。
“来人啊,好好查一下,免得有人故意抹黑副将,我们也不好交代。”段无怅指挥底下的人去查,也不知查些什么,自己又是笑着对澹台说,“实在不好意思,这皇上的指令,您不会不听吧?”
“段捕头一口一个皇上,这是要拿皇上压本帅啊,但是本帅也是讲理的人,劳烦捕头将皇上的圣旨拿出来,也好让我这一众将士安心啊。”
“不急不急,等查完了,自会副将。”段无怅找了一个歇脚的地方,悠闲的靠了起来。
“哼。那本帅就静候佳音了。”
她心中自有怨气,但不得发作,得受着,毕竟若真是皇上的旨意,容易犯个冲撞之罪。
月如勾。
到底说是个偌大的漠北军,纵使段无怅这次带足了人手,也查到了半夜。
一名手下在他身边摇摇头,“大人,没有。”
“怎么可能?”段无怅一下起了身,发现澹台还杵在那盯着自己,一改愁容,换上笑脸,“啊哈哈哈哈,今日真是劳烦澹台将军配合了,”
“既然,段捕头,查完了,那这圣旨是不是该给本帅看看了?”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不过啊,这是皇上口谕,所以早在先前,副将已经看过了。”
噌!
顿时剑拔弩张。
“你在糊弄将军,该当何罪?”泽海护主心切。
段无怅笑了笑,摆手示意身后众人放下刀。
澹台也是开口,“放下。”
“可是将军,他......”泽海心有不甘。
“本帅说,放下!”
澹台表面上是道歉,但实则是责问,“手下人不懂事,段捕头应该不会计较,就是本帅有些好奇,捕头到底是在找些什么?总得给本帅一个交代吧。”
“不过是皇上丢了个心爱的小玩意儿,有人说朝将军这来了,这才打扰了,不打紧。”
“哦?”澹台有些疑惑。
“行了,也不打扰了将军了,这嫌疑洗清了,我也该走了。收队。”
“不送。”
走到一半的段无怅突然回头,“对了,澹台副将,您平日里还是好生看着点自家的狗,这要是咬了人不打紧,但若是一个不小心让人给咬了,那可就不好了。”说完大笑着离去。
“你!”泽海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泄。
一场小闹剧便这么过去。
-------------------------------------
“我是你大哥,你得听我的。”看着面前黝黑的熟悉面孔,少年第一次没有反驳,“好,你是大哥,我听你的,都听你的。”
沈流舒不知自己昏了多久,只觉着头疼的厉害,醒来时已是入夜。
西风的夜不同别处,虽名字里带着个风,却鲜少有风。
“感觉怎么样?头还昏吗?”说话的是大头,这人倒是这军营中唯一对他好的了。
少年直起身子,“还行,就是一想起来觉着恶心,反胃。”
“你这都算不错了,还记得我当年第一次见血的时候整整吐了三天,两腿不住的打颤。”
少年知道他是安慰自己,这大头是个可以交心的人。
“行了,既然你没事我就先走了,要是饿的话那有馒头。”
翌日
段无怅独身一人又来了军营。
“段捕头,这次又玩的是什么花样?还是说你觉得我漠北军好欺负了!”澹台木兰满心怨气,上次已经是强忍着不发作,不曾想这才几日他还敢来。
段无怅仍旧是一脸笑意,“澹台副将,别这么大火气嘛,女人总发那么大火容易月事不调,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副将大人。”
最后几个字阴阳怪气,惹的澹台又是一阵不快。
“这次本官是带着圣旨来的。”
澹台木兰不傻,上过一次当又岂会上第二次,“段捕头还是不要再拿用过的花招来的好,上次本帅还能拦着,这次就不知道拦不拦得住了。”
段无怅不恼,从怀里取出一张黄纸。
“以为这次换了一张黄纸就能唬住本帅了,段捕头,您是不是太天真了些?”
“副将还是看看的好。”段无怅吹起了口哨。
澹台木兰接过黄纸,轻轻扫了一眼,攥紧的右手又松了开来,整个人有些无力,唤来泽海,“泽海,你带段大人下去歇息。”
泽海领命,故意将大人二字念的极为重,咬牙切齿道,“请吧,段大人。”
段无怅笑意更浓,“那就有劳泽海兄弟前面带路了。”
澹台木兰的营帐在西角,比一般的毛坯房好不得多少,顶多是一个人住,敞亮些。
“将军,属下有一事不明,还请将军指教。”泽海半跪在地,双手抱拳。
“所谓茶道是极其精致的事,上到润,熏,下至沏,品,每一步都马虎不得。”澹台木兰沉浸茶道是自遇见他起的,“泽海,一来品一品这新的贡芽如何?”
泽海不敢反驳,只得小心接过茶盏,一饮而尽,“将军,属下......”
“我记着你今年已二十有三了吧?”
“回禀将军,属下再过几月确实廿三了。”
“不曾婚娶?”
“不曾?”泽海回答的很干脆,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我母亲何氏家的大姨娘有一幺女,岁十九,虽年纪是稍大了些,但胜在举止得体,样貌随了她娘亲,算个美人,琴棋书画也是精通,至今未曾许人家,我觉着配你正正好,你意下如何?”
将军的心思一向让人猜不透。
泽海仍旧半跪着,“承蒙将军照顾,但泽海早已心有所属。”
澹台给自己也沏了一杯茶,置在一边,“那倒是可惜了,原本还可亲上加亲,往后除了喊我将军,私底下还能叫声表姐。”
“泽海以为,我的心思已经很明显了。”
“可是你知道的,那个女人的心里只有那个男人。”
泽海站起身,神情有些激动,“泽海愿意等,泽海愿意等到她死心。”
澹台抿了一口茶,“这茶的火候属实是差了些。”
“将军。”
“退下吧,本帅乏了。”
泽海欲言又止,顿了顿,抱拳道,“属下告退。”
出了营帐的泽海觉着有些冷,下意识的紧了紧身子,听到一旁巡逻的士兵议论,“真是奇了怪了,怎么今儿个还起风了。”
是啊,怎么还起风了。
他的思绪随着风仿佛落在了那个午后。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她,不过三四岁,话都说不清楚,就因为他不小心撞掉了她的棉糖,竟能追着他半个院子。
明明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糯米团子,却偏偏要举着肉肉的手,装出一幅凶横的模样警告他,离她的糖远些。
想到这居然没缘由的笑了。
侍卫甲:“你不是说泽海被将军骂了吗?怎么还在这傻笑。”
侍卫乙:“许是被骂惨了,受刺激了。”
侍卫丙:“有道理,有道理,那我们就装作没看见吧。”
三人一致赞同。
-------------------------------------
一大清早段无怅就来到了澹台的营帐,十分热情,“澹台副将昨日睡的可好?本官是睡的不错啊,可真是得多些副将的款待了。”
“款待说不上。”澹台有早起喝茶的习惯,“不过倒是段大人这么早来我这营帐,有何贵干?”
段无怅倒是会自来熟,坐在了一旁,拿起新泡好的茶水就喝,“澹台副将不要板着个脸嘛,素问漠北军骁勇善战,今日闲来无事,想着不知能否有幸一睹这漠北军的风采?”
澹台不想过多纠结这些琐事,虽不知他的来意,但还是随口回答,“段大人请便。”
“啊哈哈哈,那本官就先替皇上谢谢副将了。”段无怅大步流星的离开,“对了,副将的茶艺倒是不错,就是差了些火候,南雁王殿下说的确实在理。”
听罢,澹台神色微变,直到段无怅离开,手中的茶盏已被她捏碎。
他很聪明,知道如何扰乱她的心,这是一场捕食者之间的斗争,一个不慎,就有可能沦为猎物,但是她,真的不甘心,放不下。
北训练场
哈!哈!哈!哈!
即使喊声震天,大头还是吼道,“大点声,没吃饭吗?”
哈!哈!哈!哈!
“这位兄台训练倒是严格。”说话的正是段无怅,大老远便听见这叫喊。
大头见此人一身锦衣打扮,又别着配刀,估计是哪儿的侍卫或者将领,但一瞅他那满脸笑意,却不知为何一股无名怒火,蹭蹭蹭的往上冒,所以也没给什么好脸色,“大人还是往旁边稍稍,免得底下人训练没眼力,再伤着大人就不好了。”
“不碍事,本官就随意转转。”段无怅当真就背着手,左看右看。
蓦地,瞥见了一位少年。
在这一群黝黑的糙汉子中,这个白净的少年实在过于显眼。
段无怅随口一问,“这小子看着面生,新来的?“
“对,新来的。”此人是赤膊男一伙的,自那日起总是时不时来这边转转,但又没做什么事,大头也不好赶他。
大头有些不满,低语一句,“多嘴!”
“看着面生?段大人应该看着大多人都面生才对吧?”澹台木兰不放心,还是决定过来盯着免得出什么幺蛾子。
段无怅自知失言,但还是笑着掩饰,“本官不过看着觉着奇怪,怎么还有这么以为弱不禁风的家伙儿,本以为混进了什么宵小,还想着提醒副将一番,如今看来,倒是本官多虑了。”
“是否混进宵小,还不妨大人费心,大人还是多花些心思寻寻那小玩意儿吧,不然皇上怪罪下来,您可担待不住啊。”
“多谢副将关心,那本官就先行告辞了。”
看着消失的人影,澹台木兰的心情有些凝重。
段无怅啊,段无怅,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大头凑过来在澹台耳边低语了几句,她下意识的往一个显眼的地方瞧去。
少年觉着有人在注视着自己,猛的回头,便看见一双俊美却饱含风沙的眼睛。
她,好像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