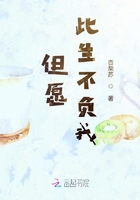此时,似有感应般,赵落昭抬头望了一眼池樊所在的房间。
没有察觉到什么,赵落昭挽手轻揭面纱,借机按一下不住跳动的右眼,玲珑笑语:“方才牡丹为各位学的舞可满意?”
众人仿佛才惊醒,却无人应答。片刻后,掌声如鸣萦绕。
“多谢各位对牡丹的捧场,牡丹感激不尽。不过牡丹留于台上时候不少,恐耽误绣月姑娘的出场,故牡丹先行告退。”话毕,欠身行了个礼,摇曳退下。
待出了百花楼坐上早已等候多时的轿子,由轿夫送回扶月楼。至于若竺,早已回去扶月楼。
“小姐,水备好了。”若竺忙步上前。
因为赵落昭跳完舞都会沐浴的习惯,若竺都会提前备好温水等赵落昭用。
赵落昭点头,对这个贴心的奴婢添了一丝满意。随后将解下来的舞衣递给若竺,因跳舞而显得沙哑的声音,称的原本清丽的声线带着喑哑:“若竺,稍后告诉我此次比赛结果。”
虽感觉这次魁花将会被自己摘得,但终归还是派若竺盯着才能安心。
“是,小姐。”若竺阖上门扉。
“毕竟…”赵落昭捻起浴桶中的一瓣玫瑰,轻嗅:“我能不能从这扶月楼里出去,可是看这次!”
亵、衣划过如玉玲珑身躯,赛雪欺霜的修长美足微抬踏入浴桶,温水的抚摸使得赵落昭有些紧绷的心放松下来。
阖眼松神中,突然啪嗒一声,浓密的睫毛下猛然掀开一双锐利的眼:“谁!”
赵落昭虽呵叱,却不敢立马起身,只能窝在水中用敏锐的目光不漏一分审查。待确定屋中无第二人,才快速站起来迅速穿好放在旁边更换的衣裳。
“自己未免过于大惊小怪了。”赵落昭边揉着太阳穴边坐在凳子上,心中暗暗道。
撇头准备给自己倒杯茶缓缓,面上突改颜色,煞白失神。
半晌后,蘼芜才伸手将桌上的枫叶麒麟玉佩攥在手中,捏紧,指尖微微抖动。
“小姐,夺魁了!”人未到语先行。
赵落昭反射性将玉佩藏于衣裳中,脸上归于平静。
若竺推门而入,姣好的面容上微微泛红,朱唇微张带着细细喘气声,胸口显而易见的起伏,语气兴奋激动:“小姐,您夺魁了!”
赵落昭听到,嘴角泛开一抹笑,发梢还带着点水滴,如出水芙蓉。又眉秀目媚,勾人心魄。
若竺一下子就呆住了。
无他,只因此刻的赵落昭好看的动人心魄,如勾魂的黑白无常,稍不小心魂就陷进去了。
“若竺,犯什么傻?”赵落昭蹙眉喝声。
“对不起小姐,奴婢刚才走神了,请小姐恕罪。”若竺回过神来,吓得白了脸色,就要跪下。
“行了,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赵落昭及时阻止她的动作,似生气的呵斥:“你小姐我不是皇亲国戚,更非名门望族,动不动就下跪!若被有心人见得,按个什么罪名,你这是要害我?”
“没有,小姐。奴婢绝没有这种想法。”头摇的如拨浪鼓。
“既没有,下次便不要如此了。”赵落昭抿了一口茶:“把香点上,散散味。”
闻言,若竺下意识嗅了一下,发现并无什么奇怪的味道。
聪明的没有开口询问,而是踱步将熏炉点燃,屋子瞬间被檀香香气充满。之后若竺又叫青楼的奴仆将浴桶抬走。
待一切都已处理完,再无外人后,蘼芜才悠然开口:“若竺,就算我无处可去你也愿意跟着我吗?”
“小姐…”若竺蓦然红了眼眶,小姐这是打算带她一起走吗?
若竺是打小就卖入青楼的,在赵落昭进入青楼的第二年就被老鸨派到蘼芜身旁服侍。在若竺的记忆中,赵落昭这个小姐不好相处,但性格温和,相比青楼中的任何一个人,若竺更喜欢待在蘼芜身旁。只因好伺候,从不打骂人,也不会动不动为难人。更何况,这些年也跟出感情来了。
赵落昭捧着若竺的白皙脸蛋,拭去她脸上的泪滴,温声细语:“哭什么,还是你想留下来?”
若竺哽咽,说不出话直摇头。
“那便不要哭了。今天我不是答应你带你走了吗?”赵落昭淡笑。
“但是……”
“好了,待明日妈妈过来我就和她说。正好我这些年也攒了些银子,赎你也够了。”安抚的轻拍着若竺的背。
“嗯……小姐。”若竺哽咽到不能语,只能用感激的眼神看着赵落昭。
好一会儿,若竺才松开赵落昭,眼睛红的如同核桃。
“哭够了?”赵落昭挪移的笑着。
若竺登时如苹果般脸红起来。
“时候不早了,早点歇息。明日我还要养足精神与妈妈讨要你呢!”赵落昭刮了刮若竺的鼻子,调戏了一番。
“那我先回去歇息了。”如兔子般跳走。
如果若竺回头,必回看见赵落昭此刻的眼中满是阴狠,手中却堪称温柔的抚摸着玉佩的纹理。
“枫叶麒麟玉!”赵落昭徒一捏紧玉佩,眼中狠毒之色徒起,声音更是咬牙切齿。
枫叶麒麟玉佩乃是王侯之物,唯有因功封的异候与被封的皇子才配有此玉。池国建国不足百年,现如今有身份配有此玉的人且在京城的人不过五人。而,今日遇见的丞相嫡三子又称约了好友一同,如此看来唯有一人最有可能。
“二皇子,池樊。”赵落昭薄唇勾起一抹冷笑,缓缓吐出次玉的主人身份。
“啪啪”鼓掌的声音对能快速答案的赵落昭很是满意。
赵落昭转过头,敞开的窗户此刻正坐着一个人,“我倒不知,向来霁月清风的礼公子有半夜偷入青楼女子闺房的嗜好。”
礼淮无所谓的笑了笑,曲起一条腿跳下:“知道采花贼为何喜欢半夜采花吗?”
此时他已经凑到赵落昭耳畔,丝缕的呼吸带着热气呼过她的耳朵,立刻浮起痒意直达心底。
“夜黑风高,好行事。”赵落昭不自觉的挪动两步。
“这只是其一。”感觉到赵落昭的眼神,说:“最主要的是,我觉得采花贼一般都是两袖清风。”
“两袖清风与他半夜采花有何关系?”赵落昭疑惑。
“自然是无钱讨的花的喜,所以才硬采。”礼淮摊了摊手。
赵落昭嘴角可疑的动了动,半晌之后开口:“礼公子难道是要告诉我,两袖清风的采花贼光临我这闺房,别无他事?”
被比喻成穷花贼的礼淮倒不所谓,只是抬手抵唇咳了一下:“我这人最是爱花。再好的名花、好花一旦种入御花园,要么便是艳压群芳。”看了一眼赵落昭,“要么便是枯萎成为她花的肥料罢了。”
赵落昭抬眼,紧了紧手中的玉佩:“你知,皓王送我这玉的意思。”皓王乃是池樊的封号。
礼淮看着她,似笑非笑:“你既知,又何必再向我求证。”
赵落昭垂眼蹙眉,在礼淮看不见的角度眼中闪过怨毒,随后眸光恢复平静,抬眼看着礼淮,似被人割了喉带着血嘶哑说:“皓王让我入宫。”
礼淮点头。
得到肯定后赵落昭目光一窒,手尖微微颤抖,之后便恢复平静:“你……为何帮我?”
身处青楼,过往高官商客众多,何况这里的女子口风甚严不会对外说,故她知道的事不算少。而在她知道的事中,左丞相与皓王生母皇后乃是一母同胞,礼淮这人更是皓王的伴读。
“不忍名花被折。”礼淮看着她淡淡说。
“若只是如此……”没有继续说下去,仿佛只是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转峰道:“既是客人,碰巧也是喜花作茶之人,不知礼公子可否与我同品一杯。”
话落不待礼淮的回答,自顾自推开房门,恰好有丫鬟经过捉着她的袖口吩咐:“去弄一壶热水,几碟点心配茶。”
那丫鬟听懂后点点头,立即转过身往东厨走去。
赵落昭合上门,转头就对上礼淮的眼,似是无解又似是了然。
赵落昭作了一个请的手势,礼淮抬脚与赵落昭一同坐落在四方的桌子旁,隔桌对望。
礼淮撇了她一眼后,默不作声的看向窗外。夜幕稀稀挂着几颗黯淡又拼命透着点亮的星星,如何抵得过明亮且庞大的圆月,终是光芒被掩盖,甚至被月夺走自己的余亮为它所有。
那丫鬟是个动作麻利的,不过几刻便敲开赵落昭的门。赵落昭接过她端过来的东西将门合上,把点心一一放好,取了自己一向珍贵的花茶泡好,倒一杯放在礼淮面前。
雾气繚繚,将面前的礼淮的侧颜称的有些模糊。
叹气如山中传起,回音不绝又止于倥偬:“锦衣之下乃是人骨,这皇宫再是精致荣华,也不过是一具具白骨搭建而成。”礼淮转过头来盯着赵落昭:“我以为姑娘应当如莲般,不沾世俗。”
赵落昭顿了一下端茶的手,失笑道:“出淤泥而不染,可惜它本身就置身淤泥之中,如何脱身。”
礼淮却是摇摇头:“身处淤泥,而非身为淤泥。”
赵落昭喝了一口茶,幽幽道:“诞于淤泥,长也淤泥,又如何置身。”末了叹了口气:“若离了这淤泥,怕是也不存于世了。”
礼淮闭了闭眼,心中不虞却是散去,徒留满腔遗憾:“是哉亦非哉,舍淤泥亦无法善哉。”
赵落昭倒是含笑看了他一眼,只不过笑中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