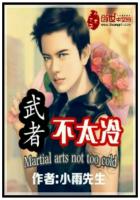朱植赶在天雷劈下之前,倒退了约有半里地。于是当蜿蜒的闪电从天而降击中地面时,辽王的卫队毫发无伤,全须全尾的继续后退,一直退进了附近的一座村镇里。
朱植在震慑住了车内仅有的一名姬妾之后,便开始着手解决新的问题。据他记忆,自己在穿越之前,乃是一位体体面面的大明王爷,绝非此刻这个衣衫不整的熊样。衣衫不整倒也罢了,大不了在下车之时,可以权充自己是刚刚车震了一次,问题是他的头发——他是短发。
本来,在他穿越之前所准备的物资之中,带有大量的优质假发,足够他和他的部下重塑自身明朝人民的形象,然而此刻他的物资和他的部下一起不知道穿越到了哪个山头去,他两手空空,自然也就无法按计划乔装改扮了。
况且,王爷的马车上放了一个姬妾是合理的,可多出来的这两个半裸男人,又怎么解释呢?
这样一想,朱植感觉自己的头都要炸了。
然而就在此时,马车也停了。有人大踏步走上前来,隔着帘子问道:“辽王殿下,怎么好端端的返了回来?”
话音落下,那人伸手一掀帘子,车内四人走投无路,一起眼睁睁的望向了他。明石倒是认得他——在现代的时候,这个人被旁人称为指挥使。
这指挥使显然和朱植关系亲密,说掀帘子就掀帘子,掀完帘子之后向内望了个清楚,指挥使登时一皱眉头:“王爷,您真是越发的要玩出花样了,怎么——不对,您的头发哪里去了?”
朱植张着嘴,思索了几秒钟,然后理直气壮的答道:“剪了!”
“剪了?为什么?”
“昨夜菩萨托梦给我,说我命中有天雷之劫,须得剃去三千烦恼丝,方能躲过这一场灾难。故而本王方才一时狠心,将这头发当真剃了些许。”
“那里面那两个人——”
“哈哈哈,本王先拿他二人练了练手法。”然后朱植向外挥了挥手:“子绯,不必大惊小怪了,今日且不走了,你自去休息吧!”
指挥使——子绯——紧锁眉头:“王爷,您这一次可真是闹得出了格,咱们接下来是要南下进京去面见皇上的,您把自己弄成这般模样,又该如何面圣?”
朱植不说话,只摆手,硬把子绯摆了走。待到指挥使真走了,朱植长叹一声,对着明石咬牙:“好,好,放着好好的真人,你们不肯做,非要看我的笑话!现在好了,你们没有回去现代,本王也糊里糊涂的浪费了一个多月的光阴。很好,很好,自作孽不可活,这一次,真人你们是做不成了,你们两个只好来做本王的娈童了!”
苏星汉问明石:“娈童是什么玩意儿?”
明石望着那名姬妾的白手,并没有听见苏星汉的问话,望了片刻之后,他抬起头,试试谈谈的唤了一声:“姐姐?”
姬妾看了他一眼,把脸扭开了。
朱植的行为,虽然看起来是古怪到了极致,但因为他是王爷,随行之人自然也不敢提出质疑,他要怎样便怎样就是了。唯独指挥使面露烦躁之色——明石打听清楚了,指挥使姓燕,名如丹,字子绯,乃是锦衣卫中的头目,朱植自小便与他相识,两人如今虽然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但情谊不减。指挥使一个多月前奉了圣旨前来,于公,是来召朱植入京,于私,也是要和朱植见上一面,做一番深谈。
朱植此刻对着燕如丹,心情有些复杂,这个燕如丹自然是他如假包换的挚友,但若是让他选择,他更想要那个和自己在未来时空共同相处了五年的燕如丹。说起来也真是令人心焦,自己的那些东西和那些人,究竟是跑到哪里去了?
算起来,距离上次穿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
朱植一边烦恼,一边开始处理眼前的小问题。所谓小问题者,就是车内的那名姬妾。穿戴整齐后下了马车,他在镇内的房屋里落了脚,镇外大雨滂沱,镇内的天空却只是阴霾而已。朱植百感交集的把那名姬妾叫入房内,问道:“你方才在车内,都看到了什么?”
姬妾慌乱的摇头:“妾身什么也没看到,只觉得眼前一花,车内就多了两个人,王爷也变了模样。”
朱植摇头一叹:“不诚实,看了这么多,还说什么都没看到。”
姬妾见他面色不善,当即跪了下来。朱植不以为然的一耸肩膀,从腰间抽出了一柄短剑,用剑锋对着那姬妾的咽喉比划了一下,想要找个一剑毙命的好位置。
可是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了“嚓——”的一声轻响。抬头觅声望去,他看木窗的窗纸破了个孔洞,一根细长的食指伸进来转了转,又抽了出去。
朱植走过去,俯身用一直眼睛向外望,结果望到了黑而大的瞳孔。他认得这只黑眼睛,这是明石。他毕生还没见过这样明目张胆的偷窥,于是索性不言语,直勾勾的和明石对视起来,倒要看看他接下来会有何作为。
果然,窗外的眼睛退缩移开了,不远处响起另一声“嚓——”,朱植扭头一看,登时啼笑皆非,因为发现明石在旁边的窗子上新捅了个洞。
“明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朱植索性走去打开房门,朗声问道。
明石直起了腰,想要回答,可是心中充满了奇异的感情,是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宁愿闭了嘴,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看一看,想一想。
后来,他恍恍惚惚的,听见自己对朱植说了一句话:“让姐姐也歇一会儿吧。”
紧接着他跪了下去。
朱植吓了一跳,不知道他意欲何为,而明石弯腰拍了拍地面,又说道:“地上太硬了,硌得膝盖疼,让姐姐快起来吧!”
然后他自己先起来了,一边拍着袍襟上的尘土,一边傻笑了几声。
朱植皱起眉毛,若有所思的问道:“看上她了?”
明石听了这句话,忽然感觉有点喘不上气。抬手按着心口做了几个深呼吸,他还是感觉胸中憋闷得慌,原地蹦了几下,他想把堵在胸中的那股子无形的阻碍震下去,然而没有用,他又想笑又想逃,又觉得羞涩又感到欢喜,于是最后眼前一黑,他晕了过去。
明石晕了一个多时辰,醒来的时候,大雨已经从镇外下到了镇内。他躺在一张硬邦邦的木头床上,睁开眼睛时看见的不是苏星汉,是那名美貌的姬妾。姬妾坐在床边小椅子上,深深的俯了身,左臂环过紧并着的双腿,左手拽起宽松的右袖,露出一截雪白的腕子。在她面前是一只更小的凳子,凳子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药,她右手持扇,正在缓缓扇散那汤药的热气。
听到了床上的响动,她扭过头来,对着明石笑了一下,露出了一点很好看的细白牙齿,但那笑容一露即收,只给人一个美丽的印象,而不许人看清楚。
“醒了?”她开了口,声音柔柔的,调子略有一点低:“先生方才忽然晕倒,真是把王爷吓坏了。”
“我叫明石,明亮的明,石头的石。”
她点了点头:“明石,奴家记下了。”
“你呢?”
她迟疑了一下,末了还是答道:“奴家名叫春枝。”
说完这话,她用手指在虚空中将这两个字写了出来。然后端起面前那碗汤药,她微垂着眼帘说道:“先生起来把这安神静心的药喝了吧,这药看着不好看,其实味道倒并不苦。”
明石坐了起来:“我不想喝,我已经好了。”
然后他伸手摸了摸春枝的膝盖:“你跪得疼不疼?”
春枝明显是慌乱了,急急的一转身,背对了明石:“你这先生,看着年少斯文,怎么这样不尊重?”
说完这话,她等了片刻,却是没有等到回答。慢慢的回过头望去,她发现明石正茫茫然的看着自己。两人对视了一刹那,明石垂头说道:“我不摸你就是了。”
春枝想了想,将手中的瓷碗向前一递:“你再把这碗药喝了,我便不怪你。”
明石听了这话,接过瓷碗,也不嫌热,仰起头就是一饮而尽。为了表示自己并没有耍花招,他放下碗后还对着春枝张开嘴巴伸了舌头。春枝被他逗笑了,站起身端了碗要走,临走前轻声说道:“先生别开玩笑了,快好生休息一夜吧!”
春枝走了,苏星汉回来了。
苏星汉穿了这明朝的衣冠,很不习惯,总想脱了袍子只穿内衣。这时关门走到床边坐下来,他问明石:“哎,听说你对朱植的女人耍流氓来着?”
明石当即摇了头。
苏星汉又问:“你喜欢车里那女的啊?”
明石这回笑了:“嗯。”
苏星汉脱了靴子,又脱了布袜,开始抠脚:“没想到,原来你喜欢熟女。怪不得我看你对那个小姑娘不来劲呢!”
说完这话,他抬起抠脚之手嗅了嗅,然后呕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