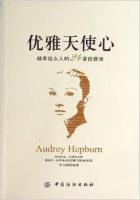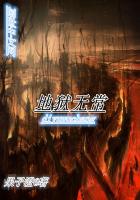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上《文选》课,刚讲了半小时,突然就宣布:“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学生们都以为他又受了什么刺激,要将哪位名人大肆评价一番。谁知却听到他说:“余下的课改到下星期三的晚上再上。”这下,学生们就更搞不懂刘文典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了,但他并不着急解释,收拾收拾教具,在学生们疑惑眼神的注视下,扬长而去。
等到了下星期三的晚上,刘文典通知选修《文选》课的学生都到校园里的一块空地上集中,说要在那里开课。等大家都坐定后,刘文典夹着教具出场了:“今天晚上我们上《月赋》。”这时候,满脸疑惑的学生们豁然开朗:当天是农历五月十五,正值月满之期,确是上《月赋》的最佳时间!
一轮皓月当空,学生们在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静听刘文典坐在中间大讲《月赋》,时而仰头问月,时而高声吟诵;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将充满新奇感与求知欲的学生带进一个人生与自然交融的化境。刘文典的一位学生后来写文章说:“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对刘文典当时在西南联大的“风姿”作了十分形象地描述: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而且刘文典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烟枪”,没有烟,根本无法正常上课。一般说来,刘文典上课,香烟不断,讲课不断。讲课过程中若是发现他突然没声音了,那一定是香烟抽完了。这时候,他一定会喊过来一位平时比较熟悉的学生,从黑得发亮的破长袍口袋里慢慢吞吞掏出几张纸币,然后郑重交代:“快去替我买包精装‘重九’来!”时间长了,学生不等他说,一看到他讲着讲着没什么劲头了,连忙将早已准备好的“重九”香烟递上去。很快,课堂里又飘扬起刘文典虽然微弱但却有激情的声音。
学生最怕刘文典讲课时没有烟抽,因为他本来声音就很小,只有坐在前几排才能听清楚。一旦他的烟抽光了,那声音就更小了,如同蚊子哼哼。有一次,一个学生忍不住说了一句:“刘先生,您的声音能不能大一点?”刘文典当即停了下来,问班干部:“你们今天来了多少人?”学生回答说:“三十多人。”刘文典拔腿就走,扔下一句话:“我上课从来不能超过二十五人,今天不讲了,下课!”
一天下午,刘文典正在上课,突然烟抽完了,于是就向坐在前排的几个男同学示意要香烟。学生们因为自己的香烟品质太差,不好意思递上去,但看到刘文典一再示意,甚至连讲课都没有什么劲头了,正迟疑着准备递一只劣质烟给刘文典。这时,有人推开了教室的门,原来刘文典的家人看到他当天忘了带烟,于是专程送来两包“大重九”。一下子,课堂又恢复了生气。
这样个性十足,知识渊博的“狂人教授”,在现如今的大学里还有几个?即使把“百将讲坛”里的诸位高人拿来与之较量,也肯定要甘拜下风。“狂人”已去,我们惟有作他的“隔代粉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