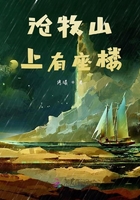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得飞快,尤利娅拿过床头柜上的年历数了一数:三十个红圈。已经过去三十天了,每天尤利娅都和儿子在梦里相会。
尤利娅已经适应了梦境,她不再胡思乱想那么多,但是心中的焦虑丝毫没有减轻,反而愈发沉重——因为梦境中唯一每天都在改变的,是阿廖沙皮肤上金属的数量。它们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它们不再是泛着金属光泽的小圆点,而是无数点连成了片,连成了块!它们堆积得越来越厚,每一天它们都毫无节制的疯狂增生,每一天都有新的金属块从皮肤里顶出来,像鱼鳞一样凹凸不平的嵌在阿廖沙的后背上!不,不仅仅是后背,而是全身!!这可怕的金属像溃烂的皮肤病,已经蔓延到了全身!!阿廖沙的后背——最先开始出现金属的地方,已经被包裹上了一层厚厚的亮闪闪的外壳,这外壳像牡蛎壳一样凹凸不平,像珊瑚礁一样坑洼交错!而他的胸口,手臂,腰,脖子全部像被铁砂散弹击中过似的,密密麻麻嵌满了大大小小的金属鳞片……最近一晚的梦中,阿廖沙的眉角和额头都开始出现细碎的金属点了!这诡异的金属瘟疫已经向阿廖沙的头部皮肤蔓延!
尤利娅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她恐惧地意识到,在梦中,阿廖沙皮肤上的金属点会越长越多,越来越密,直到全部连成一片,阿廖沙全身就会被这可怕的金属壳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她拧开灯,又在挂历上画上一个小圈。她心里害怕得厉害。她本想叫醒身边酣睡的丈夫,让他陪自己说说话,但是看了一眼时间——午夜三点半,算了吧,还是算了吧!她关上了灯,又钻回被窝里。
但是尤利娅睡不着,她特别想她的儿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泪水,不知道是因为思念,还是因为担心或者害怕……
那一天终于到来了——1980年1月22号,噩梦终结的一天,尤利娅人生中最后一次做这个怪梦:梦境中,金属像病毒一样蔓延到了阿廖沙的全身,她的儿子终于完全被亮闪闪的金属外皮完全包裹住了!
她在梦中还没意识到,这一天之后,她不会再做这个噩梦,但是她的整个生活将会变成一场真正的噩梦!
梦境中,全身裹着锌皮的阿廖沙咧开嘴对她微笑。
“阿廖沙,你笑什么?”尤利娅在梦中问儿子。
“妈妈,我安全了,他们再也伤不到我了!”阿廖沙回答着,眨了眨眼睛,笑得更灿烂了。
尤利娅看到,连阿廖沙的眼睛和牙齿都被裹了一层金属,闪着耀眼的白光。
“什么?阿廖沙?你说有人要伤害你吗?是谁?他们为什么要伤害你?”尤利娅焦急地问。
“妈妈,有人想要攻击我,但是你不要担心我,我有金属盔甲的保护!谁也伤害不了我!”阿廖沙说。
“阿廖沙,那你告诉我,你在哪里?告诉妈妈你在哪里?”
“妈妈,我在冰冷的荒野里……但我马上就要回来了,就要回到你的身边来了……”
“真的吗,阿廖沙?太好了,太好了……”尤利娅激动地说。
“但是,妈妈,要是我真的回到你身边,你会害怕吗?”
“什么?我为什么会害怕?”尤利娅问。梦境中的她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因为我……”阿廖沙突然收起了笑容,开始嘤嘤啜泣。
“因为什么?”尤利娅焦急地问。
“因为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再也……变不回来了……”阿廖沙指着自己皮肤上的金属,哭泣起来。
尤利娅突然心里一阵难过,忍不住也淌出了泪水,她深情地说:“阿廖沙,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害怕,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呀!你回来吧!”
但是阿廖沙似乎没有听见母亲的话,他依旧哭泣着,而且哭喊声越来越大:“可是我再也变不回来了……再也变不回来了……”
“阿廖沙!阿廖沙!”尤利娅呼唤着儿子。
可儿子仿佛完全听不见她的声音,继续大声地哭泣:“我被裹在了金属里……我被裹在了冰冷的金属里……呜呜呜……”
“阿廖沙!阿廖沙!!”尤利娅担心地大喊。
阿廖沙仍然只是一个劲儿大哭,他的哭声突然变得凄厉起来,奇怪的音调忽而尖利,忽而低沉,幽幽地在四方荡漾开,余音久久不散:“我披了一层锌皮啊……我的锌皮啊……”
突然间,仿佛天地间整个世界都回荡起了阿廖沙凄厉的哭声,这声音像是从云端传来下的天堂圣号,又像是从幽冥地府传出的地狱回声……在这凄厉诡异的声音里,阿廖沙的身影开始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阿廖沙!阿廖沙!!”尤利娅突然害怕得大叫起来。
阿廖沙的身影越来越模糊,他就要从梦境的场景中消失了!
“阿廖沙!!!阿廖沙——”尤利娅声嘶力竭地大叫。
突然,一切都消失了,眼前只剩下一片黑暗——尤利娅睁开了眼睛,她从梦中惊醒,发现后背沾满了冷汗。尤利娅翻身而起,拧开了台灯。她感到头晕目眩,心脏在胸腔里通通狂跳。
是阿廖沙真的要回来了吗?还是……不会是阿廖沙真的出了什么事吧……不行,一定要让谢尔盖去区团委办公室问问!不管他愿不愿意,一定要让他去问个明白!
尤利娅想道。
尤利娅睡不着,她听着丈夫不规则的鼾声,在床上翻来覆去,脑海里都是阿廖沙身披金属锌皮的身影。
好不容易熬到早上,天刚蒙蒙亮,尤利娅就赶紧把丈夫推醒。
“谢尔盖,醒醒,谢尔盖!”
“你这婆娘……现在才几点……你让人多睡会儿……”谢尔盖伸了个懒腰,又翻过身,想要继续睡去。
尤利娅一拳重重捶在丈夫腰上。
谢尔盖猛地一下弹坐起来,气愤地看着尤利娅喊道:“老婆子,你发疯了啊?!”
尤利娅心中已经燃烧起了焦急的火焰,她顾不上跟丈夫解释任何东西了。她一把抓住丈夫的睡衣,把他从床上扯起来:“谢尔盖,无论如何今天你要去一趟区团委!不要推辞!一定要去!一定要把关于阿廖沙的所有的事情都问个一清二楚!!”
“老婆子,你发疯了!你疯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去团委办公室多问!”谢尔盖气愤地敲着桌子。
“可是我昨晚又梦见阿廖沙了!他全身被包上了金属皮,还在那里一个劲儿伤心地哭……这分明是他遇到了麻烦,他在给我们托梦啊!”尤利娅又气又急地解释。
“托梦?笑话!亏你还是共产党员呢,还相信怪力乱神,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谢尔盖吼道。
“谢尔盖,算我求你,你去吧,去区团委办公室问个清楚,问问你儿子到底在哪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尤利娅几乎是在哀求了。
“我不去!绝对不去!去了也问不出什么!那是秘密工作!”谢尔盖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恳求你,谢尔盖,阿廖沙可是你的儿子啊!”
“我说什么也不会去的!我不想给儿子丢脸!”
尤利娅伤心地瘫坐在椅子上,过了一分钟,她又站了起来,她下定了决心,自己去区团委办公室问个明白!
“你不去,那我自己去!”尤利娅瞪了谢尔盖一眼,气愤地说。
“得了吧,你已经去过多少次了?人家都被你问烦了,你信不信,这次门卫都不会放你进去,都认得你这张脸了,老婆子!”
尤利娅没有理睬丈夫的话。她迅速的穿上了皮靴,披上大衣,又把帽子拿在了手里。
她的心里焦急万分,她只想着一件事:弄清楚阿廖沙人在哪里!
她快步走到门口,正要伸手开门出去,突然门板“咚咚咚咚”响起来——外头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尤利娅被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了一大跳,不知为什么,听到这敲门声,她心里猛地一沉,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从心里升起。
“是谁呀?什么事那么早来敲门?”谢尔盖高声问道。
“沃伦佐夫家吗?请开门!我们是区团委办公室的人!”门外的人大声喊道。
尤利娅伸手打开了门。
门外面,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一左一右恭恭敬敬地站着。一看见尤利娅,他们马上站直身体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而后又朝她深深鞠了一躬。
尤利娅看着他们,心中不祥的预感越发强烈了,她死死盯住他们的脸,浑身因为紧张和害怕而颤抖。
一个黑衣男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一边双手递给尤利娅,一边用低沉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我代表区团委所有同志向优秀的共青团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阿列克谢(阿廖沙)?沃伦佐夫同志致敬!我们为阿列克谢?沃伦佐夫同志的英勇无畏感到无比骄傲!”
黑衣男人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肃穆。
难道是阿廖沙在国外立了功,团委上门表彰先进?表彰不会这么早上门……
尤利娅看着黑衣男人的脸,有些疑惑不解。她接过了黑衣男人递过来的叠得方方正正的信纸,小心翼翼地打开,想看一下这张小奖状上写的究竟是什么。
当她看清信纸上写的字时,突然惊叫一声,头脑一阵晕眩,脚底像抽空了一样打起战来,她仿佛已经喘不过气来,身体一震,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谢尔盖冲出来想要扶起自己的妻子,当他蹲下身时,他也看到了那张摊开的信纸——他的目光刚一触到那些字,他就突然像被雷电劈中一样浑身痉挛,他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双手捂着眼睛用低沉的声音呜呜哭起来。
那摊开的信纸上分明写着一行大字:阵亡通知书。
尤利娅挣扎着半坐起身,喃喃地问道:“阿廖沙……难道……他阵亡了?”
“他在阿富汗战场上与敌人英勇作战,光荣负伤,不幸身亡!”黑衣男人说。
尤利娅的嘴角颤抖着,脸色煞白,又喃喃问了一句:“阿廖沙……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凌晨三点三十分整宣告死亡,请您节哀!”
“三点三十分整?天哪!!”尤利娅尖叫一声,感叹着命运的捉弄。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她都在凌晨三点三十准时从梦中醒来,而儿子正是在这一时刻撒手人寰!
深深的悲伤浸没了尤利娅。她不顾屋外一月凛冽的寒风,躺倒在门槛外的雪堆里。雪和污泥混在了一起,搅成了灰色的泥浆,尤利娅就这样绝望地躺倒在泥浆里,眼睛里流着伤心的泪水……她一遍又一遍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可儿子却再也听不见了……
“为什么?为什么事先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阿廖沙是去阿富汗打仗?啊?为什么?骗子!!你们全都是骗子!!!说什么国际主义援助,说什么去第三世界建设共产主义……骗子!!!”谢尔盖用嘶哑的嗓音朝两个黑衣人大吼,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几岁,眼角里老泪纵横……
两个黑衣人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又深深地鞠了一躬。
突然,尤利娅停止了哭泣,她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艰难地从地上坐起身,用尽全身力气问黑衣人:“我的阿廖沙现在在哪里?你们把他带回来了吗?”
黑衣人弯下腰轻声说:“共青团员阿列克谢的遗体,我们带回来了。”
尤利娅抽泣着说:“我想看一眼我的阿廖沙。”
黑衣人轻声说:“好的,这就给您看。”
“等等!”尤利娅突然一把抓住了黑衣人的袖管,问道:“我的阿廖沙的遗体,看起来还好吗?”
“这……”黑衣人不知该怎么回答。
尤利娅死死盯住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这几天一直在做梦,梦见阿廖沙,昨天我还梦见他说马上要回来,你们就把他的遗体带回来了——这梦可真是灵验啊!可我还梦见,阿廖沙全身长满了金属片,他被金属锌包裹着,那些金属就像鱼鳞一样附着在他身上,闪闪发光……他不会真的全身长满锌鳞片吧?”
黑衣人摇了摇头。
说完,两个黑衣人一起转身,庄严地大喊一声:“向家属移交烈士遗体!”
街上突然出现了六个身穿礼服军装的士兵,荷枪实弹,迈着庄严的脚步缓缓向门口走来。
他们好像抬着阿廖沙的灵柩——用一面巨大的共青团团旗覆盖着。
尤利娅艰难挣扎着起身,向灵柩冲了过去。她扑倒在灵柩前,一下子掀去了覆盖在上面的红旗。
她看清了!
她惊叫了一声!
那被红旗盖着的正是……
……一口亮闪闪的锌皮棺材!!
原来,梦境中阿廖沙身披锌皮,是预示着他被严严实实封在锌皮棺材中!
一九七九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无数共青团员被征召入伍,成为侵略战争的炮灰。政府瞒着这些孩子的父母,以“国际主义援助”和“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名义,把这些年轻人派上了阿富汗战场。毫无经验的青年人在枪林弹雨中成了敌人的活靶子,血流成河,遍地尸体!军方来不及体面地为牺牲者收尸,无数简易的锌皮薄棺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归宿。在战争初期,阿富汗战事对普通民众严格保密,毫不知情的父母们还以为自己的孩子“在山村里教授俄语”、“在沙漠里搞植树绿化”!
诡异的是:至少有十几个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孩子的母亲说,她们曾在梦中见到自己的孩子全身被亮闪闪的锌皮包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