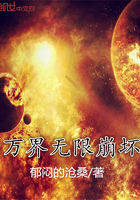上了岸,这时,才看清,这里只是一片不到一平方里的小岛,小得那样的可怜。随手把衣裤丢在草地上,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
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屁股上湿乎乎,粘连连的感受,辛操一下就知道有什么在上面?
“屁股!屁股!”
辛操大叫起来。
“屁股不是在你屁股上,叫什么?
“不是屁股,是屁股上有东西?”
“屁上有东西,有什么在惊小怪不事?”
“屁股上有······”
辛操一时不知马蝗或是水蛭叫什么名字?只一个劲的叫到:
“屁股上有,有什么东西?我很害怕。”
“我瞧一瞧?”
太蒙走来,辛操爬伏在地上。太蒙伸手就去拉辛操的短裤,可是刚拉到一半,小蛭是看见了,同时了看见屁股中间,一股气流,夹乱着些什么物质往外就吹,太蒙一退,手还拉着短裤的腰带处,退到身体与手上的力,都受到腰带的牵扯时,太蒙猛就放手。
“对不起,对不起,你伸手一摸到我的腰眼,我就忍受不住了,真是对不起。”
再一次去剔除那些水蛭时,太蒙做了准备,侧着身体,以一个准备起跑的姿势,蹲在辛操的身边。拉开短裤,两个水蛭,就死死的吸在两边屁股上。
也许是太蒙迁怒于那一个屁,抬手就向着上屁股上拍拍的两大巴掌,屁股上马上不有两个红红的巴掌印,可两只已经饱吸满血的水蛭,还是卷曲扭动着身体,强有力的吸盘,就是不肯放开。
两巴掌打完,太蒙才抽出短刀,在水蛭与屁股上划动削割,轻轻一滑,一拔,水蛭就剔在了刀口上,随手一甩,就向下一只移动过刀口去。
“其他的地方还有吗?”
辛操并不知道水蛭已经除去,伏在草地上,还是不动。
“你取下屁股上的我再看一看。”
“已经为你取除了。”
辛操站起来,还是不好意思脱去短裤,只是伸手四下去摸索。
“脱啦,脱拉,还有什么不好意思,死这样的事,我们都一同经历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看的东西,更何况,你那东西只有你自己在乎,你以为,我还在乎。未来的两天,我们光着身子,才能更好的离开这一片沼泽。”
惊慌过了,现在一切安全,饥饿马上就在胃里象一把刀子一样,拼命的剐着胃壁,一种无力的虚弱,马上又来到,口渴也跟着催动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
太蒙也不理会辛操的感受,握紧短刀,就开如挖起土来,本就潮湿的泥土,在利刀的刨插之下,一会儿就挖了一个尺余多的坑,太蒙还没有停下,还在向下,左右加宽的挖刨着。
“过来,过来,有吃的了。”
辛操听到太蒙的招乎,大喜之下,连爬接滚,就扒到坑边,往里面看。
“看哪里,看这里?”
太蒙说着话,用刀从泥里挑出一条蚯蚓,伸到辛操的面前:
“食物,只有这种东西了!”
看着今天的已经过了正午的午餐,辛操的绝望,与那扭动着的蚯蚓也没有什么两样!
“你若不吃,就等我先吃够了,你再吃,只怕到时候,这地方的蚯蚓以没有多少?”
“您先吃。您先吃。”
辛操一连用了两个您,太蒙看也不看他一眼,刀微往下一斜,蚯蚓就滑在草地上,太蒙也不去吃,还是往深处挖,又一条蚯蚓出现在刀下,太蒙用刀挑起,往草地上一斜,蚯蚓又落在草地上,先时那一条蚯蚓刚爬移了几步,一身的泥土,刚好在爬行里抖落,太蒙左手一抓,仰头张口,蚯蚓就落在口中,只见太蒙的喉咙动了一下,低头,接着就去挖他的坑。
坑越挖越深,蚯蚓也不断的在出现,可是太蒙理也不理会辛操,只是在出现一条蚯蚓后,才把先时的一条蚯蚓吃了下去,其实,太蒙也不是在吃,而是在落入口中时,直接就咽了下去。
辛操在太蒙咽下一条蚯蚓时,自己的嘴里,都会有口水在从两腮间流出,太蒙的蚯蚓咽下时,他就会不自主的咽一次口水。
辛操的一双眼睛,全在太蒙的动作上,每一个动作,都象是在眼前放大一样,而自己赤裸着的身体,还有太蒙一身肌肉,没有一丝遮掩的扭动,力量是一种在肌肉上张力的体现,可是辛操的一双眼睛,却只是在关注那些,出现了,又消失的一条条的蚯蚓。
一个深过沼泽水平面的大坑已经挖出,再挖下去,太蒙已经有一用要探下身体了,太蒙才停止下挖。刚挖出的一条蚯蚓还在爬动,辛操见太蒙有意要住手,忙说到:
“这一条,我来吃。”
太蒙也不理会,站起身体就往他早洗揉了多时的衣服走去,拣起衣服,又走了回来。可辛操在这一段时间里,两个指头还夹着那扭曲翻转的蚯蚓,一双眼睛,盯着它的动作,却是无法把这个活着呢?真正原生态的食物放在口中。
太蒙也不理会辛操,只是把衣服折了两折,就丢在深深的土坑里,拿起木棍,又往衣服的中间捅了一捅,直到有折好的衣服中间,有了一个凹处,才放下棍子,朝着小树的树冠边去。
半蹲着的辛操,两指夹着蚯蚓,站直身体,四下张望,只见不大的一块草地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小树,而小树都是一样的叶片,再有,就是绿油油的青草。
太蒙又用刀子挖起土来,辛操转身背向太蒙,眼睛一闭,张口仰头,也学着太蒙的样子,把蚯蚓放在口中,牙齿都不敢去碰一下蚯蚓。蚯蚓从长这么大,真还没有见过,扎赉旗城里可没有土地养蚯蚓,那些会动的,土里钻动的,都是在视频里,在脑机学习机里见到。
此时,一条蚯蚓正从食道滑下,经过每一寸食管时,都在想向着蚯蚓的扭动,还有爬行,还有蚯蚓肚子里的那些泥巴与它们的糞便。
好在,没有太多的恶心感,只有一丝丝冰凉,接着,也没有感到胃里有东西在蠕动。
口不渴了,只是在心里,在食管里,在胃的位置里,仔细的感受着一条蚯蚓的被吃下,当然,用生咽下去,才是准确的形容。
太蒙象是已经挖出一条蚯蚓,辛操太熟悉太蒙的动作了,只是这一次,他伸手去摘了一片树叶,直接就把树叶塞入嘴中,接着又去挖,又一条蚯蚓被挖了出来,太蒙歇了一下,咀嚼着树叶,咽下,才伸手去捉地上的蚯蚓。
看着太蒙的动作,辛操走近小树,去观察那一棵小树。
“蚯蚓难吃吗?”
辛操还没有体会到蚯蚓难不难吃,只是在体会着心理与身体的反应,一时还不知如何回答太蒙的问题,只是问:
“这树叶也可以吃吗?”
“树叶是菜,而这蚯蚓就是今天的饭。”
太蒙的回答,直接而没有迟钝,象是辛操所有的心思与行动,全在他脑后长着的眼睛里一样。
辛操也摘了一片枝尖的嫩叶,放在嘴里嚼动起来。绿叶里的不多的液汁在嘴里流动,一股青草的嫩青草味满口都是,而嚼碎的那些树叶,却是一种无味的木木的难嚼,胃里的蠕动,那种饥饿感,已经有了胃部微微的有痛感。
辛操知道,那种胃部的隐痛,是胃黏液在消蚀着胃壁层的隐痛。这种隐痛,无限的剌激着辛操对那些政府免费的食品的思念,就更不用说餐厅里飘香的,自己只有偷偷拣食,才得的美食。
树叶是咽了下去,可一嘴的青草味,还略有一些苦涩,嘴里,太需要另一种味觉去冲淡一下树叶的味道,就算也一口水,也很美好。
草地上,太蒙才挖出的蚯蚓正在爬,辛操伸三个手指就去抓起,仰头就放在自己的喉头间,喉头遇上异物的蠕动,蚯蚓再一次在食管里滑动,这是最真实的生命的粘滑感,可却象是在有意对抗先时那种树叶的苦涩,树叶带来的不适,瞬间就消失,可当蚯蚓入了胃里,那种树叶的青涩味,又回到嘴中。
太蒙一连挖了十多条蚯蚓给辛操,把刀往土里一插,坐在地上:
“现在,到你自己挖给自己吃了,我得休息一会儿。”
十多片树叶与十多条的蚯蚓,一共进入胃中,饥饿得到了一定的释缓,力气也象是回复了一些。辛操抓起刀子,沿着太蒙开垦出的土地,接着就挖了起来。
太蒙虽是坐在地上,却是在不停的咀嚼着树叶,象是这种树叶对他,有着一种不同异样的诱惑力一样,不止是饥饿那样的简单,就在他身边的一枝树叶,很快就要被他摘光了。
辛操手中的土地,不停的翻动碰上黑色的泥土,蚯蚓却是始终没有出现一条,太蒙也不理会,还是咀嚼着树中,不时,还折几条青草,放在嘴里,一条蚯蚓终于出现在他翻动的黑土前,辛操直接把刀往前插下去,翻动泥地,可蚯蚓又往土深处钻去。
这时,辛操才知道,要挖一条蚯蚓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额头上都有了汁水,终于把一条蚯蚓从土里挖了出来,送到太蒙的身前,辛操也没有递在太蒙的手中,而是让蚯蚓在太蒙身前的草地上爬动。
挖着蚯蚓,辛操无数的画面在回忆,最后,他想,自己一万年,或者是两万年前的祖先,也许就是这样挖掘着土地,翻找一条条的蚯蚓,只是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手中这把刀,可能是一树木头,当然,那时候应该是石斧也没有。
胡思乱想里,最终还是回到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越来越是迷,太蒙的回答,模糊而没有准确的定义,他也象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一样?
只挖了五六条蚯蚓,辛操就累得手足无力,刀往地上一插,就翻躺在地,口里的干渴感,伸手就去摘一片树叶来解决。
风吹起来,微微的有热的晚风里,太阳还很高,辛操只知道天要黑了,可是那时黑,他还不知道?四野是青草让他已经生出怨烦的那种草青味,只有身下的泥土,还有青草的样,还有那些小树,天边蓝蓝的天空中,飘浮着的几条条白云。
太阳还是无法去直视,头顶上,一片片水波一样轻薄的浮动,动又不动的若大一片,扭一下头,水里有云,还有金黄色的阳光,天的蓝,全在水里,风一过,一片的涟漪下,一切都动了起来,水里的太阳,长条的扭动到老长老长。
真美!一切真美!可是一想到还要吃蚯蚓,一种恶心感,终于涌到了喉咙间。一个幻影,一闪而过,自己的脑海里,自己的胃中,就是一团的蚯蚓在不停的蠕动着。
“哇······”
一声干呕,胃里所有的东西往上涌动一下,眼睛里有酸酸的泪水也象要出来一样。
“过去喝一口水,不要喝太多。”
辛操扭头去看太蒙的脸,话一时还说不出,喉咙间有一种酸楚在里面辣辣的难受。
太蒙用手一指,先时挖掘的那一个大坑,太蒙还把衣服丢在里面的那里。
辛操原以为今天的饮水,就是这些树叶,太蒙不停的咀嚼,就是为了其中的那些叶汁。现在听到太蒙说,可以过去喝一口水,心中不禁就是一阵的喜愉,手足并用的在草地上爬行,几下就爬到那坑边去。
到了坑边,往里望,果然有着一汪的清水,积在一团凹下一处的衣服中间。
辛操努力而快速的往下探头,一直把头伸到水洼边,闻也不及闻一闻,就用嘴吸了一口。水不是清凉甘甜,全是太蒙一身的汁味,微微还有一些咸,辛操不知道,这种咸味,是不就是太蒙身上那些汗液里的盐分的咸味?
扶着黑色的泥土,辛操抬起头,还是把一小口水努力的咽了下去,咽下水,辛操拼命的摇摆起头来,回头去望太蒙,若有问题要问,可闭眼一想,他必也是这样去喝一口水,只是这衣服里,全是他自己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