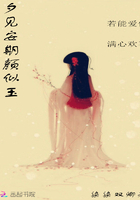“待我回去再审。”谢崇宁将穆谣纤细的藕臂环在脖子上,俯身将她抱起。
“我送你回去。”
穆谣哭声弱了下去,却仍在谢崇宁脖颈处浅浅抽泣着,教了自己六年的老师,忽然间变成了杀人狂,还要杀了自己,任谁一时间也不能接受。
更可怕的是,若是谢崇宁没能及时出现,那她此时怕是已经不在这了。
谢崇宁稳稳抱住怀中缩成一团的人儿,余光注意着她的举动,放纵了她没有安全感的磨蹭。
待马车来的时候,穆谣渐渐寻回了理智,也知道自己刚刚那矫情的举动实在是越矩,没被谢崇宁扔在地上已经是仁慈了。
她快速从谢崇宁的怀抱中跳上马车,正了正有些凌乱的衣襟,低声道谢,“多谢谢大人救命之恩。”
谢崇宁看着她利落的动作,眉心不自觉微蹙,旋即撩起衣摆径直上了马车,“我送你回去。”
“不……不必,大人有要事在身,不应被小女子耽误了正事。”穆谣低着头说完一抬头就见着谢崇宁已经迈进了马车。
嘴角抽了抽,穆谣长吸一口气抿着嘴儿也跟了上去。
人都在车上了总归不能再赶下来吧?再说了她也没那胆子。
本就不太宽敞的马车,又挤进来了一位腿长手下的谢崇宁不免显得逼仄,便是再如何拉开距离,车厢摇晃下两人总归还是会碰到。
谢崇宁坐的笔直,两手搭在膝盖上,微阖双目似在闭目养神,俊美面容沉冷一片,深蓝的官袍衬的他气势愈发深重。
穆谣心中不免打突,极力蜷缩自己的身子,低着头有些心不在焉,衣襟下滑露出一截雪白纤细的颈子。
“知道怕了,就不要以身试险。”低沉声音自头顶响起,穆谣下意识抬头就见着谢崇宁依旧闭着眼并未看她。
穆谣抿了抿嘴,心头有些沉闷,她哪晓得教了她六年的女先生会是一个心理扭曲的人?甚至今儿还险些杀了她。
相比较于谢崇宁,总归女先生会让她更安心些不是?
大抵是心中对谢崇宁成见过深,这才导致了这般后果,只是再来一次她或许依旧会在这么做。
“大人教训的是。”穆谣低着头盯着鞋面上的绣花,心头一阵阵发紧。
谢崇宁睁开双眸,目光落在她小巧的耳垂上,碧玉的坠子在脸颊边晃动,衬的肤白如雪,“日后小心着些。”
穆谣轻轻嗯了一声,仍旧是没有抬头,浑身上下都昭彰着她疏离的态度,岂料马车一个晃动,穆谣没稳住身子直接倒向了他,一声轻呼后好歹是稳住了身子没有扑到他怀里,可手还是没控制住按在了他手上。
掌心温热的触感令穆谣心中一晃,触电般缩回手又往门口挤了挤,低着头小声道歉,“失礼了,抱歉。”
谢崇宁定定看了她片刻,将手拢入袖中,启唇冷漠道:“无妨。”说罢便也不再言语,闭上眼兀自养神。
马车一路摇摇晃晃,终是再无别的意外发生。
“大人,滦平侯府到了。”
车夫的声音响起打破了车厢内沉闷的气氛,穆谣提起的心陡然一松,微微侧身对谢崇宁道:“多谢大人相送,侯府已经到了。”
她想下车,奈何谢崇宁却是占据了大半车厢让她无法顺利下车,穆谣抿了抿唇正欲张口想让谢崇宁让一让,结果车厢外却是响起了一道嚣张的声音。
“谁的马车挡在我们滦平侯府的门口?!”
“赶紧滚开!小爷要出门不知道吗?!”
跋扈的声音熟悉无比,正是穆良宣。
穆谣皱了皱眉,这马车是谢崇宁派人叫来的,外表看上去极为普通没有任何标识,只怕穆良宣那个兔崽子就是仗着这个才这般嚣张。
只是最好别叫他撞上了谢崇宁,就他那没脑子的蠢货,说不得就得栽谢崇宁手上,到时候万一拖了侯府下水,那她这些年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家弟无礼,不知道谢大人在车里,还请谢大人勿要怪罪,我现在便下去管教。”穆谣顾不得会跟谢崇宁有肢体接触,小心蹭过他的腿下了马车,一眼就看到了穆良宣吊儿郎当的站在侯府门口满脸不耐烦的叫嚷。
“在家里没轻没重,怎么出了门还这般莽撞?外面祖母可罩不得你。”父亲孝顺,滦平侯府内祖母的话便是圣旨,到了外面,祖母可就鞭长莫及了。
穆谣侧过头,撇了一眼没有动静的马车,心中隐隐催促着谢崇宁早些离开,“你惹了事是小,若是让侯府蒙羞,到时候祖母也不会护着你了。”
穆良宣执拗的别过头,用鼻子挤出个“哼”擦过穆谣肩膀不屑的走过去,“你也就是在外面威胁威胁我,等我回去告诉祖母,看你还有没有这般傲气。”
因为母亲的缘故,穆谣这几年确实很少与穆良宣纠缠,只是今日马车之内坐了个谢崇宁,她总不能对这泼皮无赖放任不管,祖母那边她自会认错。
“不对啊!你不是有早课吗?今日怎么早早便回来了?”穆良宣没走出两步又快步折返回来,直直走向马车,穆谣来不及阻止,只见穆良宣肥腻的手倏的扯下马车的帘子。
深蓝色的衣角暴露在阳光下,穆良宣虽看不清那人的脸,却也看出了是个男子,抓住穆谣把柄的他笑的奸诈,“我道你为何突然回来呢,原来是同野男人幽会去了。”
穆谣抬起的手臂无助的悬在半空,眉尾处突突直跳。
“怎么不说话了?”穆良宣得意的将帘子扔在地上,鼻孔翻上天去嘲笑道,“你这是在学二婶家的庶姐呢吧,不知你……”
还未等穆良宣吐出更难听的话,谢崇宁优雅的俯身站到马车边缘整理衣角处的褶皱,“你说谁是野男人?”
谢崇宁高大的身影将穆良宣罩住,如若不是穆良宣胖了一圈,那投在地上的影子便只能看见谢崇宁一人。
熟悉的声音让穆良宣虎躯一震,错愕的扬起头张望,“谢崇宁?”
身后便是太阳的谢崇宁浑身仿佛笼罩了一层金光,可寒气依旧从穆良宣的脚底直达头顶。
谢崇宁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由欺凌的野种,正三品的乌纱帽扣在头上,穆良宣纵使心中百般不平衡,却也不敢造次。
谢崇宁眼角鄙睨的扫过了他,便忽略了跳梁小丑一般僵直矗立的蠢货,“我送你进去。”
再一次不容拒绝的谢崇宁走在穆谣身前,穆谣只能小碎步跟在他身后,追随着那一抹蓝色的衣角。
谢崇宁先是去拜访了滦平侯穆贺云,毕竟有了官职身份,今时不同往日,虽说只是将穆谣送回来,但拜访是不能省的。
沈眉听说谢崇宁的到访,往日的繁缛礼节顿时抛在脑后,同穆贺云一起迎接谢崇宁,熟料却见到了跟在谢崇宁身后的自家女儿。
夫妻里顿觉头疼起来,左防右防怎么两人不仅没有拉开距离,反而自家女儿罢了课同谢崇宁一起回来了?
“谣儿你怎么回来了?许老师的课怎么办?”穆贺云同谢崇宁,连寒暄语都未说,先是给自家夫人偷偷递了个眼色。
沈眉心领神会的快步走到女儿身边,将她拉了回来。
夫妻二人的举动很是明显,谢崇宁离开了滦平侯府,那便与他们再无瓜葛,他们也不想穆谣与谢崇宁有任何的来往。
穆谣尴尬的撇了一眼谢崇宁,自己父母表现的未免有些太过冷淡了,“爹娘你们误会了,今日若不是谢大人……我便回不来了。”
站在一旁的谢崇宁唇瓣微动,眼神锁死在穆谣身上。
“怎么回事?”沈梅最先发现女儿的不对,穆谣眼眶红红的,仔细看去脸上似乎还留下了两道泪痕,额前本应规整好的碎发也有些散乱。
“许柔便是鱼线杀人狂,谣儿险些丧命。”谢崇宁将眼神从穆谣身上挪开,“大理寺已将她缉拿归案,侯爷夫人不用担心。既然我已将谣儿送回,便不多打扰。”
短短几句话三人皆震惊的看向谢崇宁,夫妻二人是没想到自家谣儿竟然经历了如此惊险之事。而穆谣没想到的是,谢崇宁竟然称他为谣儿,这称呼未免亲昵了些吧。
他回头看向素来紧张的父母,好在二人都被谣儿险些丧命一事震惊到,并未注意谢崇宁的措辞。
沈眉见谢崇宁将要离开,才意识到他们二人太过敏感,对于谣儿的命恩人招待不周。便立刻叫住谢崇宁,“谢大人不如在府上稍作休息,也好让我夫妻二人表示一番感谢。”
穆贺云虽是介意谢家之事,但也分得清是非,谢崇宁有恩于他们谣儿,他不能让人觉得他穆贺云薄情寡义。
“是啊,谢大人不妨在府上坐坐。”
“我还有犯人要审辩不多做打扰了,多谢侯爷夫人的美意。”说罢谢崇宁又讲目光转向穆谣,“谣儿今日受到不小惊吓,侯爷夫人还是先照顾谣儿吧。”
道谢毕竟不急于一时,夫妻二人思量一番,还是先替谣儿叫来了大夫。
沈眉心切的拉着穆谣的手,担忧的询问发生。穆谣添油加醋说着当时情况是多么紧急,更是将谢崇宁的出现美化到了一定高度。
“爹娘,当时那冰凉的丝线贴在我的脖子上,我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谢大人猛的一脚踹开了木门,及时地将我拉出了许柔的魔爪,我真的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回顾当时的场景,穆谣的害怕又涌上心头,眼角也泛着泪光。
沈眉同穆谣一样就是热着眼眶,紧紧将女儿抱在怀中,“都是娘不好,没想到许柔竟是杀人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