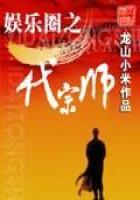殿中众人互相瞧了几眼,终于起身相互道了声告辞,携了侍从便向各自的宫室去。
百里炙心里早就挂着几日后同陛下外出,匆忙带了人便回去收拾打点了,而夜宸卿一路上倒是走走停停,并不着急,一路经了那水边的凉亭,忽而侧身问向一旁的侍从:“可是带着琴了?”
侍从闻言一愣,瞧了瞧一旁的凉亭,略微犹豫,终于道:“回公子,带着呢。”
夜宸卿微微扬了扬唇角,笑道:“那便将琴放过去。”
侍从一愣,道:“公子,天不早了,也快到用晚膳的时候了,此时,公子便回去好生歇息罢,在此处弹琴……”
夜宸卿心下明白这侍从不明所以,只当他是那等羸弱的公子,便笑道:“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何况公子炙走得快些,已然向西边回宫了,我在此弹琴,想来也不会叨扰了他人。”
侍从闻言明白是自己多言了,只得道:“奴才多嘴,这便去收拾。”
夜宸卿颔首,启步走到那水边,任凭水面的清风拂过他的面颊,掠过他的长发。
这宫里的水日日在这泉边流淌,不止不息,当真不知见证过多少香消玉殒。
他微微闭了眼眸,修长挺拔的身影映着天边的夕阳,显现出几丝落寞与冷清。
他来到这里,已有一年多了。
听着身后长琴放置好的轻响,夜宸卿回了神,转身行至琴边,悠然坐在一旁的石凳上,修长硬朗的手指在琴弦上轻掠,便有悠扬的乐音喷薄而出。
正是一番古调唱晚,他随性而弹,偏就奏了这曲子。
一旁的侍从听着这天籁一般的乐音,也是痴了,可忽而又回神去估摸着时候,掐指算来,恐怕已是用晚膳的时候了。
侍从自然记得,陛下有吩咐过,不得让公子总是弹琴。
他张了张口,可又噤了声,夜公子此时正微闭双眸,抚动那琴弦,他又岂敢打扰。
侍从迟疑着,夜宸卿又全然忘了时间,直到那夜风轻抚,皓月渐出,群星已隐。
弋栖月在养心殿里足足忙了一个下午,且不说批了那堆积成山的奏折,思量了下月大典的事宜,她还平白给自己弄出不少事务来——接下来几日暗中跑出宫去,要把一切安排好。
做完这一切,却见碧溪和卧雪两个丫鬟已经候在了一旁,碧溪此时一脸正色道:“陛下还未用晚膳。”
弋栖月闻言面色显出几分尴尬,碧溪自幼时在她家中便是这副一丝不苟的模样,认真起来她也真真是没有办法,只得比了比一旁空空如也的盏:“方才那燕窝已然吃了,也不必用什么晚膳了。”
卧雪闻言忙上前收了那空盏,碧溪则道:“陛下这些日子操劳,婢子也是知道的,可夫人前些日子还交代过,说万不可让陛下忙垮了身子,奴婢自是不敢违命。”
弋栖月闻言,脑海中出现了母亲在寺庙里念经的场面,心间不由得一暖,定了定神,便道:“朕是知道的,方才那燕窝也是不少,再吃也是不必了,朕掂量着些,不若一会子来些宵夜。”
碧溪这才颔首:“是,陛下。”
弋栖月立起身来,松了松筋骨,伸了个懒腰,心道这皇帝当真是不好当,忙起来更是没个始末,想来自己连今天下午同那三位的会都错过了,也不知那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是该寻些时候找程公公问问。
不过,宸卿在,应当不会有什么大事。
有这等想法,弋栖月一愣,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般信任他。
分明,之前可能还被他算计了一笔。
也许是因为他来的时间最长罢。
弋栖月心里算计着,已然信步溜出了殿去,想着透透气,散散心。
不想没走几步,便听见了那一番琴声。
她本是习武之人,行走江湖,刀尖舔血,也是有些时候的,对于声音,本就极为敏感,如今听了这琴声,也道应当是夜宸卿,犹豫了一下,终于举步循声而去。
这些日来,念及那晚她的所作所为,五味陈杂,却又似鬼迷心窍,不肯去瞧他。
她至今也不信,他有那般无辜。
一路上时快时慢地走着,直到那水边。
凉亭里,那抚琴的人儿凤眸微闭,着一袭月白色的衣衫,长发束起,随着他那广袖随风飘扬,依旧是如墨的头发,映着那皎洁的月光,如梦似幻。
弋栖月凝眸瞧了瞧他,轻轻咬了咬唇角,这才举步,轻声向前走去。
夜宸卿是爱琴的,自他入宫一来,便更爱抚琴了。
她向那一旁正欲行礼的侍从摆了摆手,示意不必做声,便举步进了那凉亭。
微风轻抚下他的长发掠过那瓷玉一般的脖颈,那出惨白的包扎愈发扎眼,她不着痕迹地又咬了咬唇角,上前半步,微微俯身,伸出手去,轻轻撩开他的头发,小心翼翼地触碰着那处伤口。
夜宸卿经她这一触碰,方才抬了眸,瞧见她,眸中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温度,他停了琴,正欲起身道一声陛下,却被她伸手按住。
弋栖月瞧着他那伤口,心知,在他锁骨处应当还有一处,再早些,在他手臂上,又有另一处刀伤。
她的心莫名的一紧,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抱怨,依旧是这般安静。
莫名的,脑海里浮现了那日情景,他昏过去的时候,依旧拦在她身后的,那一条手臂……
弋栖月咬了咬唇,忽而手臂一转,扶着他的头,俯身将他的头扣在怀中,侧了头去,靠着他的长发。
夜宸卿一愣,身形微微一震,他能嗅到她身上那如梅的冷香。
“陛下……”他低声唤着她,语气里带着一丝探寻。
而弋栖月却依旧抱住他,半晌沉声问道:“宸卿……当初在夜云天里,你应允随着朕回来,如今……你可是后悔了?”
夜宸卿一愣,启口道:“当初既是随着回来,便不后悔。”
弋栖月扬了扬唇,眸中闪过了一丝奇诡,又沉声道:
“……若是如今,朕告诉你,你还能出这宫门,离开这皇城,回到那夜云天,你可愿意?”
夜宸卿不着痕迹地颦了颦眉,声音却依旧是温润顺从:“臣下是陛下的人,若是陛下不嫌,不赶着臣下离开,臣下便日日呆在这宫里,陪着陛下。”
弋栖月闻言却不再言语,只是低下头来,吻了吻他颈项上那一处伤,她的气息在这一瞬间凑近了他,夜宸卿只觉微微发烫,却依旧是不动弹,像昔日里一样,格外的顺从。
她的吻便一路游移向上,顺着他白玉一般的颈项。
她的唇掠过他喉结的一瞬,夜宸卿的身形,不着痕迹地微微一颤。
夜宸卿一如既往地抬起手臂来,拦护在她身侧,这琴无人奏,本还有余音,如今已然哑了,女皇陛下的吻,伴随着的只有泠泠的水声。
可是,弋栖月的唇,只是停在了他的下颌,随后,她便抬起头来,又瞧了他一眼,然后,只是倏忽间,她直起身来,收了手,广袖一扬,转身便走。
这一切发生在短短的时间里,她来了,又走了,仿佛刚才她的触碰,她的话语,她的吻,都是水月镜花……
他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
夜宸卿微微扭过头去,望一眼她的背影,那背影孤寂而又高傲,仿佛一匹在黑夜里独行的狼。
他回了眼,手指在琴弦上撩拨,便有一串婉转的乐音,流淌而出……
弋栖月听见后面的乐音,不由得停滞了脚步,她凝了眉,侧耳听着。
晃了晃手腕上那木镯,感受着那质朴的触感,她的眸中突然闪过一丝凛冽。
方才还是一曲唱晚,如今,竟是一曲送别。
送别、送别。
究竟是无意之举,还是他再告诉她,他猜出来她要离开宫去?
夜宸卿,你当真要如此,揣摩朕的心思?
朕的心思,又岂容你肆意揣测?
几日后。
树上的蝉儿鸣得分外聒噪,眉山之上,时芜嫣的身影躲藏在一处小阁室里,她手里执着几柱香,面前的小桌上,零散地摆着些果品。
侍婢小菊随在她身后,瞧着自家小姐瘦弱的身影,轻声道:“小姐,日头高,小姐身子又热,这小阁子里没有加冰,小姐还是快些回房吧。”
时芜嫣闻言,手中动作一停,却不回头,只是沉声道:“小菊,你听,外面的蝉儿又开始叫了,小菊,你说,她可怨着我呢?”
小菊闻言一愣,知道是小姐依旧念着多年前被弋栖月隔门飞剑刺死的蝉儿,那日的剑直穿蝉儿的咽喉,蝉儿当场毙命,临死时怒目圆瞪,不向着门外,却想着立在那边的,她的主子——时芜嫣。
自此以后,时芜嫣日日惊悸,是了,原本她说,只是要蝉儿引来弋栖月,此后遁入这屋中,她自会保她周全。
可她时芜嫣食言了。
她立在门边,亲眼看着蝉儿被一剑穿喉,却连阻止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那次的计策,拖垮了弋栖月,笼络了墨苍落,让她时芜嫣,离着她心心念念的大师兄愈发得近了,可每每念及此事,她也觉得脊背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