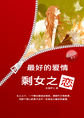“他们来找你了……”弋栖月眯了眯眼睛,笑道。
“被发现可是狼狈了点,宸卿,不若朕现在便走?”
夜宸卿这边面色淡淡朝外面瞥了一眼。
再然后,他手臂一撑半直起身子来,半靠在一侧的供桌桌腿上。
手臂顺手一环,稳稳地将她整个人拽到怀里。
这一瞬间,只觉得四下都被温暖包裹了。
不得不承认,当你被一个宽阔的肩膀牢牢抱住的时候,除非采用破坏性的手段,否则很难挣脱。
偏偏如今断不可能用什么破坏性的手段。
弋栖月轻轻动了动头,侧颜便碰上他垂落的长发。
有些凌乱,却分外温柔。
窝在他怀里,真的很舒服很满足啊。
偏头将面颊贴在他心口,贪婪地嗅着四下的苏合香。
可是逗弄他的念头偏偏也随着香气,渐渐浓郁起来。
外面鸣奏的是法事的声音,壮观之中隐隐有几分难言的诡异。
如今,现在,就在这里。
她眯了眯眼睛,勾唇笑道:“不让朕走,被发现了怎么办?”
夜宸卿抱着她的手臂又紧了紧,薄唇凑到她耳畔低低一句:
“不会。”
弋栖月笑。
窝在他怀里也不老实了,手臂一溜向下将他的腰封拽开。
今日他这一身朝服,挺拔而又规整,可惜愈是规整便让她愈想弄糟弄乱。
于是她得寸进尺一般地,一手勾着他的肩膀,抬头起来,蹭开他的衣襟,继而朱唇从他的颈项一路向上,偏偏对着而后延伸。
另一只手拽开他的腰封也不收手,指尖一绕探进衣衫里面。
她的手是微微凉的,他的身体却滚烫滚烫。
一冷一热的轻触都仿佛碰撞,更何况她只有起初是轻巧一挑,旋即便开始毫无征兆地肆意撩拨。
夜宸卿的身子不由自主地一凛。
可转眼间她便已轻轻含咬住他的耳垂,舌尖轻描淡写地轻舐。
一身朝服早已乱了,右侧的锁骨出露半方,上面掩映着的是垂下的发——紫金发冠更早地被她拽下来了,头发全是散的。
白日里规整冷清的夜君,只是片刻的功夫,就变成了北国女帝手下完美却又凌乱的猎物。
“陛下……”
耳朵异常得敏感,不知不觉已然开了口。
偏偏又舍不得大声,于是他压抑着掩饰着,低声开口。
如此声线却是低沉到了诱人。
弋栖月笑了笑,扣住他肩头的手一绕,从后面抱住他的颈项。
他的喊停分分明明起了反作用。
她钳制着他的颈项,却是轻咬着他的耳廓摩擦,同时另一只手自他结实的腰间寻了腰的中线,便沿着这一条线缓缓向下游弋……
夜宸卿不得不将颈子狠狠地向后仰去,可偏偏她的手臂栓得极紧,终究也只能将头后仰,却无法将自己的耳朵从她口中救出来。
偏偏是这么一仰头,从额间到眉骨,向下到纤长的睫毛,再到峻挺的鼻梁魅惑的唇线,和流畅得可以滴水的下颌线,浑然一体仿佛是千年打磨出的白玉石。
弋栖月这边眸子里闪过几分狡黠,另一只手却是忽而碰上衣衫里的另一处系带。
穿朝服果真是繁琐的,如今拆起来也是繁琐。
不过,倒也有趣。
动了动寻到那个冰凉坚硬的方扣,随后只听‘咔哒’的一声,她轻轻巧巧将扣子打开来。
身旁人的身子又是一凛。
夜宸卿咬住薄唇不肯出声,可是一呼一吸分明是粗重起来。
“陛下……”半晌,耳朵愈发烫红烫红的,终究是发出声音来了。
可也不过两个字,两个字说完又咬牙不言语了。
弋栖月在他腰际的手轻轻巧巧地把他的衣裳拽开,同时她一偏头于他耳畔笑:
“怎么了?”
“这里怕痒?”
夜宸卿低低哼了一声,声音有些粗重,然后偏了偏头。
不出声,可是大抵是真的敏感,又逃不开,于是红着一张脸,低喘着,睫毛控制不住地抖。
弋栖月知道,这厮是在默认她的话语,之所以不开口,大抵是怕传出声音去。
怕她走了吗?所以不想让外面人知道里面的动静?
心里突然意外地满足。
放过他可怜兮兮的耳朵,却是随意地将唇移到他恰好送到她面前的、颈子上那微抖的、诱人的凸起上。
故伎重演,一面随性地给他把衣裳拽下来,一面吻着他的喉结。
每每轻巧一舔,便能察觉到这厮将牙关又咬紧了几分。
分分明明是一副,誓死也不肯出声的模样。
末了女皇陛下坐在他腰间,面前的东国夜君,一个时辰前还是一袭规整的朝服,高傲冰冷地让人不敢直视,如今分明也是这一套衣裳,只可惜如今,发冠落了,长发散乱,右侧的半边衣襟已经乱糟糟地敞开来,腰封也给拽开了,下衣更是一派逶迤。
他却毫不在意一般,半垂着眼睛,呼吸粗沉,他咬着牙瞧着面前搂着他颈项的女皇陛下。
时不时狠狠咽下几口气去,只可惜能忍住的也仅仅是不出声。
“逍遥王爷……”
“逍遥王爷……”
外面依旧在有些急切地找寻着。
应当是夜氏的随从,发现主子不见了,又不敢闹大。
弋栖月听着声音勾起唇角,旋即眯起眼睛瞧向他:
“好不容易见上一面,你这厮却什么话都不肯说。”
“一声不吭的,怎么?不欢喜朕了?”
夜宸卿的眼睫毛抖了抖。
看着面前面色狡黠的女皇陛下,想说话却不敢开口。
旁的女子,怎么可能近他的身。
即便接近,又怎么可能能像她一样为所欲为。
更何况方才一席话,他将将把一切都挑明了。
而她还在这里嘻嘻笑着问他。
夜宸卿确定,陛下这是故意的。
好端端的见一面,还故意要这么折腾。
思量间他依旧没说话,可是陛下却不紧不慢地伸手出来,唇角勾着戏谑的笑意,要将他仅剩的衣衫也剥下来。
弋栖月心下舒坦得紧,瞧他的模样也知道伎俩被看穿了。
不过……
看穿了,才更有意思。
她弋栖月有个恶趣味,对于喜欢得紧的,就是喜欢欺负。
自然也只有她能欺负,自然也舍不得真伤着,可就是喜欢欺负。
为首的便是面前的他了。
笑嘻嘻地又凑近他:
“还不说话?真不欢喜朕了?”
“你不欢喜,朕可就走了。”
夜宸卿瞥了她一眼,一言不发默默扭过头去,抱住她的腰身的手臂,力道却是渐渐加大了。
明摆着要拴住她。
弋栖月发觉此等情形便又笑:
“好,你既是不肯,那朕来。”
夜宸卿一愣。
——陛下要叫出声来?!
有些愣愣地转眼瞧她,却正正对上那一对戏谑的眸子。
这个野狼一般的女子却勾了唇,低头凑近他,霎时间冷香扑鼻。
“怎么,还想管朕?”
“夜宸卿,来,让朕瞧瞧,你……拿什么管?”
夜宸卿略一皱眉眉,随后,却是缓缓地将薄唇送了出去,轻轻浅浅地吻上她的唇。
可这轻轻一吻,偏偏在触碰的瞬间,一发不可收。
不自觉间已经抱住她,狠狠地、肆意地,缠吻纠葛。
“这才听话。”
高傲的女帝,在四下苏合香围拢地一瞬间,如此低低而笑。
这一天逍遥王当真成了逍遥王。
外面响彻的是肃穆却又有几分诡谲的法事之声,游走的是小心翼翼寻找他的人众。
供桌只是一方大小,透过来的只有后方浅薄的微光。
桌布垂下,铺陈在下面的地面上的,是白日里规整严肃的朝服。
桌布封起的是一方空间,这之内没有烟火味,缭绕的是苏合香和冷梅香,这之内没有法事的舞蹈,窄窄一方唯有肆意纠缠……
有忌讳吗?
没有。
这二人心里都明明白白,这分明便是一场假的法事……
不知何时桌外的唤声小了。
却是无影注意到了这一方供桌。
大抵听了里面的响动,兀自红了脸。
却不多说,只是看似随意地立在供桌前,让夜氏的手下们停止搜找。
他默默立在那里。
心下却盘算着,不知一会儿主子会是何等情况。
今日这法事又该如何进行……
-
墨苍落收到一封久违的北国信件。
来信人正是北国的女帝陛下。
她在信中写着,她如今要离开西国返回都城,听闻苍流封山尚未结束,只怕再见面还需些时候。
只可惜如今天下动乱,时局变迁,她认为二人还是见面妥谈一番为好。
于是她说,既是苍流封山,他离不开,不若由她路过时去瞧一瞧他,只在苍流山脚下谈上几句便好。
墨苍落瞧着她那句‘西国探望故人归来’,只觉得心里左右不是个滋味。
当初百里炙的事情确是他所为,只是平心而论,他最初绝不是想杀了百里炙,可如今她两次提及,一字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却像是对他的控诉。
心里暗暗衡量着。
那个男子陪她不过几个月,而他足足瞧着她十几年。
时间本就是一道坎,兜兜转转总会留下最合适的。
就像她肯为他让夜宸卿离开一般,毫不任性,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墨苍落眉头紧了紧,随后又展开来,只想着月儿应当已经长大了。
兀自忽略那扎眼的一句话,他取了纸笔来回了一封信,只道若她不嫌奔波疲累,来见一面也是好的。
孰知方才将信件给侍从,时芜嫣便端着茶盏入了屋。
于是墨苍落随口道:
“弋栖月过些日子,应当会来苍流,同我谈些事情。”
孰知话音刚落,只听‘啪嚓——’一声,时芜嫣手里的茶盏已然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