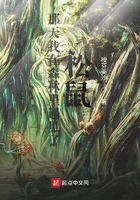总以为自己聪明,老是把别人当傻子的人,其实才是最大的傻瓜。
我现在就是那个大傻瓜。我自以为聪明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牢牢地捆在了这张病床上。
何慧这小妮子真是可以啊,我有点小瞧她了。慢慢回想她哪天晚上的举手投足,演技不是一般地精湛啊。
那天晚上的梨花带雨,那柔弱眼神里的恐惧无助,居然一整晚都在配合我的表演啊,高,实在是高。演技堪比奥斯卡影后啊。
慢慢回想她这两年和我在一起时的种种,越回想越觉得都是在演戏。就连那次聚会上求助的眼神都应该是演出来的吧。
对付我这么个老男人还真是下血本啊,图什么呢?真把我当成短期饭票,难道就是为了这两年的学费和那些手机,笔记本电脑之类的东西?
真要是这样的话也不知道我这两年的爱情买卖是赚了还是亏了。反正最后落得个结果就是被关在了这里。
我俩相互为对方上演了一出独角戏,只不过我演砸了,而她圆满谢了幕。曲终人散,我仍然还留在舞台上,而她已经捧起胜利的奖杯潇洒离去。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你必须圆满谢幕当下的角色,才能够获得登上新舞台的机会。获得有挑战性的新定位。
否则你就会和我一样,在一个舞台里打转,迷失掉自己。逐渐地懊悔自己演技的拙劣,却永远再不会有NG重来的机会。
屋子里慢慢响起了轻微的鼾声,两个义工看来是已经睡着了。
我慢慢地转动了一下手腕,果然绑带松了许多。那阵被按在床上的时候,我将手腕竖着立了起来,而且还用力地向上勉强撑了撑。现在一放平,自然就多出了一些活动空间。
右手顺利地从绑带里抽了出来,我又重新获得了活动的自由。我在黑暗中用脚轻轻地划拉着床边,可拖鞋却不知道丢到了哪里。
算了,没鞋就没鞋吧。光着脚正好还没有声音呢。就是伤口踩在凉凉的水泥地上还是有些疼。
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心翼翼地从那两张椅子边经过,轻轻地拉开门,我顺利地回到了只剩下昏黄灯光的走廊。
可我又该去哪里呢?望着那空荡荡的走廊,两边是一个个黑乎乎的病房。我反倒是迷失了方向。
我慢慢地向门厅挪去。拆了线的右脚疼的有些发木,好像已经没有了感觉。
门厅里依然亮着灯,亮的有些刺眼,看得我有些眼花。我转身摸了摸那冰冷的铁门,还有那依然无法拧动的门锁。
我用双手抓住门上的铁栏杆,将脸也紧贴了上去。门外的走廊里也静悄悄的,时不时传过来的是其他楼层的声音。空旷的楼道里仿佛都出现了回声。
可悲,可笑,真滑稽。我无奈地用头顶了顶铁栏杆。
“看啥呢?哥”一个男人瓮声瓮气地在我后边叫了我一声。吓得我差点没叫出声。
是44床,这个睡不着觉的黑大个子不知道啥时候跑到了我后边。见我松开手滑坐在了地上,他好奇地也把脸贴在了铁栏杆上向外瞅了瞅。
我站起身,没理还趴在门上瞅的黑大个子,快步向厕所走去。可能是光着脚有些凉着了,怎么突然就有些尿急起来了呢。
刚一进厕所,我和异形兄弟同时被吓得差点都跳起来。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他抬起头正眼看我,那眼神里恐惧的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动物。
今天晚上这是怎么了,难道都被我的举动吓犯病了。我缓了缓神,往最里边的小便池走去。
可我刚要拉下裤子又不得不转过身提了起来。
异形兄弟没再继续面壁碎碎念,而是直勾勾地站在那里看着我。
这我还怎么尿啊,都是男人也不好看我嘘嘘吧哥们。
异形兄弟这回没被我的回看吓跑,而是迈着小碎步快速地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反倒是被他打破常规的举动吓得下意识地抬起了手。
“看不见我。”异形兄弟小声地对我说道。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看,不,见,我?”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冲着他重复着自己听到的话。
大兄弟很很肯定地冲着我点点头,“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他又继续着他的碎碎念,倒腾着他的小碎步转身回了病房。
原来这就是他每天不停念叨的咒语啊,他这是把他心中的咒语给我用了吗?
我重新站在了小便池前,学着异形兄弟的样子面对着墙念叨起来“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我暂时放下了过去的生活,可我真的就消失了吗?要是这咒语真的管用该多好啊。好想偷偷去看看曾经的那些人和地方。
我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就是姑姑的脸。可咒语是不会灵验的,我要怎么做才能出去呢?
擦,一走神尿都落到脚面上了。我赶紧提起裤子走出了厕所。黑大个子44床靠墙站在厕所门口,见我出来嘿嘿嘿的冲我傻笑着。
望着都是护栏的窗户和那牢牢的铁门,我看不出病区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出去。
不对,好像有一个地方没去过。走廊那对对开门的里边可是有两间特别病房我还没去过。
我顾不得去找我的鞋,确切地说是我觉得这样没动静地走也挺好。
要经过那个傻乎乎的大背头待的值班室,还要经过那个海龟王八蛋的办公室,没动静还是挺好的。
一路顺风,两扇门里的办公室连灯光都没有了。真该砸进门干那个大海龟一顿。还主人呢,就说了所谓的帅哥都不是啥好东西。
我选了左边的那间病房,那间和大海龟的办公室斜对着,应该不会吵到他。
特需病房果然比普通病房高级得多。这里是里外两间的套间,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是一个长条沙发加一个木头茶几。
里间屋子里有一张单独的病床,病床正对着的墙上则是一台液晶电视。
我关心的可不是这些,我关心的是那扇窗户和窗外的护栏。那是我寄寓厚望的逃亡通道。
里里外外地看了大半天,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躺在了病床上。看来这病区唯一出入口就是正厅的铁门了,我该想什么办法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