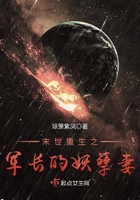余向东的死,震惊了省公安厅。
一个年轻有为、被当地警方寄与厚望的刑警队长,白天横死在闹市的街头,手段之残忍、影响之恶劣,省厅在震怒和深感情况复杂的同时,下决心彻查。
查!无论背景多复杂,一查到底;无论牵扯到谁,决不姑息。
关于余向东的死,有多个流行的说法。其一,死于情杀。——这也是人物风流的余向东,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其二,死于仇杀。锋芒毕露的刑警队长,黑道白道得罪了不少人,这些能量不小的人,都希望着余向东死。其三,也是最为夸张的,说余向东死于政治陷害。
也不怪大家关注,谁叫余向东背影特殊,又是小城的杰出青年呢?
风传着的每个版本都煞有介事、绘声绘色。谣言一时满天飞,省厅不重视都不行。
那个既是白天、又在街头,并且富于戏剧性的刺杀,省厅想想就头痛,想捂一下、低调一点都不行。
为了对上对下有个交代,省厅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限期破案。
师立言,年轻能干的刑侦专家,被省厅寄以了厚望。
同样,师立言把熟悉小城的龚晴抽到专案组,也寄于了厚望。
小城土生土长的龚晴,精明能干、貌美如花。最重要的是,师立言喜欢着她。
师立言初识龚晴,缘于一次交通意外。
多年前的一个傍晚,骑着自行车的师立言匆匆地往警官学院赶。开初迷雾重重的一个重要的案子,师立言有了脑洞大开的想法,想去请教学生时的老师。
学校路口处的一个转台,一个栽满植物、同时也挡住了视线的花园处,低着头的师立言,撞向了迎面走来的一个女生。
“对不起,对不起。”撞倒女生的师立言,忙不迭的道歉。“怪我,是我没注意。”
脑子里装满了案子的师立言,才发觉赶时间的自己,不仅没有抬头看路,还逆行了。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旁边一个短发女孩生气的说。
不怪女孩生气。逆行、速度快,还低着头往女孩身上撞,不是轻薄少年的故意找事,是什么?
自知理亏的师立言,除了道着歉,手忙脚乱的帮着捡拾散落一地的东西外,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要紧的。”在短发女生搀扶下,被撞女生站了起来,落落大方地说。
站起身来的女生,让师立言眼前一亮,这个秋天灰朦朦的傍晚,刹那间被点亮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这是一幅图画。是师立言特别喜欢的那幅“少女出浴图”的真人版。
同样是青春靓丽,同样是双手持盆的浴后女孩,同样是打动了师立言年轻欢快的心。
既一样又不一样。眼前的女孩鲜活、整洁,秀发湿漉漉的打在肩膀上。
“哎!哎!”大概是师立言“目炯炯似贼”,引起了误会,短发女生说,“没见过女生还是耍流氓?再拦着,我们报警了。”
“对不起、对不起。”失态的师立言慌张着让开被自己堵住的道。
那晚,师立言久久地伫立着。女生离去的背影已经消失在远处,他还在那里回味着。
他脑子里在迟钝的想着:我还没有问女生的名字,我要不要追上去搭讪?直到女生的背影从视线中消失了,他还在不停的想,其实我完全可以追上去的。
他忘记了刚才急着要做的事。
是秋天傍晚的风的吹醒了怅然若失的师立言。他笑笑,为自己的失态很不好意思。撞倒她在先,再追上去纠缠,不是让人讨厌的登徒子,也说不清了。
女孩面前,这是师立言绝无仅有的一次失态。
那晚,走出导师家的师立言,被学校餐厅里合唱的女声所吸引,不知不觉走了进去。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我们同忍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共风雨,我们共追求,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
倒数第二排左边,秀发披肩的那个女生,不就是傍晚出浴的那个女孩吗?
抒情欢快的歌声引发了师立言的共鸣。他真心觉得,这唱进了心里的歌,是专门为他而唱,这感动人的情和景是专门为他而设。
他记住了秀发披肩女生的名字:龚晴。
像个初涉情事的小男生似的,他找到了那种打心里喜欢一个人时,甜润的、悠然心会妙处难以君说的美妙感觉。
之后的那段时间,师立言为案子的事忙得焦头烂额。
也许是命运的玩笑,在师立言一心想要谈情说爱的时候,偏偏抽不出那怕一小块的时间。可不论再忙,他都会想起那个秋天的傍晚,那个女神般存在着的龚晴。她那灿若星辰的双眼、那清澈激越的歌声,像一道暖流温暖着他。
他把她视作生命里,注定了的那一个。
注定了的人是不会错过的。龚晴会一直等着他,等在下一个空旷的十字路口,等在下一个山花灿漫的地方。
意外的是,当他终于忙完手里的案子,可以暂时地缓上一口气,做准备了不下一百遍的事时,手捧着鲜花的师立言,才发现身着新娘装的龚晴,走向了婚姻的红地毯。
“师兄,你是来祝福我的吧?”喜气洋洋地龚晴说,“师兄百忙中能来,我已经很高兴了,还送我这么漂亮的鲜花,真的让我意外。”
师立言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龚晴心里说:不请自来,还捧着大把的鲜花,好像和女朋友约会似的。
“我才真的意外呢!”一脸惊愕的师立言,是真的非常的意外。
除了意外,失望、沮丧、以及无地自容的尴尬,一起涌上脸来。好在他风吹日晒粗糙着的脸,就算变了颜色,龚晴也没有看出来。
——这是美好的童话故事开头、残酷现实结尾的一出肥皂剧。
忙得没时间对追女孩,甚至没来得及表明心迹的师立言,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脸上除了堆着笑容、尴尬得张口结舌外,连横刀夺爱的想法都不合时宜。
把新娘从婚礼上抢走,不是不可以,可那得是身骑着白马的王子才行。
师立言显然不是龚晴的白马王子,一脸幸福、高大英俊的新郎才是。
这是师立言一生中最为尴尬、也是最为失望的时刻。
对于师立言而言,邂逅龚晴,是一个美丽的意外;龚晴和别人携手踏上婚姻的红地毯,是一个糟糕的意外;脱下新娘装的龚晴很快解除了婚姻,又是一个意外、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意外。
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意外。
小城。?专案组成立的第二天。
上午十点三十分,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走进了任秋实所在的办公楼。
春天的阳光,洒满了任秋实的办公室,也洒落在推门走进来的两个警察身上。
“龚晴,怎么是你?”听到开门声的任秋实抬起头来,不相信地看着走进来的龚晴。
任秋实听余向东说起过龚晴,说她在省厅上班,小城基本不会回来了。
——余向东说的根本不对:小城不是又见龚晴了吗?
余向东说起龚晴,是什么时候的事?——对,上个星期五,他们把对方打爬在地上的那天。
“我们几天前才说起你。”任秋实迎上前去,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知道今天会是个好日子,可没想到会美梦成真。”
任秋实摇着龚晴的手,对被冷落在一旁,看上去是头的警察说,“对不起,我跟龚晴多年没见,一时高兴失了礼,请多谅解。”
这个看上去比龚晴年长几岁的警察,理解似的点着头,笑笑。他心里在想,这个任秋实看上去聪明热情,是个有涵养的人。
两个人握手的时间,似乎太长了。龚晴的脸上微微一红,挣脱了他的手,多少有些惊讶的说:“你们说起过我?——你们都是谁啊?”
“还能有谁?我和余向东呗。”?任秋实理所当然的说。
任秋实实话实说。那天他和余向东说到了龚晴、龚晴市高官的老爸。余向东约任秋实过天一起去找龚晴,通过龚晴见下龚书记。
这是余向东和任秋实打了一架、喘息稍定后,认真强调的事。
——也是奇怪,那天打的架,余向东没有心存芥蒂,心里憋着的任秋实,气也消了不少。
人有时真不经念叨,几天前他们才说起龚晴,今天龚晴就站在面前了。?这下好了,省得他们去省城折腾了。
对于龚晴出乎意料的到访,任秋实想不出别的理由,只能往不久前被人打闷棍的事情上想。
余向东几天前说,塘双巷他被人黑打的事,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现在,面对着制服在身的龚晴,任秋实不由得想,那天的事一定是有了眉目,才会有今天警察的正式拜访。
“这点小事,其实不用你们亲自来,一个电话,我就过去了。”任秋实心里高兴,满脸笑容的说。
省厅的龚晴,为一个寻常的案子亲自前来,既让任秋实打心眼里高兴,又让他生出疑惑:余向东说的足够重视,还真惊动上面了?
也许打闷棍的事顺藤摸瓜,牵扯出了什么大案要案吧?他心里揣测着。
刚才提起余向东时,任秋实注意到龚晴和同来的警察,交换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眼神,似乎同来的警察和余向东也是熟人。——任秋实理所当然的想。
“任秋实。”龚晴对同来的警察介绍说。
“师立言。”同来的警察微笑着和任秋实伸手相握。
“您好!”任秋实热情地笑着,对这个成熟稳重、眼睛炯炯有神的的警察,很有好感。“谢谢你们前来。”
有的人认识不到三分钟,就让人有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眼前这个亲切友善的警官就是。
“不客气。”师立言的举止,和他的声音一样亲切。“我们来,是为余向东的案子。相信你能给我们帮助。”
师立言坦诚地说。刚才任秋实和龚晴的对话,让他知道,这个任秋实和余向东关系很不一般。这让他对今天的到访很有信心。
余向东的案子?——半晌才反应过来的任秋实,满脸的惊讶:怎么会是余向东的案子?
任秋实难过的想:莽撞有余、智慧不足的余向东,终于还是闯祸了!
这个不理智的家伙,早就苦口婆心地跟他讲,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他老爸那种江湖水太深,不是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辈玩得转的。要三思、要量力而行,偏不听,这下闯祸了吧?
——余向东有枪!对余向东冲动有一定了解的吕美净,曾担心的说。
没想到担心着的事,终于还是来了。只是,吕美净的担心,是怕他对任秋实不利,而不是这个。
余向东的冲动,和他们的担心南辕北辙,完全不在一个方向。
不怪这两天没有余向东的消息。任秋实忧心忡忡:省厅的警察亲自前来,意味着有枪的余向东闯祸不小。
“余向东惹下什么事了?”任秋实不想吓自己,可事态可能真的很严重。“刚才我还以为是我的事呢。”
为缓解自以为是的尴尬,他自嘲的笑笑,说。
——也是,街头莫名其妙被黑打,在你是天大的事,人家那里就是鸡毛蒜皮。
“你的事?”龚晴皱起了眉头。
龚晴注意着任秋实的一举手一投足。她看到他蹙着额头抚肩的动作,似乎肩膀那里伤痛似的。
“哦,没什么,真没什么。”任秋实说起了那天的事,最后笑笑说:“他们说可能是抢劫,也可能是报复,我刚才还以为有结果了呢。”
师立言留神地听着。任秋实被打闷棍与余向东被袭,这两件事似乎并不相干,但放在一起,就有些耐人寻味:同样在街上,同样是白天,同样背后偷袭,难道真的是纯属巧合吗?
师立言心里摇着头。他对任秋实更感兴趣了。
“余向东跟你是同学,并且一直有来往,是吗?”
“是的。”任秋实回答。——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你们关系怎么样,有没有过冲突或者矛盾?”
来了,任秋实心里暗自警惕:这是一个陷阱!他们想顺藤摸瓜,调查我是不是余向东的同伙。
“没有过冲突,也没有矛盾。”任秋实正襟危坐。“我们关系一般。”
撒谎!龚晴心里说,你们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前几天,也就是5月20号,余向东到你这里来过是吧?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或者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没有说什么。”任秋实小心的说,“就是家长里短的闲话。也没看出他有什么不对劲。”
这话不尽不实。他们那天破天荒的打了一架。余向东后来还约他去省城找龚晴。
“你可能还不知道?”师立言看出任秋实的担心,心里想,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敏感、小心得过了头的年轻人。师立言不太了解任秋实,可从年轻轻的就当上重要部门的负责人来看,一定有其过人的地方。
现在,师立言理解似的笑笑,说:“5月20号,也就是余向东从这里出去后,在新兴路上遇害身亡。”
“什么?”大吃一惊的任秋实,从坐位上站了起来,情绪激动着,“这怎么可能?!”他说。
他摇着头。?这不是真的。他们在跟他讲一个黑色的笑话,可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不愿相信的他,愕然看着面前的龚晴,看着师立言。
他们是警察。他们严肃认真,一点都不像跟人开玩笑的样子。?哦,这难道是、是真的?
他颓然倾倒在椅子上。——这当然是真的!
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
悲从心来的任秋实,这时是无尽的后悔。后悔之前没能好好的珍惜,后悔曾经的不满,后悔对马青青动的歪心思。还有,那天他是发什么疯了,要打那混帐的一架?
“那天他跟你说了什么?”师立言说,“你知道他有什么仇人吗,或者都得罪过什么人?”
任秋实耳边,师立言的声音时断时续般飘忽着。声音似乎从信号不好的远方传来。
“你说什么?”悔恨着任秋实,听不清师立言说了些什么。
“他得罪过、或者有什么仇人?”师立言提高着声音说。
“没有。”这次听清了,他瞥了眼龚晴。“没有。”任秋实摇着头。
——余向东当然有仇人。他的仇人是龚书记、龚晴的老爸。
“你再想想,那天他说了些什么?”师立言有些着急。显然,他对任秋实失望了。
余向东说:我们一起去找龚晴,帮我说说老爷子的事,让她求龚书记放我老爸一马。他还说:我的话,她权当放屁。你不同,她对你印象很好。你去说,她肯定给你面子。
“没有。”他肯定的摇头说,“就是朋友间的闲扯。全是不相干的话。没一句是他得罪、或有人对他不利的话。”
也对,警察得罪的人,都是些为非作歹的混蛋,书生似的任秋实不清楚不足为奇。师立言心里说。
这家伙——龚晴看着神态恢复平静的任秋实,赞赏的想,还是这么整洁、灵敏,岁月刻下的印痕,不仅无损他的俊朗,相反地,让成熟的他更显魅力了。
小城。新兴路。
早晨阳光下的大街,车水马龙。站在街上的龚晴,心里的时光回到了过去的青葱岁月。
岁月匆匆。春天的小城更显妩媚。多年前,这条大街上匆匆前行着的那些少男少女,却早已风流云散了。
那时的少男少女今何在?任秋实、她,对了,还有马青青,算得上硕果仅存吧?
“师兄,你怎么看?”回过神来的龚晴说。
“任秋实吗?”师立言感觉得到龚晴的愉悦,春风满面、眼睛水盈盈的她,看上去就是一个怀春的少女。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在心里说。
“思维敏捷、谈吐不俗。”师立言不假思索的说。
他在想,任秋实是他所认识的年轻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无疑地,也是对龚晴最具吸引力的那一个。还有,让他不得不担心的是,任秋实对龚晴,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
“你是说他耍小聪明?”龚晴敏感地看出来,师立言其实并不喜欢任秋实。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说。”师立言哈哈笑起来,心里想,龚晴太敏感了,可不能让她认为自己是小肚鸡肠。
龚晴和任秋实可不单是老同学那么简单。师立言心想,龚晴对任秋实那种近视于小女生对白马王子的好感,眼睛不好的人都看得出来。
师立言感到了来自任秋实的挑战。但他不怕。他已经准备好了。
师立言心想,在爱情的路上,他们互有优劣。他的优势在于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于历经岁月对龚晴不改的初心。任秋实的优势在于他们是同学,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目前看来,似乎他胜算较大。可任秋实要是也死心塌地、非龚晴不娶呢?究竟花落谁家,还真是说不清了。
师立言心里想:我再也不会让人把龚晴夺走了。谁也不行。
春天的太阳,落向了大山的另一边。
华灯初上,位于城北的博览馆里,省里巡回的摄影展,正在小城如期举行。
任秋实去找龚晴,得知龚晴去博览馆了。于是他立马赶到了博览馆,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龚晴。
博览馆二楼的一侧,挂着两幅龚晴参展的作品,其中一幅“行刑的少女”,反映的是贩毒的女孩,被执行死刑前的一个瞬间。
图片上,花季少女的美丽与空洞,透过光线的应用和构图的处理,具有了一种憾动人心的力量。
任秋实不懂摄影,对摄影的立意、构图、用光、色彩,一知半解。但他知道,兰心慧质的龚晴,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
这幅视觉和心灵都予人以震憾的作品,就算是妙手偶得,可从作品反映出的专业造诣来看,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了。
“老同学,怎么,对摄影感兴趣?”
龚晴走了过来,看到任秋实留连在自己的作品前,喜滋滋的笑着说。
这正是任秋实所致力营造出的结果。
“还行。”任秋实开心的笑了起来,心里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特别喜欢这幅‘行刑的少女”
他指着墙上的作品说:“无论是立意、构图和用光,还是色彩的运用,都恰到好处,赋于了画面一种震撼般的张力。”
这家伙,夸夸其谈,却又头头是道,好像他很懂似的。——龚晴有些喜出望外了。
“你知道我不会说好听的话,我只能说作品很深刻,我真的很喜欢。”
他腼腆地说,对于说赞美的话,好像怕人误会拍马屁似的,有些不好意思。
这话我爱听。龚晴有些轻飘飘的了:这家伙,尽捡好听的说,还说不会说好听的话,假了吧!
“说吧,找我什么事?”龚晴端正身姿,得意地笑着,一副知道你不怀好意的样子。
“你知道我找你?”任秋实有些惊讶。
龚晴矜持的笑笑,眼睛看着他,一副一切都在本小姐掌握中的神态。
一向清高的任秋实主动找她、说着好听的话——这是套近乎讨好我呢,她想。这不像他的为人,如果不是有所图谋的话,很难想像任秋实会讨好人。
有所图谋、有所图谋,她猜测着,发觉自己不仅没有反感,相反地,还有些期待了:俊男对靓女,会图谋什么?
“我想,”任秋实挠着头,眼前的这个场合闹哄哄的,似乎不太适宜私聊。“我想、我想道歉。”憋了半天,他红着脸说。
龚晴“卟哧”一下,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太搞笑了”,她掩着口,瞅了似乎手足无措的任秋实一眼,“走,请我吃烧烤。”她不容分说的说。
小城灯火通明的烧烤街,烟熏火燎地冒着腾腾的热气。
一张简易的小桌前,龚晴和任秋实相对而坐。
“太好了,闻着味道就香。”龚晴一副好心情地轻笑着说,“在省城,最恨的人是任秋实,最怀念的美食是小城烧烤。小城烧烤,做梦都会梦到,嗯——太美味了,怎么只是看着我?快,一起吃!”
“我怎么、怎么成你最恨的人了?”任秋实口吃起来。
知道龚晴口直心快,可才落座就这样毫不留情,也太出乎任秋实想象了。
“你说道歉,不就是因为对不起我吗?我还以为,有人终于良心发现了呢。你说,对于对不起我的人,我怎么就不能恨了?”
也是,任秋实一直为过去的事抱歉,刚才也说要道歉来着。仔细想想,笑笑,心里却喟然长叹。
“怎么,不想说、不好说、有难言之隐?”
“那时太年轻!”任秋实喟叹着说。
龚晴笑笑,任秋实也笑笑。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似的。
过去那种有温度的青春又回来了。她笑吟吟的看着着他,以手支颐,仿佛那过去了的青葱岁月,还在余音袅袅中。
烟雾缭绕着的这个夜晚,龚晴主动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她的工作、恋爱和婚姻。
她轻描淡写地说着,好像那个被伤害而离了婚的小妇人,是另外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人。
龚晴不是一个喜欢说自己的人,特别是那场失败了的婚姻。她从不愿、也从没对人说起过。可这个轻烟弥漫着的晚上,不知怎么的,她却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这是一种缘份吧。有的人朝夕相处,却仍然陌生;而有的人,只须一个眼神、一句问候,就会让人温暖、让人敞开心扉一吐为快。
这个露天的、天幕上繁星似锦、街道两旁轻烟弥漫的烧烤摊上,和龚晴相对而坐的侃侃而谈,让任秋实回到了同看露天电影的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青春靓丽的龚晴也是这样的坦率、热情,让任秋实深觉温暖。
“这么说,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了?”龚晴看似漫不经心的说。
这让任秋实怎么说呢?
他想起了马青青。马青青说,她现在只想着把孩子生下来哺养成人,让任秋实不要再去烦她。
任秋实同时想起了伤透心而不知所踪的吕美净。她的不辞而别,不就是为了不想见他吗?
还有,为了他不受到东方飞的伤害,情深而绝抉的林秋抒。
生命中的女人,一时间纷至沓来,又在不经意间一一远去。
俱往矣!心里沉痛而伤悲着的任秋实,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抬起斟满了酒的杯子,一饮而尽。
——那晚,为马青青伤透了心的他说,酒来!举杯一饮而尽。结果,又伤害了吕美净。
千言万语,尽在这一饮一啄、皆是前定间。
“是的。”他无力的说。?一饮一啄,皆是前定。
他有一种无力挣扎的沧桑感。?垂头丧气盯着手里的空杯子的他,心里充满了苦涩。
“别这样!”深有同感的龚晴说。
这是一个外表坚强,心里却有着太多痛苦的大男孩。龚晴悲从中来,有一种和他一起痛饮、一起痛哭的冲动。但她忍住了。
现在,她轻抚着他那有着厚实茧子的手。——这不是读书、坐办公室,而是积年累月干苦力的人,才有的手。
他说起了那苦役般漫长的三年。
那苦役般的三年,牛马般的苦还在其次,看不到明天的无望,才最让人煎熬。
他的心酸让她忍不住。
“别这样!”她轻抚着说,像是安抚一只受了伤的老年狗。
他点头,对着温婉的龚晴,心里有一份愧疚,也有一份感动。为生命中遇到的龚晴、马青青、吕美净,以及林秋抒而感动和愧疚。
一饮一啄,皆是前定。
第二天。中午。
龚晴电话,让任秋实晚上八点去见龚书记。她晚上有会。她说龚书记会在家里等着他。
傍晚七点零五分,任秋实走出了家门。
去龚晴家,走路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对于去见百忙之中的龚书记,去早去晚都不合适。任秋实必须按约定的时间准点到。
天上飘着傍晚的细雨。有风。斜风细雨里,任秋实的雨伞迎着风斜撑着。
阴雨的傍晚,天空灰蒙蒙的。没有红绿灯的街心花园,斑马线的一侧,几辆主动减速停下来的小汽车,礼貌地让着行人通行。
任秋实感激于小汽车的文明行为,加快着脚步快速通过。当他越过斑马线的一半时,一辆从一侧突然冲过来的小汽车,在任秋实不及避让的刹那间,猛地撞了过来。
糟糕!任秋实只来得及在心里惊叫一声,小汽车“嘭”地撞到了膝部,紧跟着是头部撞到汽车挡风玻璃的闷响声。
斜风细雨里,任秋实的身体飞了起来。同时,他的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淅沥沥的雨声中,任秋实醒了过来。他看到自己躺在马路的旁边。天开始黑了下来。街旁的路灯亮了起来。
雨声大了起来,浑身湿淋淋的他,躺倒在斑马线一侧、隔离栏杆的旁边。他记起了刚才的事。
岂有此理!——他不由得怒火在胸中燃烧。
愤怒使他挣扎着坐了起来。
旁边的人说,撞你是辆银色的面包车,已经跑了。下雨天黑也没看清。已经报警了。
怎么回事啊,任秋实既愤怒又不解:前几天才被人从背后偷袭,现在过马路又被车撞,还让不让人活了?
“死亡!”任秋实记起了老妪女巫般的预言,她说,“死亡包围着你!”。
死亡!死亡!死亡!!女巫魔鬼般的声音在街上回荡着,并且越来越大,震得他的脑子轰隆隆的痛。
任秋实才被车子撞击的脑袋,难以忍受地疼了起来。
雨水淋透了的他,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还以为女巫预言着的死亡,应验在余向东身上,已经没他什么事了,原来事情没有完。
不,绝不能认输。他必须坚强地站起来,与置他于死地的命运博斗!
他记起了刚才要做的事,龚书记在等着呢!
——说服龚书记,是余向东的嘱托,也是他死前最后的愿望。
我已经够对不起好友的了。现在,我绝不能继续呆在这里。——任秋实对自己说,我必须去见龚书记。现在。马上!
内心坚韧着的信念,让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摇晃着迈开了步。开头腿有点僵硬,走了几步后,好多了。
他不禁暗自庆幸:幸好撞他是自重较轻的面包车;幸好撞上他时,速度不太快。
这才是不幸中的万幸呢!
回家梳洗后换了身干净衣服任秋实,忐忑不安地摁响龚晴家的门铃时,已经是晚上的九点三十分,距约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半小时了。
他可以向龚晴解释、向龚书记解释。想必他们都会谅解。毕竟,迟到是因为该死的车祸。
“来了!”室内答应着,声音柔柔的似曾相识,却不是龚晴清脆的声音。脚步声随之响起,房门打开,林秋抒站在打开的房门口。
任秋实吃惊得眼球都要掉下来了!——这就是一个梦,一个日有所思、梦有所得的梦。——这当然不是真的!
林秋抒鲜活地站在那里。有声音,有呼吸。——这不是一个梦。
这当然是真的。
任秋实哽咽着。他有太多憋着的话想说:抒姐你去哪了?知道我在找你吗?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吗?抒姐,你还好吗,东方飞没有为难吧?
他却只能止住哭泣,到了喉咙里的话,咽回肚里。因为,这是龚晴的家。龚晴的老爸还等在屋里。
“抒姐,你、你也是来找龚书记吗?”任秋实无法控制、却必须控制行将崩溃的情绪,泪眼朦胧的他,心里有千言万语,临了,竟无语凝噎。
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不。”同样泪眼朦胧的林秋抒说,“这是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