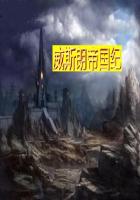Stand in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Now face North
Think about direction
Wonder why you haven't
Now stand in the place where you work
Now face West
Think about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Wonder why you haven't before
If you are confused check with the sun
Carry a compass to help you along
Your feet are going to be on the ground
Your head is there to move you around
R.E.M., "Stand"
减去三十二,乘五,再除九。晓野兔子说。
减去三十二,乘五,再除九。胡熊说。减去三十二,乘五,再除九。他已经记不清这是晓野兔子第几次传授这口诀了。
嗯,就这么几个数字,怎么老忘啊。晓野兔子说。您真是学工科的吗?不会是偷渡来的吧。
这儿太热,我智商下降了。而且我这不是手里有活吗?胡熊抬起那盆搅拌很久的面糊,耸肩抹掉耳垂吊挂的汗珠。一百二减去三十二。八十八。八十八乘五是?五八四十。四百四?四百四。四百四除九是?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百六。四百四减三百六是八十。八十除九差不多是九。那么结果差不多是四十九?
嗯,算得真快。怪不得他们给您奖学金。太热和智商下降有什么关系?
您知道分子热运动吗?温度越高,信号传输的噪声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人发了高烧就神志不清,要敷上冰块。
胡说。晓野兔子看着他,将信将疑。胡熊发现这是种新表情,得意地笑了。虽然才认识几天,他已经发现了她的很多种表情。他尤其喜欢这一种。他喜欢被崇拜,虽然自己确实在信口开河。这说明自己的智商还没下降。
您不懂也正常。好吧,华氏一百二十度等于摄氏四十九度--行,记住了。胡熊点点头,继续搅拌面糊。本厨房气温现在是摄氏四十九度。还是摄氏度好,听起来没那么夸张。那天我给我妈打了个长途电话,说本市近日最高温度一百度,最低温度九十度,她老人家也说我胡说。
嗯。您小名就叫胡说。晓野兔子继续掰生菜。
在工科博士生眼中,世间万物都是用数字定义的,刚来美国不到一周的胡熊却有点系统紊乱。或许确是因为天气太热。或许有别的原因。比如,昨晚在公寓喝酒,晓野兔子指着啤酒瓶的标签一字一顿地向他解释说,这瓶里装着十一点一五流体盎司。十,-,点,-,五,流,体,盎,司。他只看着晓野兔子的纤纤玉指,心不在焉地说:这差不多也就顶半瓶燕京?要不咱一人再来一瓶?
又比如,胡熊刚买的车有十四加仑的油箱。他不知道这容积是多大,只知道油表指针跌进红线,就要找加油站了。汽油每加仑九毛九。他不知道一加仑有多少。他甚至没看见油,他只知道油从加油站的地下油罐通过油泵流进了油箱,油泵上的数字在跳,他的心也在跳。因为当时他口袋里只有几块钱。他必须迅速找到工作。
再比如,为进城找工作,胡熊跑了三百英里,三百英里大约等于五百公里?总之,这段路他跑了大半夜。若不是只学了一天车就上路,他能开得更快些。
容积和距离实在是很抽象但又无关紧要的概念。路再远也还是要走,油再贵也还是要加。酒不管有多少流体盎司,都会被消灭。温度不一样。哪怕您老老实实待着,温度还是能要了您的命。胡熊想起刚进城那天在车里过夜的惨状。更何况我还在这儿做机械运动。此刻,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成了小小的泉眼,汗水不断涌出,积聚成珠,从额头滚到下巴,从后颈顺脊梁下滑。胡熊没功夫去擦这些调皮的汗珠。他只能抽空用前臂抹掉挂在睫毛上的汗珠,或是耸起肩,用T恤上还算干净的那一片擦擦湿漉漉的耳朵。
真热啊,是不是!站在晓野兔子另一边的圣子桑看着胡熊微笑。当然,圣子桑自己也好不到那儿去。她脸上的妆被汗水侵蚀着,脸颊边隐约可见两条汗珠滚落的痕迹,眼镜片似乎都蒙了一层水雾。胡熊看着她的微笑,心也静下来--年过半百的老太太都能挺住,何况大小伙子。现在是华氏一百二十度,摄氏四十九度。胡熊微笑着向她报告。他知道圣子桑听不懂他们刚才的对话。
坚持住!很快就会凉下来。圣子桑说。若不是手里也忙着剥生菜,她肯定会拍一下胡熊的背。胡熊是新手,她这两天总这么拍他,以示鼓励。
堂哥刚把饭锅和酱汤锅的火关掉,在桌子另一头大厨专用的案板上切胡萝卜丝。胡萝卜丝是用来配生菜的。这标志着厨房里做饭熬汤之类的工序已经完成。炉灶熄火,气温就会从一百二慢慢跌下来。惟一开着小火的是胡熊背后那口大油锅。按堂哥的教导,油锅要先预热,单子进来就能迅速开炸。
但胡熊此时依然在搅拌他的面糊。面糊不备好,油锅再热也是白搭。他还没掌握这门手艺,加了面粉又加水,盆里的内容渐涨。刚才趁堂哥不注意,他又往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晓野兔子建议的。
沙漠里估计也就是这个温度吧。胡熊说。
嗯。怎么,扛不住了?晓野兔子说。
还行。不过时间长了我是不是也会升温到摄氏四十九度?热传导我是学过的。
您该学生物。您不是在出汗吗?出汗能把体温保持在三十七度。体温四十几度您就死掉了。
有什么动物的体温是四十九度以上吗?那就不会出汗了吧。
好像没有。哺乳动物的体温好像和人类都差不多。好像鸡的体温挺高的?
鸡不算哺乳动物吧。没见过它们有乳房啊。
嗯。嗯?您是不是热坏了?
哺乳动物不是都有乳房吗?那鸡算什么动物?
鸡?
嗯。
鸟类?
因为有翅膀,所以是鸟类。您是不是也热坏了?
干活,干活!堂哥的声音像几只破空而来的乌鸦,惊开两只咕咕低语的鸽子。你那个面搞好了没有啊!
好像是好了!要不您帮我看看?胡熊大声报告。
堂哥用菜刀把切好的胡萝卜丝码进保鲜袋,沉着脸走到桌子这头,接过胡熊奉上的面盆,用两个手指挑起些看看,说,可以啦。你打了几个鸡蛋啊!不要钱的是不是?把桌子收干净!说罢把面盆推进胡熊怀里,解了围裙擦擦手扔在桌上,取下耳朵上夹的烟卷,拉开厨房后门出去了。
鸡算是鸟纲。哺乳动物属于哺乳纲。这些我还是记得的。晓野兔子有了片刻考虑,迅速接上话题。
对了,什么动物既有乳房又有翅膀?
这个,好像没有。
天使是不是?天使好像都是女的?
天使都是不生小孩的,要乳房干啥?对,我记得天使好像都是男的?
我怎么记得画上的天使都是女的,还都穿着裙子……胡熊正搜索着记忆,厨房前门突然开了,有客人!安迪的头伸进来,撂下这句话,侦察兵般消失了。
来了!晓野兔子的声音追出去。
来了!来了!圣子桑说。她不懂汉语但经验丰富,自然明白安迪说了什么。
帮我们把生菜泡在凉水里。晓野兔子用英语大声吩咐。胡熊知道,这种指令,是胡熊作为餐馆雇员应该做的,若用汉语,便是凭私人交情帮她。晓野兔子把装生菜的大盆推给胡熊,用小指理理发梢,推门奔赴前线。她一头短发不需要打理,虽然脸上泛些红晕,但竟然没有出汗。胡熊目送她的背影。门开时一阵凉风从大堂里飘进来,令他神清气爽。
谢谢!圣子桑钻进储物间,从手袋里找出化妆盒,拍拍呆立着的胡熊,从厨房后门出去了。她要去卫生间补妆。
胡熊打开水笼头冲着生菜叶,也冲着他的双手。这清凉仿佛来自北极。滚热的血液骤然降温。
光用凉水不行!拿过来加冰!安迪突然又冒出来。他掀开制冰机的盖板,往胡熊端过来的生菜上面加了好几铲冰块。要用冰镇上,菜叶才会新鲜,才会脆,知不知道?安迪拿起一片菜叶在胡熊面前晃晃,扔进嘴里,又侦察兵般消失了。
胡熊四顾无人,抓起几块冰塞进嘴里。冰块如蜜糖般融化,薄荷般的凉气透过上腭进入大脑直冲顶门,随血液流遍周身。他感觉自己就像一片蔫了的生菜叶,又重新挺起来。
胡熊当初进城找餐馆打工,未曾细想是要端盘子还是洗碗。学校确实会给奖学金,但只在开学后按月发放。他想在美国转转,便早几个月飞过来,打算先挣些路费。他用随身带来的美元换了辆旧车,独自在学校空旷的停车场练了一天车,傍晚开到加油站,把车加足了油,买了一张地图和一个热狗,便向城市出发了。
胡熊进城后结识了晓野兔子,经她指点在一家上海餐馆找到工作,发现自己不适合端盘子。晓野兔子去参观过,也觉得他不是那块料。他们的感觉很快被证实了--第三天晚上,也就是试工最后一晚,老板娘把胡熊叫到一边说,小吴啊,这是他们几个waiter waitress给你凑的钱。本来试工是没有tip的,但大家都看得出侬蛮努力的,所以这是从大家自己的salary里给你凑的--十块,二十,三十--三十块!如果侬想继续锻炼的话,大家都还是welcome的!胡熊反应慢,但还是听出了这话的意思。他没有沮丧。他不紧不慢收起老板娘拍在收款台上的三张钞票。他甚至没有纠正老板娘,他姓胡不姓吴。走出餐馆大门,他在夏夜的暖风中感觉到冉冉升起的自由。无论未来如何,今夜还是会在晓野兔子的客厅里入睡。
我挣着钱了,请您吃饭。胡熊在客厅里对晓野兔子说。
您挣了多少?
十块,二十,三十--三十块!胡熊把钞票一张张拍到地铺的床单上。
不错啊,我以为老板娘一分钱都不打算给呢。不过这钱不够吃饭,您改天请我吃冰淇淋吧。
胡熊认为晓野兔子是个好姑娘,所以决定用三十块钱请她吃饭,哪怕自己第二天就要搬走。但晓野兔子说她会帮他找工作。您也要交房租啊!晓野兔子有自己的小算盘。公寓房租五百块,她住卧室交三百。胡熊住客厅交两百。她说她占了有利地形--也就是说卫生间--所以多交一百。但是胡熊可以使用卫生间。在胡熊眼里,晓野兔子就是这样一个大方的人。胡熊开始在古都工作时,她建议他最好多用古都的卫生间,少用她的,但混熟之后又说无所谓了--反正两个卫生间都由胡熊负责打扫。晓野兔子就是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那天晚上,胡熊洗完澡,出门到对面加油站买回一打啤酒,庆祝自己挣到了钱然后又获得自由然后又正式迁入新居。晓野兔子说您不适合打招待,只好去打厨房了。胡熊说我不适合打招待不是因为我笨,而是因为我不喜欢打招待。我从小就在自己家里打厨房,后来又学工科,动手能力强,擅长做实验和操纵机器。晓野兔子说厨房挣的钱要少很多。胡熊说,现在我的房租省了一半,所以挣的钱少一半也很合理。她说对呀,然后以后咱们可以同车上班,油钱也省了一半。那晚上胡熊喝着酒憧憬未来,又多听了几个"咱们",有些晕,所以算术又退步了。他不知道晓野兔子是不是也有点醉了,还是在开他的玩笑。这点他一直没想通。他只是隐约觉得她有点自私。但他并不讨厌这种自私,因为那和钱毫无关系。
第二天,胡熊被晓野兔子带到古都,把昨晚排练的理由对安迪说了一遍,安迪一乐,就让他打厨房了。古都不要男招待,但洗碗工胡安最近提出辞职,厨房正好缺人。既然是晓野兔子介绍的,招进来自然皆大欢喜。一切就这么顺理成章。安迪从储藏室角落里翻出一件围裙扔给胡熊,让他不要穿白衬衣黑裤子黑皮鞋了。以后穿旧衣服来上工就可以啦。他把胡熊带到厨房交给了堂哥。你是叫小胡? 是的,小胡。然后他把堂哥拉到旁边叽哩咕噜说了一通闽南话,其间对胡熊指指点点。然后胡熊便在厨房上班了。
那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坐您的车了?当晚下班后晓野兔子说。
呃?哦,没问题。您喜欢坐我的车,我很荣幸。
您车上可以听音乐啊!我可以提供唱片。
上班头几天里,胡熊每次在古都洗碗池边的酱油桶上坐着休息,都会检讨自己为何不适合打招待。上海餐馆的回忆在厨房的烘烤中迅速蒸发,但还留着些印迹。比如,胡熊一直记得老板借给他的那副皮马甲,每道缝线上都嵌满油腻,可以拿去烧一锅好汤。他穿着崭新的白衬衣,好像器宇轩昂的指挥,套上这马甲,立刻变成没落大户的老管家。那家店由老板娘坐镇收款台,老板跟招待们一起跑堂,偷懒比登天还难。
干起活来,胡熊觉得自己更像喜剧演员。其他男招待在桌子和厨房间往来穿梭时,他在过道中央彷徨着东张西望--老板娘不止一次要他眼睛勤快。远处有客人向胡熊微笑,他也向他们微笑,直到看见他们招手,才如梦方醒急忙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