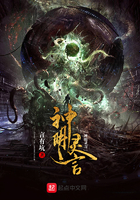日本这民族,总是让人感觉奇怪:文雅却又暴躁;赏花落泪却又杀人不眨眼;随处小便可以谅解,随地吐痰必须禁止;甚至,中国人还可以追溯到当年的杀人、放火、强奸,却又看不得鸭子受伤。这是一个价值取向上最“二律背反”的民族。究其原因,就在于看重了什么,怎么“看”,同样一个事物,这样看,那样看,是不一样的。中国也有一句话说,“此一时彼一时”。当年为了日本崛起,举国共力奋斗,那么侵略杀人只要有利于国家,就被“看”成是英雄行为;现在向文明“看”齐了,当然不能残杀鸭子。但是要说文明,应该什么都不能残杀的,但为什么还可以吃其他动物呢?而且日本人还是生吃。即使是再文明的人,不也得吃食吗?即使只吃素食,植物就不是生灵吗?这样,就没法活了,“水至清则无鱼”,人类就不存在了。人类不存在,一切也就无以附丽了,包括人类文化。
其实,所谓人类文化,就是一个“看”字,把自己看重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比如把某些动物“看”成了“保护动物”,就不去食杀之,其他的则可以食杀;而同样是控制,饲养宠物就被看作是“爱心”。这是披着文化袍子演出的喜剧。假如不作这样的区分,同样是食肉,吃鸡肉、鸭肉跟吃人肉有什么区别?同样是肉体,进入别的女性身体,跟进入自己母亲、姐妹、女儿的身体有什么区别?这是我小说《我爱我妈》中主人公的观点,当然不是我的观点。但备受谩骂,是因为把小说中人物的观点当作作者的观点,这样的人,是不配读小说的。小说家所以写作,是因为他困惑。也许最初还觉得他可以阐释世界,比如列夫·托尔斯泰,但后来发现做不到。从困惑始,至困惑终,这就是写作。小说家不像哲学家,小说家无法圆满弄清世界,也恰因此,小说才比哲学著作更能保留世界的本相。
至于日本人为何不吃鸭子,我想,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吃鸭子。这等于没有回答,但也许是最恰当的回答。
曾经,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跟我商量,能否把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翻译成中文。其实《人间失格》已经有中文翻译版本了,他们觉得翻译得不地道,又觉得我的写作风格跟太宰治很像,所以找到了我。关于后一点,他们的考虑是对的,翻译某种意义上说是再写作,但并不是说你随便再写一个作品,而是要写出跟所要翻译的原作精神上契合的作品。这很难。所以当初,我看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觉得非鲁迅还真翻译不出那准确味道来。这是最高境界的准确,那种只知道在字词句上亦步亦趋的,甚至一手拿着字典翻译的,用叶廷芳先生的话说,简直是笑话,应当坚决杜绝。
至于前一点,恰是我不敢翻译的原因。翻译难,翻译好更难,翻译日文,简直难上加难。我说过,日语是很暧昧的,作为中国人,最初往往不能理解。并不是说不能听懂他们讲什么,而是不能准确领会那语言背后的意思。每个词都听懂了,整个句子也明白了,但是其实并没有明白他们的意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在日本签证。战战兢兢准备了签证材料,包括所在学校的出勤率证明,考试成绩,经济担保人材料,一大摞夹着,去了入国管理局。那里有好多人,蝗虫一样,大多是中国人。不料百密一疏,仍然出了皮肉。那个签证官在我的护照上敲下一章,丢了回来。在我之前,就有几次中国护照被这样丢出来的,丢垃圾一样,中国那褐色护照,跟其他国家的不同,一看就看得出来。单那色彩,就很泥土,好像特地要告诉人们:我们是黄种人,我们是土人。那签证官还嘟囔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再问,听明白了,对方是说你能否弄清楚某些东西。既然是“能否”,我能,就连忙点头说可以,要开始说明。对方却不听我的,仍然说了那一句,用的仍然是委婉的商量语气。我仍然试图说明,对方火了,又瞧了瞧我,大概明白了,我是中国人,并不能听明白,索性明确吐出一句:“回去!”
原来对方是让我回去。可是对方却是用商量的语气。按我的理解,说这种意思时,一定不是那种语调的。这种情况也常发生在其他同胞身上,比如日本人叫你传递个东西,会说:“能否传一下?”既然是能否,那我就可以说否。结果,刚去日本的中国人往往会说:“不能。”对方马上脸灰了。原来虽然用的是商量语气,其实是叫你非做不可的。到后来没好果子吃了,才知道自己冒犯规则了。既然是非做不可,你日本人何必用这种语气?如此谦卑?
其实,谦卑未必就是卑下,它是一种素养,甚至是一种自傲。所以敬语并不只是为了尊敬别人,同时也是塑造自己。我多次听日本人对我说,日本是世界上最讲究礼貌的民族,其他民族的语言都没有这么复杂的敬体。可见他们多么自豪。晚辈对长辈怎么说话,长辈对晚辈怎么说话,女人对男人怎么说话,男人对女人怎么说话,下级对上级怎么说话,上级对下级又怎么说话,都是要讲究的。不仅说话,还有鞠躬,不同身份的人之间,谁得向谁鞠躬,腰要弯到多少度,都有具体规定。刚到日本的外国人,对日本的敬语甚是头疼,往往只能简单表达意思算了。日本人往往也不计较,知道外国人掌握不了这些的,原谅地笑笑。能原谅他人的人,一定是身居高处的人,又是高下立现了。所以他们那么认真地坚持着暧昧又刻板的语言。
说日语暧昧,只是说对了一个面,另一面恰是,它又很讲究准确。使用敬语是一种准确,在动词的表达上,又是一种准确。比如在表现时间上,汉语要表明某个动作发生的时间,是在动词前后加上时间副词,比如那个烟草局长日记里,就很“汉语”地使用了“已搞”、“正搞”、“待搞”。过去时是“已搞”,进行时是“正搞”,将来时是“待搞”,作为动词的“搞”一直没有改变,跟时态脱钩,无论时态怎么变,这个“搞”是搞定了的。具体什么时间点“搞”,“搞”的本身是不管的。中国人的意识里,只有宏观的时间。
日语则不一样,动词词尾都是する,当一个动作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时,动词词尾的する就会有相应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自动的,只要使用某个动词,这个动词的词尾就要有相应的标识时态的变化。这对我这个中国人是挺难适应的。当一种语言的时态能够决定其动词变化时,那么,使用这语言的人对时间的概念是极其强调的,表现在其性格上,那就是守时。我在日本第二天,就不守时了。严格说,是失约,被狠狠地怪罪了。虽然对方是中国人,但是已经是在日本很久的中国人了,中文跟我相比,差远了。日语却讲得很日本,于是也习惯了日本人的守时。我这么说,又有褒扬日本人的嫌疑了,有人肯定又要不爽了,“汉奸”的帽子“将盖”到头上了。
忽然想到,以民族血统论人,其实是很荒谬的,甚至“国民性”的说法也如此。台湾人和香港人就是中国人,他们说的也是中国话,处世风格却跟大陆的不一样。这么看来,语言也未必就是思维的方式,拿文化说事,也不靠谱了。喜欢“和谐”的,回答多是:“是啊!”“是这样啊!”虽然心里并不认可你说的。但是我知道我心里应该很清楚:老师不批评我,我的缺点仍然在。从我自身角度,给我吃苦药的人,其实我无论如何应该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