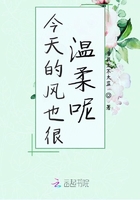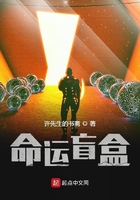孔笙据说是孔家圣人的后裔,孔笙自己并不以为然,但是父亲深以为然,从小训以孔孟之道,不听是不行的,那么只好耐着一颗心听听。
某日有挚友书信自远方来,挚友很客气地请他来当幕僚,孔笙除莫名其秒的家世外并无所长,挚友之醉翁之意仿佛也就不言而自昭明了。然而实在受够了所谓子曰孟子曰,出去散散心也是好的,父亲以为孔笙已经到治国的地步了,出门的时候开怀大笑引以为豪,当然,君子“不重则不威”,所以所谓的笑是隐匿在心里勿使人知道。孔笙欢天喜地不胜愉快喜逐颜开地离开家。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亲,孩儿此去倘不得以立功立德立言不足以归家。”
“嗯,君子之道。可。“
孔笙三步一回头地再三辞别父亲以表示自己的忠孝之道。
父亲很慈祥地笑笑,但只一下,印象里是孔笙这辈子见的最和蔼的笑了。
孔笙等到消失在父亲的视线中,便觉得浑身轻便了,一有大展宏图的抱负的期望。
太阳都是懒的惰的弓着背的,不然何至于漫无目的随意地散放,倘使精确一点或许也不至于天地的混乱了,孔笙想。
孔笙半蹦半跳地到了远方的客栈,家书半颠半递地先他一步到。
太阳的光芒全死了,不再是金色的,而是布满黑色的光丝,聚合起来的样子竟成了黑色,父亲的离世当然意味着孔家的分崩离析,不必回去了,孔笙一清二楚,回去只剩下苟且的烂摊子。
在客栈的几百里,孔笙最后一点银钱及干粮所能及的地方,不期而遇的寺庙使之不至于饿莩于野,于是顺理成章地凭借佛家胜造七级浮屠的理论和当仁不让的孔家后人的身份成为佛门一抄经人,蝇营狗苟地哀悼万分,以期回忆离家前温柔绚烂如金光的某人的藏不住的暗自赞许的微笑。于是此微笑毫无意外地继续巩固了其生平最宝贵的回忆的地位了。
再二十里,有一家空空如也偌大的房宅,孔笙的鲲鹏之志首先不能被困守在所谓浮屠之中,远离佛门,保持七情六欲都是紧要的事,可惜佛门油水不足,给与梦的燃料尚供不应求,不过总算拾得漏网之鱼,这间大屋的东家久居金玉里,忽觉得新鲜空气比金玉更有魅力,以傲视群氓的姿态入世了,可怜着苦苦大众不知富贵其中,这种愉快的自得不足以与外人道哉,且当与民同乐了,于是下乡去了。
房屋里还有一书生,怀着莫大的同情心听完孔笙的哭诉,此时便不能不展示人类高贵的爱心与善良了,“既然如此,莫不如在这当个先生吧。”
“唉,在下才疏学浅,难堪大任。”孔笙欠了欠身,以表示自己确实当不了老师的样子。
书生觉得他可怜之外又多一份可笑,不过是小小的私塾老师何来大任之说,不过还是很正经很温和地劝说,“先生不必谦虚,不妨先当我的先生,来日再有大任再去任职也不迟。”
孔笙心微微一动,以为并无不可,于是很谦卑地说:“哪敢,不过互相指教罢了。”
“好好好,先生先坐,学生自不敢指教老师,先备下酒食以庆良师之远来。”
孔笙嘴上说着不必多礼,身体却绷直了,以回敬这种讲究,表示自己确实堪当良师。
不多时,书生不仅酒食齐备,又击掌三声,缓缓进来一个女子,面容含春色,一举一动倒像是朵桃花般的娇羞,只是眼神大胆地投向书生,好像有损娇弱风气,孔笙面对着书生,将背后的女子看的真切。
“红袖,为先生舞一曲罢。”
红袖走到书生面前,收敛了炙热的眼光,于是缓缓起舞,翩然若仙,而且是桃花仙,称之为桃花妖或许也无不可。
孔笙明白不是为他舞的,随意地拜了摆手,“算了,算了,今日只饮酒,不必助兴了。”
“红袖,退下吧。”
酒饮至一半,一老者幽幽而来,书生立马起身,“父亲,您怎么来了?”
孔笙心里猛地一震,手上的杯还放置在唇边,这一震使他想起某人的微笑,但是他也笑了笑,几乎是把酒灌进嘴里,酒杯撞击在牙齿上,发出一点咚咚地清脆声响。
老者并不言语,只深深地看了看孔笙,而后扭过头来,大声怒斥道:“孽障,还不跪下?”
书生一惊,嘴里诺诺地说:“父亲...”
老者伸了伸拐杖,敲在书生腿弯出,“跪下!”
书生还愣自犹豫了一会儿,深深看了一眼孔笙,再稍稍回应了下父亲愤怒的眼光。
“跪下!先生就是先生,先生把你当朋友,你真拿自己当什么东西了?”
书生好像明白了什么,于是眼光倒变得坚定了,屹立着不言不语。
老者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脸上的老皮微微抖动,皮下的青筋略微鼓胀。
半晌无言。
老者终究不够书生年青,长叹了口气,转身念念叨叨地走了。
孔笙这才缓过神来,“令尊...”
“不必理他,我们继续就是。”书生冷淡地说了一句,随后缓缓坐下。
坐下那一刻又换上一副欢笑的脸,使孔笙很容易被感染了。
孔笙和书生第二日便开始读书了,书生学的很快,三两边即能熟读成颂。
不过就是每逢两日即与孔笙相约饮酒,并且唤上红袖,一开始孔笙还想初次见面一般让书生将红袖唤下,不过长久以往,孔笙就懒得多言语了,毕竟是寄人篱下,并且即使不为自己的舞姿也饶有趣味,舞蹈里终归是饱含爱意的,比没有感情不知好上多少。
太阳出来的时候,月亮要远远避开,当然有月食的时候,不过这长期以来并不被看作什么好事。春去秋来的很快,孔笙觉得太阳有些耀眼了,于是某天夜晚,孔笙对书生说:
“今日喝酒吧。”
“哦,先生今日怎主动提出喝酒了,况且昨日不是刚喝过吗?”
“太阳照到身上了,也要翻翻身吧?”
书生看着孔笙,笑了笑。
“坐吧。”
“先生有事请说。”
“把红袖给我吧。”
“先生不是一直不喜欢吗?”书生不动声色地说。
“人的喜欢是会变的,不是吗?”
“也未必吧。”书生又温和地笑了笑。
“这不是你一直想做的事吗?我今天帮你实现。”
书生说:“好啊,明日就成亲吧。”
“是啊,当然好啊,拜脱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孔笙好像不是对书生说一样。
书生还是笑,“祝先生幸福。”
“不必了,公子不必拐弯抹角了。”红袖从阴影里走出来,说。
“红袖,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啊。”书生很高兴地告诉红袖。
“公子难道不知道?”
“知道了如何?不知道如何?”
“这个人从一开始出现我才知道你早已经知道了。”
书生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差点掉了,是真正开心的笑,“那你知道的还是太晚了。”
红袖扭着头,仔细看了看书生,半晌,说:“好吧,今晚就成亲吧。”暗暗却把刀丢在黑暗了。
金属撞击着青石板,发出沉闷古拙的声音。
“奴婢多年以来,不过靠公子一口饭吃而已,何必等到明日?”
书生拊掌大笑,“春宵一刻值千金,祝安祝安。”立刻转身走了。
晚上洞房的声音是两个人刻意的结果,于是不比寻常,缠绵悱恻而惊天动地了。这么说或许有失公允,因为书生并没被惊动,反而香甜一梦。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起点,依旧是一日读书,一日饮酒,不过倒是孔笙常常将红袖唤在身边起舞了。书生比孔笙的欣赏力更好,倒是从未让红袖退下。
某日,孔笙病了。
书生急请了医生,无功而返。
书生于是出门,不几日,一个袅袅女子与之一同归来了。
书生引女子到病床前,说:“舍妹娇娜,名医,定可救先生。”
三两幅汤药下肚,确实药到病除了。
孔笙好了的第一件事,就是笑笑地又把书生叫来饮酒。
书生还不等孔笙开口,便说:“不可。”
孔笙又笑了笑,“为什么?”
“不可。”
阳光照在孔笙的背上,使他想起多年前离开的父亲的阳光。
书生说:“走吧,没事,我可以等。”
孔笙顿了顿,“多久?”
书生说:“我不是人。”
“我知道。”
“等很久。”
“我是人,不会想有人等那么久。”
“我不是人,不会将就。”
“那么,你等吧。”
于是就回房去收拾行李了,看着阴影里某个期盼的眼神,孔笙说:“你的毒,毒不到心,也救不了心。你早应该知道。”
又是很多年过去,孔笙返身在庙里帮衬着抄经,有时经文放在太阳底下,散发出的浅浅墨香常常令孔笙心醉,他已经不去想父亲的事了。住持说放下,孔笙就说,早就放下了。住持说,他没有,他要是真的放下,不会执着于抄佛经,
某日,一个女人走进佛门。
女人对孔笙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孔笙有点意外娇娜的到来,但是又好像意料之中,反过来说:“这话应该我对他说。”
娇娜说:“怎么都好,该有了结了。”
“怎么?”
“杀人是有天劫的。”
孔笙急匆匆想去探寻真相,也不是探寻,只是确认,一进门,看到精神很好的书生坐在竹椅上,书生看了他一眼,先他一步说话:
“当时他就是这么坐在椅子上的。”
孔笙多年的答案总算亲口被那人承认了,这时他想起住持说的放下。
“当时我说红袖早该知道的,你也早该知道。”
孔笙没说话。
孔笙张了张嘴,他本来应该上去和书生拼命的,但是他听见自己的声音:“要我怎么帮你?”
“你帮不了我,杀人者必将被杀之,我们也要遵循这个规则。我让她叫你来,是想见你一面而已。”
忽然雷声震震,“是时候了。”
当雷声迫近的时候,地上已经看到一具尸体了。
孔笙说:“慎终追远,民德可厚矣。”他想到也许爷爷去世的时候他的父亲也这么想吧,他真傻,父亲果然还是父亲,他身体里大概确实还流淌着圣人的血吧。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书生悲痛地明白了一个道理:有的人,也是不肯将就的。
阳光还是懒懒地撒,并没有什么黑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