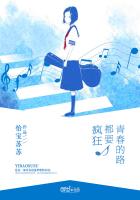“公子,您……没事儿吧?”许掌柜弓着腰,就和做错了事的孩童等候在一旁,呆呆望着这个眼看着长大的白衣青年。
一个马夫一个公子,地位云泥之别,当年受那个女人嘱咐把他捡回来之后,不论这个男孩多执拗,他也只能躲得老远看着,既不能走近亦不能远离。
长云公子呵了口白气,摇摇头,分明眼睛已经湿润了,“没事,许叔,你先忙去吧。”
许掌柜也愣了好久,这个称呼多少年没听过了?他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只得腆着一张含泪笑容的老脸道:“唉!公子,我先退下了!”
等这矮敦敦的中年掌柜下了楼,随即传来震耳欲聋的训斥声。
吕长云重新坐下,绑好狼尾。窗外雨下大了,哗啦啦和当街不要钱地泼水似的,汴梁每场秋时雨都是如此轰轰烈烈,不知不觉听了二十几年。他叫了一壶酒,温好之后送上来,一个人自斟自饮。
而此时青梅坊往西的竹龙坊中,一个过度依赖现代化天气预报而不会看天的年轻人飞也似地跑着,免不了被淋成落汤鸡。
张柯本想着出来逛逛,顺便尝尝沿街摆摊子的美食。这条街上都是买吃食的店铺,煎炒煮炸样样都有,他还听说附近有家买冷饮的地方,那家的酸梅汤、桂圆莲子粥、茯苓膏什么的都是远近闻名,古井的水冰镇的吃食,纯天然无添加,闷热的晚上来一碗,又酸又甜下肚还带着丝丝凉气,啧啧,那叫一个痛快。
张柯从一些小贩那里打听完,立马就馋了起来。
虽然叫卖甜汤的这白天可能不营业,但其他诸如炒货、糖葫芦串、北方独有的汤饼、西域传来的烤肉烤馕,能吃的食物琳琅满目,他算是来对了。
可没想到天公不作美,一泼倾盆大雨俄然将至,劈头盖脸打下来,把他的计划又打乱了,匆匆逛过几家炒货摊子,还没咬完一张热乎的烤饼,只能没头苍蝇一样找躲雨的地方。
张柯抱着头乱窜,却连连躲开了那些支着棚子的茶摊,只是一路沿街小跑,最后钻进了一处乌烟瘴气的所在。
莽撞冲进来的青年两边看了看,抓着水淋淋的头发,一拧就哗啦啦地淌水,他眼角瞥见了一个火盆,旁边零散蹲着一个同样淋湿的人,他也不管这是什么地方,赶快蹲到了火盆边,占据一方位置烤起了火。
等身前差不多烤干了,张柯才转过身,正打算将背后和尾巴一齐烤烤火,却发现至少有十来双不怀好意的眼睛正盯着自己。
那哥几个都拎着狼牙棒,像是土匪窝子里钻出来的绿林,浑身一股横劲儿,看向这边的眼神就像是发现猎物的狼。
张柯这才咽了咽口水,慢慢挪到门边,抬头看了一眼,两个言简意赅的黄漆小篆字不算复杂:赌坊。
他娘的他娘的他娘的!怎么随便乱走都能走进这种地方!我只是个想过平静生活的穷酸作者,为什么老是给我带歪了?
不等他心里骂完,那个打头拎着狼牙棒,一脸匪样的男人啐了一口,粗横道:“怎么介,小相公,看你路都走不直往这里面撞?知道那头上三尺挂的是哪三个字不?”
旁边一个矮瘦家伙悄悄提醒了一句,“大哥,那是两个字!”
这男人一瞪眼,一脚将那个瘦胳膊瘦腿的小子踹开骂道:“你个催人死的,别给老子面前显摆你读过书!”
说罢他又提着狼牙棒,挥舞出呼呼风声,陡然直指眼前这个文弱书生的眉心,“小相公,别走神,说,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张柯眼神淡薄,他听说过那些赌场镇场子的,都是混不下去的地痞青皮,他一没偷二没抢,不可能真的当街动手,于是就没想计较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如实答道:“哦,这是赌坊。”
听到这么一本正经的回答,那群匪气上头的青皮爆发出一阵刺耳笑声,张柯觉得自己可能捅了狒狒窝,吵得要死,只能堵住耳朵。
青皮看他捂住耳朵,想来就是个怂包书生,便冷哼一声,那支木头上钉铁钩子的狼牙棒架在张柯脖子上,傲慢道:“那你说说看,既然来了赌场,是不是好歹给大爷我留下点什么?”
张柯二话没说,掏出身上几枚银铢,双手托了上去。
壮汉青皮皱了皱眉,吼道:“笨蛋!当我们是劫道的?今天你是来也好去也好,都得给老子上桌赌一局!”
张柯被这足以穿透耳膜的狮吼炸得有些懵,随即想明白了,好歹这汴梁是天下首善之地,这人确实不能当街抢劫,但是,要是他“自愿”地输在了赌坊里,那就没有什么罪责。
他当下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撒腿就跑,第二,利用昨晚领悟的驭物力量,给这个眼高于顶的青皮一点教训;第三,陪他玩几局。
对一个深知赌场套路的现代人,第三条方法未免不明智。但鉴于眼前他走不了,而且他的本意也只是获得异世界的别样体验而不是打怪升级,所以第一、第二条张柯没有考虑,而是干干脆脆地认怂,就假装自己是个菜鸟新手,被迫入了赌局。
毕竟,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多面怪才,一个兼修贵族气质和贵族生活的伪装者,他研究过不少赌局,计算功底极佳。别忘了,这厮还有驭物的作弊能力,操纵几个骰子不在话下。
一群即是赌场请来镇场子、也同样下场下注的青皮将这名误闯赌坊的书生围起来,就等着这个文弱小相公输个精光,他们好发泄一下暴力,更有甚者,那都是男风馆的常客,癖好不一般,就盼着这细皮嫩肉的家伙输光后卖屁股呢。
打头的那位青皮开路,领着他去了内厅,这间屋子很大,摆着至少十张桌子,每张桌上都围满了人,摇骰子声、喊叫声、斗殴撕扯声不绝于耳。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小!小!小!”
“大!大!大!”
张柯双手后背,悠哉游哉地走着,每经过一张桌子,便踮着脚往里面看几眼,随即摇了摇头。
都是很原始的赌博方式,摇骰子比大小,真想不明白这些人为嘛热衷这种游戏,有这时间练练口才和摇,街边摆个算命摊子来钱都稳定些。
最后那青皮停在了一张旁观者稀疏的桌边,这张桌子边不过站在寥寥几人,都像是看热闹的看客,从微弱的灯光中可见几人怀抱着砍刀。桌子呈长方形,两边主位上坐着上下家,中间一个倒扣的茶碗做骰盅。
张柯站在这边,正好看得见对面上家的位置上坐着一个身形消瘦的男子,眼神畏首畏尾,衣服破破烂烂,但看得出料子不错,此人应该也是被骗入了赌局,又被这些个看场子的地痞威胁着下注,估计不脱一层皮是不会放过他的。
那壮汉走上跟前,提溜着狼牙棒一挥,原本坐庄的那个消瘦男人立刻扑到地上,一个劲地磕头感谢,抬眼时便对张柯投来了怜悯目光。
“滚吧,下次有钱了,别让爷爷瞧见了,保准请你来金银桌上滚一遭!”那壮汉青皮扯着破锣嗓子笑道。
已然是输个底掉的男人低着脑袋,一副两边崴的模样,还得强颜欢笑哈腰点头,等这个青皮允诺了,他拔腿就往外走,张柯目送着此人离开,经管身边时,他将手中攥着的一物塞进了张柯的袖子。
等他走后,确认没人瞧见,张柯摊开手心一看,是一枚满是汗渍的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