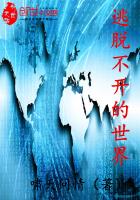同为“北大人”
——记胡适与李璜的情谊
陈正茂
1917年夏,胡适应蔡元培邀,博士学位还没真正到手,即风尘仆仆从美国回国赶赴北大就任,尔后历院长、校长等职,成了终身以北大为傲的“北大人”。而李璜呢?这位青年党的领袖,国家主义的大将,于1924年偕曾琦回国后,先在武昌大学任教,1925年亦应聘至北大,讲授西洋史,与胡适成了同事,同为“北大人”。胡适,一生交游满天下,上至王公巨室,下到贩夫走卒,到处都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喊得满天价响,甚至成了一句揶揄的话。
胡适好交友,友朋也确实多,不过基本上,仍以教育、学术界为主,大陆学者沈卫威谓其为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1]当然,胡适也有不少政界的朋友,包括在朝在野党派都有。胡适和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层,都有若干公私情谊与恩怨。胡适终生道义支持蒋,但对蒋之威权独裁,亦常严辞批评之;而蒋对胡适也始终尊而不亲,让胡适一人拥有言论自由,装点门面弄弄样子而已。与汪之关系,虽曾一度在对日立场上,双方想法接近,惜汪最终下海,胡适一向秉持大是大非的原则,当然与其分道扬镳。而对宋子文这位国舅,胡适自然是不敢恭维,尤其胡在驻美大使期间,更是受了宋不少气。
至于胡适与在野党派领袖的关系,旅美史学家李又宁博士,于近二十年来,一直对推广胡适研究与搜集相关史料相当用心。十余年前,李氏在纽约主编《胡适研究会丛书》,且出版一系列有关胡适与其亲族朋友的专书。1988年2月,李氏在其主编的《胡适与民主人士》一书中,收录了杨天石等人所写的胡适与柳亚子、郭沫若、陶行知、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王造时等七人的论文,其中包括民社党的党魁张君劢,惜青年党的领袖与胡适的关系,仍付之阙如。[2]
同为“北大人”
众人皆知,青年党的领袖为曾琦、左舜生与李璜,即所谓的“曾、左、李”三巨头。三人中以李璜与胡适的交谊最深,关系也最厚。这可能与胡适终身标志的“北大人”有关,一日为“北大人”,终身即为北大的一分子,胡适常以此自豪。而李璜曾于1925和1926年间,在北大史学系任教,讲授西洋史,故胡适亦常呼其为“北大人”,有此渊源,双方关系自然容易建立起来。但其实李璜至北大任教时,胡适已暂离北大赴欧旅游,故彼此并未真正谋面。此事,李璜在其《学钝室回忆录》即载:“我在北大教书的一年(民十四),并未晤见适之,因他于民十四的十月就去了上海,民十五便由上海赴欧洲旅行去了。我是于民十七在上海始认识适之,从此交往不绝。”[3]
彼时,胡适与李璜虽然缘悭一面,但胡适对李璜的才学已相当欣赏,并无任何门户之见,诚如李璜所言:“适之为人,性格开朗,虽自己的思路是本于美国的实验主义,然而并不排斥在欧洲大陆德法两国留学而略有成就的学人,一视同仁,十分合作。”[4]举例而言,1926年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中国边省设立四个讲座,李璜积极向中基会总干事任鸿隽(叔永)要求担任成都大学的社会学和教育学讲座。但据李璜说:“叔永是一个谨慎人,对我这个不大务正业而爱惹是非的教授不大放心,迟疑不决,去电适之询问可否;而适之立刻回电,称‘人选最妥’。于是我才得着讲座聘书,回川任教,免了次年张大元帅的大刀威胁。”[5]由此可见,胡适对其是如何的信任,尤其是李璜国家主义派的政党背景,胡适毫不芥蒂,一切以才学专业为考虑,更令李璜直到晚年仍感佩于心。
当然,李璜与胡适真正晤面,并进而有所往来,还是始于1928年,当时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等人正在上海办《新月》杂志。[6]而李璜则于1927年,在上海主持青年党中央党部,其后又与张君劢合办《新路》杂志,抨击共产党的“流寇主义”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7]基本上,《新路》理念与《新月》相近,此即为双方接近,提供了精神上的相契基础。
而他们两人真正认识的时间,胡适日记并未刊载,李璜则回忆为该年夏天。李璜说:“民国十七年夏末于上海张君劢处,认识其弟禹九,后又因禹九请客,得晤见胡适之、潘光旦、徐志摩、刘英士、梁实秋、邵洵美诸人。适之其时在吴淞中国公学当校长;我与他虽是北大的老同事,但并未会过面,但他看过我的谈历史学方法的文章,引为同调,相见甚欢。其时适之与禹九、储安平诸人正在上海办《新月》杂志,且经营一间新月书店,每周‘新月派’中人必有一次聚会,适之也请我去参加这一聚会,计有三四次。适之要我为《新月》杂志写文。我已知当适之归国过日本时曾发表《论孙文哲学》,已使国民党当权者对他感到不满;我便推辞,我有‘异党该死’的罪名,文章发表出来,于《新月》的往外埠发行不利。适之认为介绍法国的历史学方法的文字无妨,再三约定,我只得写了一篇长文,介绍法国涂尔干派的对古史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并及于法国汉学家用此方法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贡献。文分三期在《新月》上发表出来。我其初只署的一个‘幼春’,而适之认为《新月》货真价实,从来无假,乃由他添上木旁用我真名‘幼椿’二字发表,尚未发生问题。”[8]
李璜又回忆说:“他与我虽是民十四年在北大的同事,彼时大家忙于讲授,往还不多,并不觉得他在那时候,便留意到我在北大史学系学生晚会所演讲的Durkheimian School的研究古史的社会学方法。直至民十八,他在上海办《新月》杂志时,他请我参加并作文;我表示我的政治色彩太浓厚,于他的《新月》不利。他说:‘我不是要你谈政治,我是要你将Durkheimian的社会学方法论用的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并且要求你写得不枯燥,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因此,我曾用‘古中国的舞蹈及其故事’的题目,在新月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后来在上海中华书局出单行本,现在已绝版了。”[9]
由上述两段引文看来,胡适与李璜似乎是一见如故,且同为北大人,胡适早已读过李璜的文章,尤其是李璜以法国社会学理论来阐述古史的做法,想来是深得胡适肯定与认同的。唯查《新月》杂志目录,与李璜的回忆有些许出入,《新月》上,李璜只发表过两篇文章,即《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署名幼春),载《新月》第2卷第8号(1929年10月10日),与《法国支那学小史》(署名幼椿译),载《新月》第2卷第9号(1929年11月10日)。有意思的是《新月》杂志在李璜投稿后,开始陆续有其他青年党人的文章登载其上,如茅以思(左干忱)《打靶的人》,载《新月》第2卷第11号(1930年1月10日),陈翊林(陈启天)《社会标准与控制》,载《新月》第3卷第1号(1930年3月10日),及庐隐、刘大杰等青年党人译作,是否与李璜有关,颇值玩味。[10]
另方面,检阅胡适日记,开始有确切日期和李璜交往,是在1929年6月16日。当天胡适日记写着:“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任叔永昨天从北京来,我邀他加入。饭后三点,我同梁、罗两君去寻李幼椿先生谈,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幼椿是国家主义派的一个首领,曾在北大教过历史。这一天谈话最要之点有几点:(一)我说,你们的标语是‘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你们主张多党政治,但多党政治的根据有二:(1)少数党已成一种实力,使政府党不能不承认。凡政府党皆不愿承认反对党,其承认都是因为反对党已成势力,不得已而承认的。(2)多党政治是多党共存,虽相反对,而不相仇视。若甲党以‘打倒乙党’为标语,则不能期望乙党之承认其共存。(二)国家主义者似总不免带点为中国固有文化辩护的气味,此是我最不赞成的。幼椿先生态度很好,我们谈话很公开,很爽快。他劝我多作根本问题的文章,他嫌我太胆小。其实我只是害羞,只是懒散。”[11]这天日记透露出一点有趣现象,即从长谈的情形看来,胡适与李璜的交情,应该已到相当不错的地步,否则李璜不至于唐突到嫌胡适胆小,而胡适也不客气地直接批评青年党的政党理念,与胡个人不赞成国家主义的立场。晤谈后半个月,即7月1日,胡适又写信给李璜与常燕生二人,针对该党若干杂志,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不负责任的报道,提出严厉批判。信中说道:“……国家主义者所出报章,《醒狮》、《长风》都是很有身份的。但其余的小杂志,如《探海灯》,如《黑旋风》……等,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污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如《探海灯》诗中说蔡孑民‘多金’,便是轻信无稽之言;如说‘蒋蔡联宗’便是捏造故实了。我以为,这种懒散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纵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12]
所谓爱深责切,《醒狮》创刊于1924年10月10日,为青年党的机关报,水平素质均高;《长风》月刊于1929年创于上海,左舜生、常燕生常撰文其上,内容水平亦高。《探海灯》为三日刊,是青年党香港总支部所办,畅行于港、粤一带,常刊登一些未经求证的小道消息,胡适能见此刊物,足见其阅读之广博。[13]至于《黑旋风》刊物,以笔者研究青年党多年,尚不知青年党有此刊物,因此有可能是胡适的误认。胡适于此信函中,不留情面地给予批判,双方设若交情不够深,胡适也不用如此苦口婆心地规劝青年党,惜李璜回忆录,并未说到接此信后,如何感受与处理。
1930年一年,胡适与李璜仍往还不断,胡适日记中有多处提到李璜,如1930年8月27日言:“幼椿、慰慈、梦旦来谈。”[14]四天后,即8月31日又记载:“在觉林吃饭,幼春谈及谭延闿给人写条幅,曾写这首诗:‘炼汞烧丹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学会吹箫便得仙?’谭三先生的感慨不少!此诗不知是谁作的,颇有风趣。”[15]10月19日:胡适与张子高、丁在君、赵元任、傅孟真、陈寅恪、姜立夫、胡经甫、胡步曾、任叔永等人,参加由欧美同学会所邀请的编译委员会同人聚餐。此次餐会是要决定国内高等教育用书、译书的问题。各个学科所建议之用书,都是一时之选,且水平极高,最后还要经由胡适、傅孟真、陈寅恪等专业史家审核通过才可。胡适负责历史学门,在决定选用西洋史中的法国史部分,胡适拟用李璜所推荐的Albert Malet: Nouvelle Historie de France(1924)一书为选译底本,当时陈寅恪等大师原本有意见,但胡适仍拟从李璜所开法国史书目,可见李璜在法国史的专业知识,是深受胡适所肯定的。[16]
胡适不仅同意李璜所开法国史书目,并且委请李璜翻译,以为一般大学所用。此事李璜曾有如实之回忆,“适之先生在民十九接受了中华文化基金会新设编译委员会之聘,去北平之后,还寄给我一大册法国史的法文名著,请我翻译,我只译了两章,‘九一八’事变一来,并加以淞沪抗日,我便卷入抗日义勇军中,原书与译稿都弄掉了,真正对不住他的好意!”[17]
雪中送炭
胡适与李璜交谊,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九一八”变生,当局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几乎没有抵抗地让白山黑水的东北,瞬间沦入日本的铁蹄之下。青年党义愤填膺,秉持着“野战抗日”的宗旨,由李璜所领导的青年党游击队与东北义勇军,不时地游击偷袭日军。其后,政府与日本达成“塘沽协议”,转而开始取缔抗日义军,李璜即在此情况下,遭到通缉,四处躲藏,最后在即将被逮捕前夕,幸得胡适帮助掩护,才有惊无险地安然脱困。
此事经纬,李璜曾有如下追忆:1933年,“塘沽协议”签订后,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开始捉拿抗日义勇军首领,时在北平的李璜亦为当局追缉的目标之一。6月4日,李璜在王慎庐处,知警察已找上门,只有赶快想办法脱身。但当时他身上只有一两元钱,根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到之前胡适有约姐夫张真如(四川人,美国密歇根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双料博士,娶李璜胞姊李琦——留学法国习西画)和李琦去他家吃饭,也顺便约了自己之事,乃急中生智,迅奔米粮库胡同胡适家躲避,因为胡适家里绝对不会被军警怀疑有抗日行动的。最后在胡适金钱赞助与细心策划下,搭胡适的包车,贿赂加煤工人,躲藏于车头煤卡之内李璜安然脱险至天津。李璜说,“在危难中,像适之这种热心帮忙,而且帮得很有办法的朋友,真是难得之至。”[18]
基本上,胡适与李璜密切往来时间,大概只有在1928年至1933年这五年间,以后双方各奔东西,来往就不那么频繁,晤面也大多在重要集会的正式场合。如1937年8月14日,政府决定在国防最高会议中设国防参议会,聘请各党派及社会名流为国防参议员,最初为十二名,继增至二十五名。第一次国防参议会开会,由汪精卫主持,到者有张君劢、胡适、张伯苓、梁漱溟、黄炎培、曾琦、李璜、周佛海、周恩来等。[19]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开幕,出席者五十国。中国首席代表宋子文,胡适与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胡霖等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赴美与会。[20]
胡适与李璜,久别重逢,自然畅叙一番,期间,胡适向李璜表示,其心脏病亟待休息,而《水经注》的研究工作也放不下,要不是因为诸位各党各派,他才来捧场,否则他绝不会从东部远道来跑这一趟的。言下对宋子文的皇亲国戚派头,似尚有余痛在心。[21]
大会结束后,李璜于9月24日至纽约,与邱大年(椿)、李圣策、李国钦、李爙乃、胡适游。李璜头痛失眠,还是胡适介绍他的医生姜森(Dr.Jeanson)为其检查医治。胡适更劝李璜暂时不要归国,把政治放下,还是回到书本中来,有如在法国时专以社会学方法治中国史学,比之政治较有所成就。李璜晚年写道,回思适之在纽约告彼之言,真良友也。[22]1957年,李璜在纽约治病,检查身体,又承胡适为其介绍医生,并每周亲来问讯一次。李璜说,胡适之热情异常,可感之至![23]
纽约一别,未几,胡适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发生雷震的“自由中国事件”与中国民主党的胎死腹中,使得晚年的胡适更感凄怆孤寂。而李璜所领导的青年党,来台后更是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纷扰不休,亦使无力整顿的李璜,只能困居香江一隅,教书为生,苦闷至极。时代的巨变,造成同为“北大人”胡适与李璜难得心境的一致,这或许是命运的捉弄与时代的无奈。
李璜对胡适的评价
胡适是位天生的热心者,对裨益世界、国家、社会、朋友的事务,无不热心。他在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函内,说梁任公是“热病者”,而他自己也差不多:“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24]胡适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脑筋是储满理性的,但心底下永远翻滚着一腔热情。也因为胡适热心地对待李璜,让李璜终生感念在心。当然,李璜的高度推崇胡适及其思想,不是因为胡适曾有恩于他,而是出自双方对民主自由理念的契合。李璜赞许胡适,说他是自“五四”以来,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最能将科学的怀疑思想与求证精神普及于中国知识界的一位学者。[25]
李璜并评价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与胡适,他说,陈独秀所主办之《新青年》杂志,确实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但在思想改造方面,如脱出家庭制度及其伦理思想的阐扬,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文字,是比陈独秀更为有力。李璜认为,如胡适在《新青年》4卷6号,所主编的《易卜生专号》上,其《易卜生主义》一文,及其译载的《娜拉》与《国民公敌》等篇,都给予当时及后来的青年人抛弃家庭以及妇女解放的影响至大。
又胡适在1919年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无疑是使青年知识界不但不再去随便信从传统的人物及其学说,而且可使有志于学者去求所以自立之道。李璜认为这些都非陈独秀只是文笔勃茂,固多所主张,而大半冲动与笼统的篇章之所能及。
所以,归结到底,李璜认为在自由主义与科学主义(即民主与科学──当时亦称“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理论阐发方面,于《新青年》杂志作者群中,胡适要算是主帅,而陈独秀与其他作者只能算是偏将。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科学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的思想主流;其影响所及,李璜以为,在政治上乃直接有功于国民革命之顺利发展,在文化上又间接地有功于中国今日能与世界交换知识的科学成绩。[26]因此,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实功不可没。
除高度推崇胡适对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巨大影响外,李璜亦慧眼独具,肯定胡适在史学上的成绩,这点是过去较少人提及的。李璜总结他对当时国内史学流派的观察,他说:“在民十三,北大的钱玄同、顾颉刚等一味疑古的一派哄动形势渐归平静,而南北各有名学府大都在注重获取西方治史的科学方法,以求如何去整理国故,真正的去从事于‘温故而知新’中有所创见。在这点上,可以说,梁任公先生于民十一至十二,两年之中,先后在天津南开、北京的清华与南京东大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影响特大;故其讲稿印行后,销路甚广,流传至速。”
他又说道:“不过任公的文笔虽锋锐无比,对于中国历史也涉猎至广,且以其颖悟过人,创见不少;但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其谨严处,又不及胡适之先生之能寻根究底,一枝一节的都非内证外证的求其水落石出不可。适之在民十二三之间,其整理国故的提倡已入了轨道,大可以补任公之不足。如他的《淮南鸿烈集解序》上,首先提出整理国故的三个途径,是足以启示学生从事中国经史的新研究着手津梁的。又如他的《古史讨论读后感》,将读经、史、子等书,把所谓‘度之以情,断之以理,决之以证’这三点都分析得很清楚,而结论到历史演进的必然步骤,要求治古史的人去先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这一类有建设性的指导,比之民十之前,对于中国古史徒事破坏,却已有进步。”[27]
李璜上述的回忆,重点在说明,胡适在史学研究方法的见解上,其眼光是超越梁任公的,胡适一再强调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这当中自然也包含史学在内),在李璜看来,其实也是为未来中国的史学研究,指示出一条明路。同为“北大人”,胡适终生信奉自由主义,李璜毕生笃信国家主义,在政治信仰上,看似南辕北辙,但对民主自由的认同,却是殊途同归,也因对民主自由理念的一致,维系这两位同为“北大人”一生不变的情谊。
以英文写作的温源宁教授
蔡登山
胡适在1931年2月7日的日记上说:“与温源宁同吃饭,谈北大英文系的事。他近年最时髦,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名声。他今晚极力撇清,但我仍劝他不可自己毁了自己。”后来胡适在写《丁文江的传记》一书时,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我到北平,知道孟邻已回杭州去了,并不打算北来。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时的北平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来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候,已被贬作‘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大齐)先生。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一个大学教授最高俸给还是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地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般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派定时间表,有计划地在各校轮流讲课!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
由胡适的描述,我们可知温源宁当时是名气很大的英文教授,同时在几个大学兼课。温源宁(1899-1984),广东陆丰人。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25年以后,历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英文组主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系讲师等职。徐志摩1931年3月4日给陆小曼的信,谈到他除在北大教课外,也在女子大学兼课,他说:“女子大学的功课本是温源宁的,繁琐得很。八个钟点不算,倒是六种不同科目,最烦。”
名作家张中行在30年代曾在北大听过温源宁的英文课,他在《负暄琐记》一书中,这么描述:“是三十年代初,他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文组的主任,每周教两小时普通英文课。我去旁听,用意是学中文不把外语完全扔掉,此外多少还有点捧名角的意思。第一次去,印象很深,总的说,名不虚传,确实是英国化了的gentleman,用中文说难免带有些须的嘲讽意味,是洋绅士。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洁而考究的西服,年岁虽然不很大,却因为态度严肃而显得成熟老练。永远用英语讲话,语调顿挫而典雅,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中国人,英语学得这样好,使人惊讶。我向英文组的同学探询他的情况,答复不过是英国留学。我疑惑他是华侨,也许不会说中国话,那个同学说会说,有人听他说过。后来看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知道徐先生也很钦佩他的英语造诣,并说明所以能有如此的原因,是吸烟的时候学来的。我想,这样学,所得自然不只是会话,还会搀上些生活风度。问英文组同学,说他有的时候确是怪,比如他的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他却从来不坐,遇见风雨天气,夫人让,他总是说谢谢,还坐自己的人力车到学校。只是听他一年课,他就离开北京大学。到哪里,去做什么,一直不清楚。”
其实在1933年后温源宁南迁来沪,同年6月,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来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温源宁在清华大学授课时是钱锺书“最敬爱的老师”之一,他对钱锺书这个学生格外欣赏,给过“超”的最高分。在钱锺书刚刚读大学三年级时,温源宁就主动介绍他要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钱锺书将这个消息用航空快信告诉父亲,钱基博于1931年10月31日给儿子回信,告诫他要谦虚,“勿太自喜”,因为“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声名大、地位高”更加重要。因此,身为光华大学文学院长的钱基博聘请温源宁为光华大学教授。钱锺书的旧诗中,有一首题为“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足见二人交情之深。
1935年温源宁应吴经熊博士之邀,担任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 sia Monthly)的主笔。吴经熊在他的英文自传《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就提到1935年5月6日,是“我组织的《天下月刊》编辑部在上海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聚会”。至于何以要办这个英文刊物呢?吴经熊说:“我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 Weekly)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了温源宁,他曾是北京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我对这个人的学问和人格有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一天,我们谈起了办一个中英文的文化和文学期刊——以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的可能性。这只是一时之想。这样的一种期刊会显得曲高和寡,很少会有人订阅,不能自养。谁能资助它呢?我们只是谈谈而已。正巧,我在担任立法院的工作时,还兼任孙中山文教进步研究所宣传部的部长。一天早上,我和孙科博士在公园散步时,谈到了我与温源宁的谈话。出乎我意料,他对这件事比我还要热心。他马上说:‘给我一个计划。研究所也许可以支持。’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交给他。他作为研究所主席立即就同意了。我和源宁一起商量编辑部人选,决定请林语堂和全增嘏。他们两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们还请了余铭作我们的广告经理,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开始运转了。我们的办公室位于愚园路,‘愚园’字意为‘傻瓜的花园’,这正好用来描述我们。‘天下’一名是我建议的。我在孙博士那里看到一张很大的横幅,上书‘天下为公’四字,就是‘普天之下的万物都应该为人民所享’的意思。我想,我们的杂志也应谈论天下大事,要与别人分享,‘天下’倒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我的建议在编辑部第一次会议上被采纳了。”
吴经熊提到他初识温源宁是在《中国评论周报》的一次宴会上,1934年1月温源宁加入了《中国评论周报》的撰稿编辑行列。在1月4日出版的第七卷新开了一个专栏,Unedited Biographies(人物志稿),陆续撰发二十余篇评介当代中国文化名人的文章,对时贤加以月旦,“评头品足”一番。林语堂曾将其中写吴宓及胡适的文章译成中文,分别在其主编的《人间世》第二期(1934年4月20日)及第三期(1934年5月5日)发表,引得文化学术圈内好一阵“热闹”。1935年1月,温源宁挑出其中的十七篇,吴宓、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遇春、王文显、朱兆莘、顾维钧、丁文江、辜鸿铭、吴赉熙、杨丙辰、周廷旭、陈通伯、梁宗岱、盛成、程锡庚,取名为“Imperfect Understanding”,交付上海Kelly & Walsh Ltd.(别发洋行)刊行。
温源宁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些对于我所知的一些人的一知半解是我闲散时候写的。自然,它们的合适的安身地应该是废纸篓。不过它们曾经给有些朋友以乐趣,也就是适应这后一种要求才把它们集在一起印成书。我相信这里没什么恶意,也不至惹谁生气。不过,也可能有一两位不同意我关于他们的一些说法。如果竟是这样,我请求他们宽恕。”温源宁透过表面,深入内心,一针见血地评论各式各样的人物,文笔悠缓雍容却不失幽默,正是英国散文Essay的特点。
钱锺书一生恃才傲物,真正受到他内心钦佩的现代学人似乎不多。然而,他却对温源宁十分佩服和亲近。同年6月他在《人间世》第二十九期发表了篇书评,将书名译为《不够知己》。钱锺书说:我们看过温先生作品的人,那枝生龙活虎之笔到处都辨认得出,轻快,干脆,尖刻,漂亮中带些顽皮;从侧面来写人物,同样地若嘲若讽,同样地在讥讽中不失公平;温先生是弄文学的,本书所写又多半是文学家,所以在小传而外,本书中包含好多顶犀利的文学批评,其中名言隽语,络绎不绝;不过,“本书原是温先生的游戏文章,好比信笔洒出的几朵墨花,当不得现代中国名人字典用”。话虽如此,后人对温源宁这些“游戏文章”引用率之高,恐是温、钱两人所始料未及的。温源宁在今日还未被遗忘,要归功于这本书了。
《天下月刊》是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印行。《天下月刊》是民国以来水平最高的英文学术性刊物。吴经熊在《回忆哲生先生二三事》文中说:“《天下月刊》第一期是在二十四年(1935)八月问世的。发刊词是哲生先生所贡献,指出本刊的宗旨,主要是在沟通中西文化。《天下月刊》一共出了五十余期。起初编辑部设在上海,上海沦陷后,搬到香港,到香港沦陷,才始停版,迄未复刊。”杂志由温源宁主编,林语堂、全增嘏、姚莘农(克)等任编辑,温源宁每期都写有编辑前言,除此而外他还发表不少篇的文章,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黄芳指出有《中国绘画之人种特征》、《爱尔兰诗人A.E.诗作》、《当今英国四诗人琐谈》、《奥布理琐谈》、《艺术历程》等大量的文化专论以及图书评论文章。他着力译介英国文学作家及作品,为英国文学向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做出重要贡献。这些论文不同于《不够知己》的英式Essay的笔法,它们都是严谨而掷地有声的文章。可惜的似乎很少人注意这些文章,若能将这些文章搜集,并译成中文,当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温源宁的学术思想。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这么描述:“这些文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以讲英语自豪。温源宁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生,回上海之后,装出的模样,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他穿的是英国绅士的西装,手持拐杖,吃英国式的下午茶,讲英语时学剑桥式的结结巴巴腔调,好像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字眼才可发言。吴经熊在哈佛大学读法律,他与温源宁不同,不肯穿西装,讲英语时故意带点宁波口音。邵洵美常在《天下》投稿。他是上海富家子弟,在剑桥读过两年书。他是追随徐志摩的新诗人。家住在杨树浦,每天开一部轿车到大英租界找朋友,逛书店,寻欢乐。他有老婆小孩,却又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结婚。洵美表面上厌恶一切旧思想、旧风俗,却不肯穿西装。这批骚人墨客略带矫揉造作的举止,无非是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想找出一条和谐的出路。语堂自己觉得当时对许多事都必须有所选择,是要西方的,还是要东方的,要新的,还是要旧的——由双足所穿的鞋子以至头顶所戴的帽子都要选择。他刚从外国回来时,穿的是西装,后来改穿长袍,但仍旧穿皮鞋。后来他又认为中国旧式的小帽子比洋帽较为舒服。”
今年已九十五岁高龄的诗人钟鼎文(笔名番草)在接受访问中,曾谈及他在1937年受邀参与创办上海《天下日报》,那是一份四开的小型报,由他任总编辑,邀来诗人艾青担任副刊主编。中文的《天下日报》与英文的《天下月刊》是姐妹报刊,因此之故,他与温源宁也相熟。
除《天下月刊》主笔外,温源宁还担任过太平洋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中国访英团团员、泛亚会议中国代表。1936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处住香港办事处主任,1946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起任国民政府驻希腊大使。在担任“希腊大使”期间的1962年10月10日,即第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中,阿尔及利亚的左倾总理班拜拉发表其首次演说,宣称要使世界和平必须让新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班拜拉发言时,温源宁半睡半倦的坐于“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在班拜拉的政策演说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与中立集团的代表们为他鼓掌喝采。此际,温源宁向四周一顾,迟疑了一刻,也参加了他们的鼓掌。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以醒目的大标题刊出:“班拜拉保证与殖民主义奋斗,中国代表也参加喝彩。”据《陈雄飞先生访问纪录》(稿本,许文堂、沈怀玉访问)说:“温源宁因打瞌睡跟着喝彩的新闻曝光后,原本只是一件小事,不幸经由媒体和共产集团刻意渲染后,对我国的形象造成不少损害。消息传回国内,立法、监察两院的委员要求政府勇于认错,并撤换温源宁大使以对此事负责。当时,外交部政务次长朱抚松还为了此事到立法院备询,但他的说明并未获得多数立委的谅解。后来事情愈演愈烈,美国的侨界与报界批评、报导比台北还来得激烈,侨界领袖甚至发电给行政院、立法院、外交部长,要他们严办此事。正当各方对此事僵持之际,我国代表团的薛毓麒在纽约召开记者会,代表中国代表团公开发表意见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联大发表演说,各国代表照例都应该起立,这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和风度,我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温大使是位干练的外交官,自当懂得国际礼仪,《纽约时报》的这则报导,仔细推敲确实有很多问题,因喝彩只是外在的表示,并不表示温大使同意对方的看法。’他并举古巴元首在联大中曾把美国攻击得体无完肤,但美国代表团人员在他演说结束后,仍然循例起立,这是国际礼仪,美国代表的起立不见得是对古巴元首的支持。薛毓麒的这番出面辩解,无形中也化解了这场风波。”
温源宁从1947年派驻希腊大使,至1968年9月“卸任”,任期长达二十一年之久。历史学者许倬云在《许倬云先生访问纪录》(稿本,陈永发、潘光哲、沈怀玉访问)中说他在1962年在美国学成归国时,曾透过他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温源宁的次子温祖希,写信给温源宁,因此他在希腊见到温大使。他说:“温老先生在希腊做了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华民国不敢把他调回来,怕一把他调回来,希腊就要跟我们断交。当时希腊还有王室,希腊国王五岁时曾经被他抱着坐在膝盖上。他的英文好得很,在希腊几十年没什么公事可办,闲来无事就研究希腊历史,后来他回国,台大外文系请他教英文,没请他教希腊史,实在可惜了。……有一天老先生赏饭,傍晚六点多派人来接我到家里吃饭喝酒聊天。我不喝酒,只好猛灌茶,但是到了八点多还不开动,我都快饿死了,我说:‘老伯我很饿耶!’他回答:‘没关系,给你吃点小点心。’我说:‘吃点心?那晚上饿了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你先吃点心。’后来把我拖到卫城面前一间小餐厅吃饭,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卫城浴在月光中,甚有韵味。然后他又带我出来,向我娓娓道来,讲哪块石头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有什么历史典故,quite an enjoyment!第二天他又开车带我到海神庙,底下海浪碧波荡漾,浪潮拍岸,他老人家一时兴起背了几首希腊诗给我听,可是我不懂希腊文,他一句希腊文,一句英文,背得很起劲。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学者外交官了。在希腊盘桓那几天,温老先生很高兴,我也很快乐,他老人家高兴是因为难得找到人聊聊天,而且很投机,与他和一般外交官聊天不一样,我们之间天南地北,上天下地都能谈,那是我生涯旅行最愉快的一次,真是舒服。”
温源宁于1968年卸下“大使”职,回台定居。他曾在台湾大学教西洋文学史,又受张其昀之聘,担任中国文化学院西洋文学研究所所长。据曾在文化英研所读书,后来在静宜大学英文系任讲师的何沐莲老师回忆当时上课的情景说:“我们英研所学生到温所长源宁家去上英国文学,我帮他向书局买Norton第二册英国文学集,他要自付款。他家客厅米色沙发大方,大书柜满是书,欢迎同学在那儿借阅。餐厅和客厅之间柜子上摆一幅心仪照片。大而椭圆形餐桌上置放一面玻璃垫。大伙儿围坐一旁听课。他面貌清秀,眼睛炯炯有神,眉宇之间严肃认真,鼻直挺鼻头有肉,下有希特勒式须,剑桥式英语随口说出,腔调或顿,又绅士风,极有吸引力。他说读作品要了解时代精髓,才能对时代和作者有‘perfect understanding’,否则就成‘imperfect understanding’。他首度强调Minor writers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ir age:therefore,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m.意指次要作家代表当代,具有时代意义,吾人不能忽视他们。他偏好T.S.Eliot艾略特、A.E.Housman侯司门、D.H.Lawrence劳伦斯等人的诗作品。据说老师最早向国人介绍他们的作品。当时温老师并未提及早年他学生钱锺书赞美他‘那枝生龙活虎的笔’。第一次课后在婉约贤慧温师母的安排之下,在椭圆形桌上,Tea Time大伙儿享用典美餐点,荣幸之至。”
之后,温源宁因健康欠佳,逐渐摆脱教书工作。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温源宁因一时激愤不幸中风,缠绵病榻多年,于1984年1月13日因肺炎在台北“空军总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有关温源宁的生平资料流传在两岸都极为稀少,很多人都听闻过他的大名,但对实际的一些细节,却都无法详述。笔者曾访问过女诗人徐芳女士,她在北大曾听过温源宁的课,但她的回忆和她的同班同学张中行所去不远,因此在此不再赘述。倒是在她们北京大学在台的校友会的通讯簿上,我查到温源宁晚年的住址:台北市敦化南路369巷36弄19号之4五楼。笔者曾试图去找寻他邻居中的老者,看是否能问到一鳞半爪,但无奈几经数十年的沧桑,当时的里弄已不复存在矣。在苍茫的暮色中,望着过往的车潮,如烟往事,已然苍老!
众说《温故》
民间的历史
徐长云
《温故》里既有学者们理性的叙述,更多私人化叙述,甚至是普通百姓的叙述。真正的历史,不仅由名人铸造,更由平凡而可爱的普通民众铸造,他们一起构成时代的基石。他们真实的情感,沟通着今天人们的心。
那个外孙女眼中的齐如山(戏剧家),孙女眼中的张元济(学者),那个生活在鄂北大富河岸边的普通农民“我公公”,那个叫石妹馨的乡下种田不识字的“我婆婆”……亲切,真实,朴素,高贵,名人的平凡,平凡人的伟大处,交相辉映,而温情流溢其中。
许多篇章写到胡适,那个在特定历史时段,走或留,赞或骂,作为或不作为,温和或尖锐,中肯或偏颇,被A骂或被B骂,种种矛盾费解之处,只基于他个人的立场、主义、修为、原则。各个篇章从不同侧面,展现出一位历史人物的丰富、复杂性。真实可信更加彰显。
在“人物”、“记忆”、“口述”、“回眸”诸栏目之外,还有“风物”,比如浏阳河畔的“谭嗣同故居”。它的古朴深邃,将人们带入对谭复生“剑胆琴心、慷慨就义不复生”的追怀。
历史不冷硬,它需要真诚和温度。“温故知新”,在每个即将成为历史的当下,记取曾经,开创未来。
(原载《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