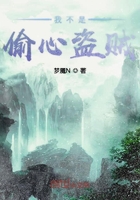刘桃枝带着人,在很远的地方就跪拜,高俨却命令将其捆绑起来,所带禁兵四散逃走。帝又派冯子琮召俨,俨推辞,说:“士开罪该万死,他谋废至尊,剃去母亲头发让其做尼姑,还带领兵马屯驻在孙凤珍家中,因此臣矫诏诛杀了他。尊兄若想杀臣,臣不敢逃罪,若放臣,则请派姊姊来召臣,臣马上就来相见。”
其姊姊就是陆令萱,俨想诱骗出来后将她杀掉。
令萱执刀站在帝的身后,听说之后战栗不止。帝又派韩长鸾召俨,俨准备去,刘辟疆扯着他的衣服说:“如果不杀陆太姬,殿下就无理由入宫。”
安德王高延宗刚好从西边回来,想助成其事,道:“为什么不入宫?”辟疆答:“人少。”
安德王回头看了一眼众人,说:“孝昭帝(高演)杀杨遵彦(杨愔),只有几十个人,今有众数千,怎能说人少?”
后主哭泣着启禀太后:“有缘份还能看到母亲,没缘份就永别了。”之后急忙征召斛律光,光同时被高俨召唤。
斛律光听说士开被杀,拍着手掌大笑说:“龙子做事,确实不同于凡人。”
他入宫到永巷拜谒后主。帝率领宫殿卫士和四百步骑,授给他们盔甲准备出战。斛律光说:“小儿辈弄兵,一交手就会乱套。俗语称‘奴见皇上心死’,至尊应该亲赴千秋门,那琅琊王就不敢乱动。”皮景和认为斛律光说得对,后主便听从了。
光徒步走在路上,让随行站出来喊:“皇帝来了。”
高俨部众听到后吓得四散而逃。帝停马立在桥上,高呼俨,俨站着不肯开步。斛律光走到高俨身边,说:“天子弟杀一汉,有何苦恼?”拉着他的手,逼着他往前走。
斛律光向帝求情:“琅琊王年轻,肠肥脑满,容易轻举妄动,长大后就不会这样了,希望皇上宽恕其罪。”
高纬哪肯,心下早已杀机大动,呲牙咧嘴的抽出高俨的带刀,就差手上使劲。
此刻,宫门外缓缓来了一骑,造反的部众侧目一看,竟然是那任城王。躁动的人群一时间安静下来,自动的为他行处让出一条小径。
人群中,高湝嘴里叼着根麦穗,不急不缓的上了桥。
高纬、斛律光和高俨看着他走近,心里不知道这任城王什么打算。男人呸的一声将那麦穗衔出,翻身下马,凝眉看着那高纬拔出的刀,一把按回了鞘。
“皇帝,孝悌手足之情,不可不顾。琅琊王年少,但心思确是好的。皇帝三思,可别重蹈了前人的覆辙。”
这话语调不高,分量却重。当今齐国前线不稳,高纬手上拿着一半的兵权、斛律光、高湝手上虽然兵不多,可威望健在。
高纬的那部分死士一部分还是从羽林中调过去的,所以今日宫中禁军数量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
高纬看着斛律光,又看着高湝,心里来回纠结。
算了,且忍一时。
高纬将琅琊王用辫子缠头乱打一气,许久才停手。逮捕了伏连以及高舍洛、王子宜、刘辟疆、都督翟显贵等人,亲自抄箭向他们射击,然后开刀问斩,肢解后,全部放在大街上示众。高纬还想杀掉高俨手下的文武职员。斛律光认为他们都是勋贵子弟,杀了就会引起动荡,赵彦深也称《春秋》只责罚将帅,于是依罪轻重进行了罚处。
此后太后将高俨收养在宫内,俨的食物她都要先亲自尝尝。
陆令萱劝告高纬说:“人们都说琅琊王聪明雄武,天下无双,观其容貌,殆非人臣。自掌专杀大权以来,常有恐惧,陛下应该早点为他打算。”何洪珍与和士开一向关系很好,也请求杀掉高俨。
犹豫不决时,帝派人用小轿秘密将祖庭接来问计。祖庭称周公诛管叔,季友鸩庆父,帝明白了他的话意。
帝打发高俨赴晋陽,并指使右卫大将军赵元侃在途中诱捕俨。元侃说:“臣往日事奉先帝,每天看到的是先帝对王的喜欢。今天臣宁肯死,也不能去。”
高纬无奈,出元侃为豫州刺史。
一次吃饭的时候,高纬装作不经意间跟胡太后提起:“明天准备和仁威一块去打猎,当早出早归。”是夜四更时分,帝召高俨,俨怀疑有诈。
陆令萱罚没入宫后抄入了长广王府,虽只是高纬的养母,但对高俨也还算熟悉。
她对俨说:“阿兄唤你,你为何不去?”高俨出门来到永巷,被刘桃枝反捆住了双手。俨大喊:“我要见太后!我要见尊兄!”刘桃枝用衣袖堵住他的口,拉起衣袍蒙住他的头,背负着他到了大明宫,此时高俨鼻血满脸,马上就被杀死了,年仅十四岁。不脱靴,草席裹尸,埋在室内。
刘桃枝坐在大明宫一个角落,转了转发酸的肩膀,看着暗部将杀人现场处理完毕。
她本来以为,自己在桥上向高俨缴械,是暗中帮了斛律光。按照女人的推测,那夜义父猜出了皇帝动了杀心,必然要做出反应。而这琅琊王的宫变,没有斛律光从中斡旋,他可下不来台。说不定,高俨一个冲动,真将高纬踢下了王座。
那,可就不好办了。
因为高俨虽然年纪比高纬小几岁,但为人却着实老辣,不好对付。
经过了这次大乱,斛律光顺水推舟让高俨替自己除掉了忌惮自己的和士开,而高纬又替他除掉了高俨,最后自己渔翁得利。而傻傻的高纬反而会感激斛律光动乱中替自己解围,心一软还会放过斛律光。却不知,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让她始料未及。
自从宫变过后,余波未平,刘桃枝宫里埋头处理公务之余,能在高纬身边,就在高纬身边。
她自知自己杀了琅琊王,那高湝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想见她。
虽然她只是听命于高纬,但是恨这种东西,到底和爱一样毫无道理可言。
那夜斛律光的话,将她拉回了现实。
她这双手,早已洗不干净。
复仇就是她的呼吸,复仇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
平凡的生活,终究只是遥不可及的梦。
一天傍晚,斛律光丞相府佐、名叫封士让的偷偷摸进高纬寝宫,说是要有密奏亲自面见高纬,连刘桃枝也不给看。
刘桃枝站在门外,小心的听着里面的谈话声,却也听不出个所以然。只隐约听见要送给斛律光一匹好马。
翌日,高纬果然下令要赐给斛律光一匹好马,说是明天要去东山游览,相王可乘此马。高纬吃过午饭后,有内监进来通传,说那咸阳王进宫谢恩面圣。高纬屏退众人后,神秘的对刘桃枝说——
“等那老头进来,朕问他几句话。问完了,你就看朕脸色行事,懂了吗?”
原来,竟然是个鸿门宴。
你终归还是躲不掉。
女人直到这一刻,都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斛律光。
与高湝一起的生活,确实让她体会到了做一个平凡的人的快乐。可这并不能让她就这样放弃她和陆令萱的同盟。
老者那夜的话不断地萦绕在耳际,一瞬间,女人又仿佛回忆起了高涣刚死那会儿自己绝望的心情。
或许老者说的是真的,她注定只能是一个杀手。
两个女人在墓前发下毒誓,为了复仇,愿意堕入阿鼻地狱。
但,如果现在调转车头杀掉高纬,斛律光胜算几成?就靠府里那一千私兵,就算杀了高纬,也不能杀尽那外放的许多姓高的王爷。
当然,眼皮子底下的高湝将会首当其冲。
斛律光得位不正,必有殃灾。
不行,这天下一统,还是得靠西边的宇文周。
她又想起了那夜老者的话。
——你就做他让你做的就好。
——你要做那立于天下顶点的杀手,这不是老夫从小培养你的夙愿吗?
好吧,既然如此——
您九泉之下可别怪我。
这凉风堂和晋阳那个恰好同名,却不是一处,而是高纬按照晋阳游豫园中的规模依样画葫芦在邺都新建的,名字也懒得改。
斛律光被领着走进了凉风堂,被刘桃枝从身后偷袭,拉杀于堂上。但他毕竟老将,临死时有所反抗,高纬急命几个力士一拥而上将老将死死按住。
女人对杀人,一直很在行。只是她没想到,这次会这么轻松,相王简直就像求死一样。
“相王毕竟还是老了。”女人蹲下身,看着眼前吐着血泡的老人。
老人因为喉管被割了一半,氧气供应不到大脑,浑浊的眼珠充血严重,嘴角也溢出一注暗红色的血流。老将口唇、颜面青紫,心跳加快而微弱,处于半昏迷状态,紫绀明显,呼吸逐渐变慢而微弱,继而不规则,心跳随之减慢。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桃枝常为此事……”
老人挣扎着,一只手贴着地扫动。那手缓缓地移动到脸侧,轻轻盖住左眼。
斛律光朝着杀死自己的女人最后笑了,皲裂的嘴唇微动传递着最后的讯息。
——根源。
女人站起来,看着老人合拢于左眼的手。她也将自己的左手合拢,遮盖在自己被白茫茫的光线刺痛的左眼上,再躬身合上了他的眼。
——你救了我,养了我,教了我,却又最后毁了我。你我之间的恩怨,今日终结于这凉风堂上,孰是孰非,也就随风而逝吧。
刘桃枝带领着几个力士,在皇家园林中随便找了处向阳的山坡,恰好有一颗枯萎的巨大桃树。女人亲手在桃树下挖了一个一人大小的坑,将老人的尸体用绢布裹了抬进坑里,再合上了土。
“您曾说过,桃枝能够驱鬼。”女人合上最后一锹的土,喃喃自语。
她将铁锹扔在树下,抬头仰望高高的树梢。模糊的记忆中,浮现出几个碎片。
昏黄的烛火晃动,花鸟翱翔于破败的房间。
——姐姐你知道遗腹子吧?就是没见过父亲的样子就成了孤儿的孩子哦。
铁笼中,男人被业火所灼烧。
——就让业火烧光我们的罪,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树下的暴君眯着眼,身体被树叶间漏下的金子般的阳光所温暖。
——如果你没遇到七哥,你现在会不会是个平凡的女人,在一个平凡的巷角,锅里煮着平凡的饭菜,过着平凡的一生。
屏风后老人长髯颤抖,声如雷鸣。
——你的天分,你的潜力,注定了你不能做一个凡夫俗子。你要做那立于天下顶点的杀手,这不是老夫从小培养你的夙愿吗?
春风和煦,轻轻抚过窗下男人痛苦的眼。
——活着的人……总要向前看。
刘桃枝突然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分裂。
没办法彻底的去恨,真的很痛苦。
这是一个忠于自己欲望、完全靠欲望驱动的人。无论是成为御影卫,还是铁笼之上决定复仇,还是接受高湝,都是顺从自己内心本能的欲望。
但是,现在的她竟然对于自己心底的欲望产生了疑问。
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说,自疑,比什么都要可怕。
佛法有云,一切有情之物,终究逃不过爱憎的轮回。
深秋澄净的日光从天穹慈悲的洒下,将女人包裹于圣洁的光影里。
仙乐环绕,这一刻,女人的左眼彻底失明。
刘桃枝一时间被左眼的剧痛所惊醒,左脸一注滚烫的灼烧感。
“统领……您的左眼……”一名禁卫惊叫。
女人手掌擦过左脸,放在右眼前徐徐张开。
血,淡红的血,宛如枯败的桃树下一捧桃花。
女人不愿意被部下看见自己流血的样子。她强忍住左眼的剧痛奔出内宫。狼女站在城门上,大脑一片雪白,天下之大,竟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的安身之处。
对了,她还有他。
她选择了一条最为僻静的路线出宫,一只眼睛失明的怪异感让她难以准确的捕捉到物体的位置。一路跌跌撞撞,到了日落之后才从后门摸进任城王府。
她没有惊动王府中的奴仆,只艰难的寻到高湝的书房。晚饭后的时间,他一般都在这里看些旧书。女人站在书房的窗下,从窗框鱼贯而入,不愿意让房门的守卫看到自己落魄的样子。可刚一跃入书房,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她越过案几和屏风,来到最里面的书间。
高湝趴坐在那张榉木黑漆攒银丝的书案前,脸贴在案上不省人事,两侧滚落着七八个空空的酒坛,还在滴落着混黄的液体。
男人一手攒着一坛喝了一半的酒,一手捏着一张纸,纸被酒浸透了一半,黑色的墨迹被诡异的渲染开。
女人绕到男人沉睡的背后,轻轻的抽出那张纸。
是一封信。
刘桃枝将剑插回腰间,犹豫着要不要看。今日的他,有点奇怪。可她看到那信的落款,斜斜的“光顿首愧奏”几个字,身体仿佛遭了雷劈一样定在那里。
女人将信倒转,从头开始阅览。
——任城王敬启:
事出仓促,老夫怕是时日无多。回望这一生,无愧于先神武帝一起策马扬鞭的岁月。弥留之际,辗转反侧,实难将一桩秘密带入坟茔,只因这件事牵扯到刘氏。
或许任城王已经知道,名为刘桃枝的女人乃是老夫于二十几年前在那令尊父暴死的讨逆战后收养的遗孤。今日想来,老夫本不该多此一举,心中也多有悔意。多年后我才辗转多人秘密寻访,得知那女子乃是令兄文襄皇帝和那文宣皇后隐秘中种下的恶果,老夫思虑再三,为着父女情分和皇室风评不忍将密事曝露。哪知此女年岁微转,竟与七公子眉目传情,定下终身。老夫为着伦理纲常不忍说破,却万万不敢同意这门亲事。哪知文宣末年,七王惨遭屠虐,此女竟然为情所困,所思所想只为颠覆宗庙。这十年间,多少王公宗亲死于其手,孝昭帝和武成帝的死,老夫看来也颇多怪异之处。临别之际,慌乱着笔,万望任城王为着高家江山,手足之情,将此妖女手刃与太极殿祖宗牌位前,以告慰死去的诸王,拯救苍生于危难。
——光顿首愧奏。
女人轻轻的将信扔回案上,受伤的眼瞳泪血俱下。
义父,您竟然死了也不肯放过我,定要将我推上绝路,断了我对世间的最后一缕羁绊。
只为了……将我培育成……您心中无情的杀手。
看着高湝熟睡的侧脸,此时的她,恍惚间终于明白了那夜笼中男人大吼出那句话的心情。
——既然你已经知道,那我就不能再装作不知道继续骗自己。
是啊,最重视手足之情的他,知道了全部的真像,怎么可能还会接受自己。
她直接毒杀了高演,扶持高湛间接的杀害了老四,老五,与陆令萱合谋假借胡太后之手毒死了高湛,扶持高纬间接杀害了老十二,更遑论那么多宗室诸王惨遭她的虐杀。
甚至那无罪的高涣,也……
女人俯下身,轻轻的将熟睡的男人额侧的几缕乱发别于耳后。
“与君共度的半年时光,是桃枝难忘的回忆。只是……你我终将永别。”
血混杂着泪滴落在男人右脸的伤疤上,他痛苦地抖动了下睫毛,侧过头又沉沉睡去。
雾夜,陆令萱的药房里,总是弥漫着奇怪的味道。
药房的主人轻轻的将涂上药膏的纱布在女人左眼上缠好结于脑后,再用白色的丝绢轻柔的拭去女人那因痛苦而滴落的冷汗。受伤的人即使坐在药炉旁,也止不住的打着冷战。她紧紧的将两手横抱住自己的胸口。陆令萱转身,将一条毯子轻轻的披在她的肩膀,又将炉火烧得更旺盛了。
但女人还是觉得全身冰冷。
“妹妹还是决定要走了么。”
女人将毯子紧紧的裹住自己发抖的身体,仅剩的右眼中再也不见往日的半分神采,剩下的只有痛苦和疑惑。
“姐姐看我这……伤……也知道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统领没了一只眼睛,陛下是不会再重用我的。”
“陛下那边自有我去说。我说一,那小皇帝绝不敢说二。”
“陆姐姐……不怪我吗……”
身着宫中盛装的太姬笑了:“我为什么要怪你?”
“我……我与任城王的事……也并没有和姐姐说起过。”
陆令萱不语,只是又在那火炉中填了几块宫中精制的炭火。半晌过后,伴着火炉中噼啪的炭火裂开的声音,她才缓缓开口。
“我起先确实觉得奇怪,只是怕你有了新欢却忘了复仇。可之后,任城王却有意交了兵权赋闲在家,我这才明白你的心思。大概……你是想拖住他,对吧?”
“……是。如今我的过去被斛律光捅出,再留在宫里,只怕只会成为姐姐负担。我……想去长安,那里……我认识一位遁世的名医,或许——”
“妹妹糊涂啊,既然怕事情捅出,那就该登时将那任城王一不做二不休的杀了,这样不就无人知晓了?”
“我……”
女人将毯子裹得更紧了。
她知道,这是那被自己杀死的老人最希望她做的事。
“我的心很乱,从来没有这么乱过。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我需要静一静,想清楚是不是应该……杀了他。”
陆令萱松了一口气。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发抖的女人跪倒在地,连磕几个响头。陆令萱也不去看她,只是盯着熊熊燃烧的炉火,轻抚着碎蜂甲,又是半晌才开口。
“其实……我很羡慕你,心里还能装下别人。如果我是你,我也不知道会怎么选择。”
此时已经权倾朝野,万人之上的陆太姬那依然清秀的脸映着火光,被服帖的挽起的青丝中隐约可见几缕银线。
“如果不是太子婚夜你制止住我,我也不会坐到今天的位置。朝中的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无法回头。今日你杀了斛律光,给了这个腐朽的王朝致命的一击。大势……已经铸定。”
女人抬起头看着火炉旁的她。
“妹妹既然决定要走,我不会拦着你。或许会为你感到遗憾,你没能亲眼见证这个王朝的覆灭。”
“剩下的……就全靠姐姐了。”刘桃枝重重的伏下了头,呜咽难语。
“你去吧。”小字行针的女人幽幽的眼中浮现出藏不住的哀伤。
刘桃枝从胸口摸出一封信,双手恭敬的放在行针的脚边,伏连许久才站起来,摇摇晃晃转身离去。
从此以后,邺中再也没有一个名为刘桃枝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