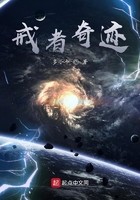春秋战国,时局纷乱,群敌窥伺。身处中原的鄢国,地产丰饶,人畜兴旺,金银铜铁矿颇多,周围的郐国、厉国、丹国皆虎视眈眈。
鄢国主公生性软弱,胆小怕事,面对周围诸侯国侵略城池,掠夺人口与牲畜的事,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甚者,郐、厉两国兵马攻占鄢国北部二十余座城邑,其中就包括鄢陵,乃鄢氏祖脉之地,公然向鄢国公勒索钱财与土地。
正值鄢国大都督元培胜在中央大营训军。得闻消息后,元培胜坐在帐中帅椅上,一言不发,面色铁青,众副将皆咬牙切齿,沉默不语。
但谁也清楚,没有国君之令,谁都不敢调拨兵马,而纵观朝堂之上,连国君在内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言战之词,都未听有人提及。
元培胜起身,遂解下半虎符与匕首,言道:
“老夫不以帅令,即讨郐、厉二贼,愿附者,同老夫上校场誓师!”此言一出,打蔫脑袋的裨将们顿时来了精神,异口同声,愿同大帅共赴生死。
来到校场,千夫长们早已集结好队伍,一个个士气高昂。元培走向指挥台,途中接过一个旗兵的军旗,旗面上正绣着的是黑底白字的大“鄢”。
“大家都是鄢国的好儿郎,而老夫,却不是鄢国的好元帅,如今贼寇犯进鄢陵,而我等,未出一兵一卒,这张大旗,何能得守哇。”情不知所起,纵然间,老元帅涕泪肆流。
只见他双手扶着旗杆,不知不觉,人已矮下半个身子,几个副将见状,赶忙向前搀扶。
元培胜起身后,将周围人推开,顿顿旗杆问道:“今老夫不得符令,欲要带大家北上退敌,收复鄢陵,大家敢不敢?怕不怕?”
“不怕!不怕!……”底下声音陆续传出,越传越大。
“纵然是个死,死在战场上,也比窝囊屈死强!我们要驱逐敌寇!收复鄢陵!”一位体形微胖的副将也发了话,受到底下众战士的山呼:
“驱逐敌寇!收复鄢陵!……”
元培胜持旗如持枪,重重往台上一顿,旗杆破入板中,稳稳扎住。振臂一挥,三万兵马有序拔营北上,只留下身后漠漠烟尘。
看到鄢国的大军奔赴而来,郐国公与厉国公均感诧异,莫非真是自己把鄢国公逼急了?竟让大都督前来讨战。情急之下,两国公先行碰头,商量一个对策才好。
【营口处】
“郐老弟,郐老弟,来得正好。”厉国公正想去郐国大营,未出营,便碰到了前来的郐国公。立刻迎到帐中议事。
“我的厉哥哥,你说说,这次是怎么回事,莫非我们真把那个娃儿打急眼了吗?”郐厉二国犯鄢国多次,从未有过鄢国大军与之正面对垒之事,一般都是能顺利捞上一笔肥厚的赎金。
“不曾听闻鄢都有动静呀。”厉国公不得解。
“当务之急,是要想,如何应对鄢国这三万之师。”郐国公觉得这事有点火烧眉毛,毕竟自己带出来的军队,缺少很多正式的军需器械,特别是粮食短缺,在他国领地上,更是耗不起。
“正在想,正在想。”厉国公绞尽脑汁想着对策。
“有了,有了。”厉国公一拍脑门,想到了对策,郐国公坐不住,直立起身子请厉国公细说。
“鄢陵闭塞,其重要的防御,当在石柏与段柏二邑。只要我们放他进入鄢陵,于两邑处切断,令其首尾难顾,这不就成了稳中捉鳖的事了吗?”厉国公得意地笑道。
“计虽是好计,但鄢国的大都督元培胜可是一个老将军,这点计谋,他们上当吗?”郐国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
“屠杀鄢陵的百姓,详装我们的大军屯居鄢陵的假象,我不信,他不着这个当,人一旦被仇恨蒙蔽双眼,做事是不会计后果的。”厉国公颇有几分胜券在握的姿态。
“老哥这招狠呐,郐国若有不敬之处,还请老哥多担待些。”郐国公啧啧称道,心里也有些许害怕这类人。
“哎,又不是真要做,把这个风放出去就好了嘛,鄢陵多是鄢国贵族后裔,真屠了,我不就真和鄢国上下反目了嘛,不值当,不值当。”罢罢手,两人吩咐下去,一切也正是按料想的那样发生着。
听到鄢陵百姓遭受屠害,莫说元培胜,全军上下无不激愤。元培胜率先遣军一涌杀入城中,结果发现城中并无埋伏,也无敌军,倒是身后频频传来遭遇伏击的令情。整个大军果然中计,被分切三段,首尾不能相应,被郐、厉大军围剿蚕食。
元培胜率部在鄢陵附近激战了三天三夜,士卒所剩无几,身负重伤的元培胜在属下的搀扶中躲进鄢陵深山。但郐厉二主,并未穷追不舍,而是任由鄢军残部进入山林,把军队驻扎在山下。
昏醒过来的元培胜四处张望,周围的士卒无不丧气着脸,不用他人讲,也知道此次是败了,还是惨败。生还的一名副将同元培胜讲损伤情况,逃进山里的,不足百人。七位副将也只剩下一位。
不知是不是无气力,元培胜全程未说一句话,也未进一口水,吃一口食。而是起身,从地下颤微微拾起一块柴炭,于洞壁之上,写下:愧对天地,唯有杀身成仁,祈保大鄢昌运。
【鄢都朝堂】
得知自己的大都督不遵王令,私自出兵,被困鄢陵山一事,鄢国公于朝堂上暴跳如雷,在鄢都朝议之上,破口大骂:
“郐、厉二国不就是想要钱财吗,给就是了!又不是给不了!好一个大都督元培胜!原以为他老沉持重,至少也能明事理,这下子,折我三万中原好儿郎。”
“为父擅自出兵是有违王令在先,但鄢陵乃主公祖脉之地,落入强寇之手是我鄢国奇耻大辱啊,身为鄢国的热血男儿们,岂能不挺身而出,报效朝廷!”正在说话的是身为元培胜的独子,鄢国骠骑将军元及。
“笑话!我都不觉得耻辱,何来的耻辱!就你们这些舞刀弄枪的武痴莽夫们,贪军功,图名利,才有这么多的借口。金钱能比人命更值钱吗!就想着怎么折腾,不想让我过个安生!”鄢国公拍案而起,说教元及。
“望主公准令,我愿领一万人马前去救父。”元及单膝下跪,行以军礼。
“刚说的就忘啦?俩父子,都是粗鲁莽夫,打打杀杀,没完没了,就不知道换个途径,哎!”鄢国公叹气失望。
荀大夫巴接承话:“主公德明精算,爱子爱民,三日后郐国公与厉国公相邀的鄢陵会宴,臣已准备妥善,珠宝一乘,金银五车,东北两城两邑割让郐国,西北三城四邑割让厉国,主公您看如何?”边说边奉上羊卷图纸。
“没点新奇的吗?怕这两位叔公不高兴。”接连的金银珠宝相送,土地割了又割,是把郐主与厉主的胃口越养越大了。
“臣的府上豢养了五位正值豆蔻华年,长相水灵的妾女,为报朝廷,臣愿纳贡主公,主公也可解近忧之急。”荀大夫颇懂鄢国公的心思。
“荀太令还是深知我心,不过,还得让我再挑挑,这二位叔公,还是老当益壮的哟。”鄢国公仿若自己得了宝似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荀大夫唯若,心里亦是欢喜,不消费力,把话言语之间,就迁升太令。这等阿谀奉承的手段为在场的武将所不耻,特别是元及与萧洛河,看见鄢国公与荀大夫淫容满面的样子,反胃作呕。
散朝后,元及倍感失落,父亲生死未卜,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萧洛河安慰他,义父吉人自有天相。
萧洛河何许人也,鄢国大都督元培胜的义子,因其剑法出神,武艺高强,为人敦厚,被鄢国公赏识,赐官都军校尉。
话说他的身世亦是离奇,早年间鄢国大将军的元培胜行军至萧家庄洛水河畔拾得的一个弃婴,初见弃婴时,置身软巢,灵鸟陪护,顿有金光护体,周围豺狼虎豹不敢靠近。待大将军走近时,灵鸟遣散,金光消失,只闻得一个婴儿咯咯乐笑,讨人喜爱。
元培胜念及自己尚有一子,初为人父,心怀慈悲,便收其为义子,因是野外所拾,小儿身份难识,又不能冠之元氏尊姓,遂以所拾之处为小儿取名萧洛河。
【鄢陵会宴】
鄢国公奉厚礼参宴。果然金银珠宝之物,郐国公与厉国公不屑一顾,陌陌然收下。幸好鄢国公早有预料,拍拍手,几位风姿卓越女子持流扇掩面,相继从屏风后出来,把两位老色主的眼睛都看直了。鄢国公会心一笑,此行心里便有了谱。
一段秀舞助兴过后,鄢国公大摆挥手:“此等尤物,二位叔公觉着如何?稍稍有所满意,便可尽情拿去!”
一番挑选的声乐过后,郐国公择了一位伴坐,厉国公选了两位左拥右抱,还有一位,鄢国公自然不会冷落,拉过纤手,坐到自己的身边。
“原以为这中原的儿郞里,七分忠勇,三分怂憨,怂憨之辈应尽出你鄢地,不料想此地一战,竟然可以得见浴血奋战的鄢地男儿。”厉国公讥讽道。
“厉叔公说得好,人人皆知我鄢人怂憨,断不敢兴战,大都督萧老儿是违我的令,擅自出兵,多亏二叔公出手教训,当谢,该饮一杯!让二位叔公劳师动众而来,一定是做晚辈的我平日里侍奉不周了,当罚,当罚三杯。”鄢国公端起酒樽,自饮四杯,全然不觉被羞辱。
“这土地之事,还得再议,我只得宜东与居来的两城两邑,厉国公只得三城四邑,我们手下的城邑可有二十一座,怎的,还要退还了不成?”郐国公不悦。
“这鄢陵的一城两邑就还于你了,毕竟为你鄢氏祖脉,于道义上,我们也不可取之。但其他的八城十邑,就不消再讲啦。”厉国公作出退让,言语里尽是轻浮。
“先谢过二叔公归还鄢陵,但剩下的八城十邑中,不是已割让五城六邑出去了嘛,剩下的尹桑、陈化、晓金三城四邑乃为河中要塞之地,拱卫鄢陵与鄢都,倘若真失在我的手里,百年后以何面目见我的父君呐。”鄢国公嘤嘤啜泣起来。
“贤侄莫哭,我与你郐叔公无这等意思,实话说了吧,是想要这三地的金银铜矿。”厉国公安慰道,郐国公也点点头,表示正是此意。
“小侄的主公之位便是当年二位叔公扶上去的,断然不会相信叔公会加害于我,使我身死国灭。”鄢国公先笑脸迎逢,又转言道:
“但这三城同样被东侧的丹国所觊觎,我若割让出去,且不论采掘难度、工匠之术,一旦丹国发难,此地必反复兴兵戈之乱,我如何安寝安食,惶惶度日太为可怕了。”此话一出,鄢国公偷偷察着两位叔公的脸色,见其二位一时之间言不出话来。于是自解道:
“何不如这样,金矿年采数吨,铜铁矿年采十数吨,三月一季,季季奉贡,巧作运夫,不教他国发觉,这样也避免叔公们陷于兵乱了。”鄢国公巧献计策,郐、厉二主觉得妥贴。
三人开怀畅饮,琴瑟萧萧,美妓作伴,好不快活,这时有人来报,鄢国大都督在鄢陵深山中自尽而亡。得知消息的鄢国公嚎啕大哭,涕泪肆流,悲痛欲绝。
“我的大都督哟,主公无能,来晚矣,未能护你性命呐。”边哭边自责起来。
郐国公与厉国公不知如何是好,也没想到会闹这么大,逼死了鄢国的大都督元培胜。想到鄢国公尚以他人的利益为先,自己也不好欺人太甚,何况郐、厉二主确实也不是心肠歹毒,不近人情之辈,见到鄢国公哭成这样,也避免鄢国举国上下的民愤,心软了下来,归还此次的所有城邑土地,只望鄢国公信守承诺,季季奉贡金银铁器。
鄢国公如愿以偿,接回大都督尸体,举国同悲,行国葬之礼,也算是对元府及全国上下的子民们,有所交待。于大都督的葬礼上,宣其义子萧洛河继大都督之职位,而独子元及承袭其父的大司马尊荣。
【大都督元府正堂】
披麻戴孝的元及,面无神情,眼神冷峻。萧洛河发觉了他的异常。走到他的身边,同他一起跪下,往火盆里烧秸秆碎皮,小声说:
“你不要做出傻事来。”
“你不是说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么?”元及冷冷回话,目不转睛地盯着火盆,机械般投着秸秆。
“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打击很大。”萧洛河不知如何安慰,也不敢看向元及。
“我并不嫉妒你承袭了父亲的职位,你不需要心怀愧疚,因为我清楚主公是什么样的人。”元及的话依旧没有温度,就似这六月飞雪的寒风天,异常而又肃杀。
“兵权被分散了,大都督也只不过是名不副实的虚职。”萧洛河有些失望。
“洛河,你一定要答应我,保护好鄢国。”元及突然陡转话题,转向望着洛河。
“你在打算着什么!你不要吓唬我。”萧洛河越发觉得不对劲,与元及四目相对时,越发能体会到这种感觉里透着深深的险恶。
“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我做好我该做的事,我们都是父亲的儿子,不是吗?”元及话毕,也烧完最后一把桔梗,遂而起身,拍拍下身,抖落秸杆烧毁飘出白灰,然后离开,留下萧洛河一人在空旷的灵堂里。
元及的身影渐行渐远,直至他一把扯开麻服,露出一身武服,腰间别着一把直剑,猜想中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
元及仅率五百死士,假作运送贡礼的乘卒,刺杀了郐国公,又硬闯厉国公的行宫,虽成功刺杀厉国公,但被众军围截,死于万箭穿心之下,五百死士亦无一人生还。
郐、厉二国新主上位,征战杀伐日益增多,知道自己的父君被刺是元培胜之子元及所为,两国一致伐鄢,萧洛河因知情不报,被鄢国公罢黜流放,贬为庶民。
【流放中】
在流放南荒的途中,突遇山精野怪,押解的差爷吓得屁滚尿流,溜之不见踪影,剩下手脚被铁链束缚的萧洛河,独自面对庞然的吃人山怪。
山怪一个猛然扑身,萧洛河一个翻身鹞子,骑在山怪背上,想凭手上的铁链勒住它,山怪暴怒,血盆大口之下咬碎了锁链。
萧洛河仗着好身手,很快便降服了山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被降服的山怪化成了一把重剑,剑把柄端的样式乃是一只饕餮神兽。
随着战事加剧,丹国的军队也趁火打劫,一路上的流民日益增多,轻贼盗寇,山精野怪四处横行,世道已经混乱不堪。即便如此,萧洛河也不敢忘自己元府子弟的身份,惩恶扬善,忠肝义胆,不从草寇之流。也在行侠仗义的路上,结识了一位身袭红装,黑发如瀑垂肩的奇异男子。
“你的剑法纯清至正,力道虽足,但灵活性差了些。”男子双手交叉于胸前,背对着萧洛河,评价道。
“这是元家的破虏剑法,讲究人剑合一,迅捷有力,一虚二实三探首,三招毙敌。”萧洛河望着他的背影,解释道。
“三招内毙不了敌,该当如何?”男子转过身,露出三根手指,质问道。
“稍稍强劲,或应变较快的人,都能接过三招。”萧洛河承认是很难三招毙敌的。
“所以,也只是一个嘘头。”男子颇为自傲,眼神又飘忽到一旁,很快给元家的破虏剑法盖棺定论。
“力与速本就是一对悖论,重剑当如此,求力,自当减速,虚实有数,不全然只凭蛮劲,肘腕灵活,加之微步,也能身轻如燕,急急如风,劈砍刺挑,快意恩仇。”萧洛河一边说,一边用剑笔划着,这一番理论让男子觉得新鲜有意思。
“行侠仗义是所谓的道么?”男子换了话题,眼神也回到萧洛河的身上,服虽脏、发虽乱,但为人精神挺拔。
“算是吧。”萧洛河略有迟疑,可能是没想他会有此一问。
“这么说,那些轻贼盗寇,还有山精野怪们一定是无道之辈。”这位奇男子顺着话下圈套。
“那我行的不是道,是仁。”萧洛河觉得有必要纠正他的认知。
“仁?仁是不是一种欲?”男子对萧的话提上兴趣,也期待着他的回答。
“仁者见心,当然算作一种欲,不过不是邪之欲,不是淫之欲,是一种正之欲。”萧洛河对自己的一番解释很满意。
“哈哈哈,本尊还是第一次听到欲分正邪之欲,你确实很有意思。”男子有些欣赏他,双手也背到身后去了。
“鄢国将灭,你何要往回走?”男子发问。
“因为我是鄢国的大都督。”萧洛河神情严肃的回答。
“哦?见你打扮,本尊还以为你仅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流寇。”男子打量他上下,凌乱散发,一身布衣,确实很难教人把他和一个大都督联系起来。
“流寇如何?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是鄢人应有血性。”萧洛河的话刚毅坚定。
“纵然身死也不悔?”男子再问。
“为国而死,其哀也荣也!”萧洛河似乎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
“很好!本尊很欣赏你,你叫什么名字?”男子褒赞。
“萧-洛-河!”萧洛河一字一字顿从口出。
“本尊记住你了,既然赴国之难,怎能无甲胄良骑,本尊赠你了!”男子话毕,大袖一挥,乌金锁甲穿在萧洛河身上,汗血宝驹出现在他一旁,而男子消失不见。
遇神人也,萧洛河感慨道。
返回鄢都的路上,集结鄢地亢勇男儿一万人左右,少数能够配齐甲胄、刀剑与马骑,多数者是脚着草履,身披汗褂,手抡田锄与镐械,再不济者,只有一根端头削尖的竹棍。
但每一个鄢国人的脸上,写满了国仇家恨,每每冲杀都有一种痛杀敌贼,慷慨赴死的气概,无不教人动容落泪。
纵使萧洛河有百般能耐,手持破虏剑斩杀敌首百余人,终究无力回天,鄢国公本指望丹国出手相助,不料丹国亦是狼子野心之徒,郐、厉、丹三国强强联手,将鄢国瓜分殆尽。
萧洛河战死在城门之下,身中数箭,右手持剑杵地,使得自己不被击倒。几个敌国士卒小心翼翼向前试探,突然一只猛兽从破虏剑中冲出,瞬间将人撕得粉碎,继而消失不见,萧洛河也应声倒地。
鄢都城门洞开,一片血海汪洋,贪婪的敌军不断涌进,鄢国公大悲:
“国失我手矣,国失我手矣!宁作亡国之君,不做亡国之奴也!”遂尔自尽身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