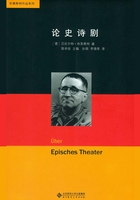接到半分钱姐姐的电话,是在一个阳光洒在房间里的温暖秋日的午后,我从睡梦中挣扎着起来按下接听键。
“极光,是我哦,你还在北京对不对,我下午4点半到南站,来车站接下我吧。”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完这一段话,半分钱姐姐毅然挂断了电话。
我在这个惬意的中午,莫名地感到一丝寒意。
从小到大,半分钱姐姐在整个年级甚至全校都有着超高的知名度。
这种知名度来源于她“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理念。
省,是可以概括半分钱姐姐整个教育阶段的关键字。
每周六下午放学,住校生总会归心似箭飞一般冲出校门,半分钱姐姐会抓紧时间赶回宿舍,在宿舍封锁大门前,用公家的水洗完整套校服、床单被罩后才心满意足地凯旋回家。
如果一位同学问一道题,半分钱姐姐一定会向其索取一个苹果之类不等的劳动报酬。
然后她会用替人解答问题换取的小刀,将替人解答问题换取的苹果分成均等的四份,每个课间吃一份,说是为了均衡营养。
而半分钱姐姐吃的大多数苹果,几乎都来自于当时成绩平平却又力求上进的我,那个学期里我付出了将近半箱苹果的代价来换取半分钱姐姐的谆谆教导。
直到现在,不明真相的母亲大人还误以为我是真的爱吃苹果。
半分钱姐姐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家庭贫困,且实际上她的家庭条件比一般同学都要好得多。
朋友们在忍受了半分钱姐姐无节制的占小便宜之后纷纷毅然与其决裂,而彼时仍是一枚孬种的我就成了陪伴她左右的供奉苹果的唯一人选。现在想来,我进贡了那么多只苹果,她却从来没有切好之后分给我其中一份过呢。
我坐在出租车上一边回忆,一边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急速往后倒退,仿佛那些回首观望却发现如此经不起推敲的日子。
但当我在南站苦苦等候了近40分钟后,半分钱姐姐的电话才姗姗来迟:“我在汽车站呢,你在哪儿?”
我匆匆跑去,穿过不算拥挤的人群,看到半分钱姐姐以一种怪异的姿势站立在长途汽车旁,在北京的大风中摇摇欲坠。
为了节省30元钱的差价,她选择忍受七个小时的汽车颠簸。
事发突然,我还没来得及帮半分钱姐姐订好宾馆,当我向她坦白之后提出陪她一起去找宾馆时,半分钱姐姐的目光久久地在我身上徘徊,有一种立等可取般的即时感。“你是一个人住吗?”半分钱姐姐问。
我点头,半分钱姐姐露出了满意的神情:“那我先住你那儿吧。”
瞧,这就是半分钱姐姐,任何无厘头的事情只要是建立在省钱的基础之上,于她就变成了完全的理所当然。
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什么的真的不能作数,否则我又怎么会立即石化当场?
条件反射一般,我开始竭力向她表示孤男寡女多有不便,再说一个独居男人的卧室是多么羞于见人啊……
而半分钱姐姐神色雍容,似乎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圣母一般的光辉令我产生了一种接受洗礼的错觉。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无法相信自己真的在半分钱姐姐面前退却了,任凭她犹如这片领地真正的主人一样主宰了我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的命运。
第二天一大早,在沙发上睡得超难受的我就在足够吵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噪声下被迫醒来。模糊中看到半分钱姐姐十分贤良淑德地在帮我整理衣柜,我立刻惊醒,刚要道谢却发现地上还杂七杂八堆着许多衣服。
“我看这些衣服的大小已经不合你的尺寸了,干脆送给我得了。”半分钱姐姐语气轻快而又理所当然,并没有什么我可以参与决策的意思。
但这又仿佛确实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于是在我的沉默中,半分钱姐姐一边继续挑拣,一边用一个不知哪里找来的巨大的尼龙袋收走了那堆衣服。
其中还有一条名牌牛仔裤,这让我不得不感叹半分钱姐姐是个识货的女子。
半分钱姐姐作妖事之二,就是洗衣服,不停地洗衣服。
半分钱姐姐以每天两套衣服的速度换洗,我的耳边永远充盈着水龙头上“哗哗”的水声和洗衣机“嗡嗡”的运转声,似乎身在一个极为机密的工作基地中,默默地活成了一个房客。
半分钱姐姐作妖事之三,就是卖废品。
她在严肃地批评了我家里太乱和象征性征求了我的意见之后,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我房间各个角落堆砌着的纸箱纸盒和各色饮料空瓶全部整理好,交给了一个收购废品的大叔,然后默默地把换来的钱收好,临了还义正词严地环视房间后对我说:“看,这样多干净整洁。”
我度日如年,开始试探性地问半分钱姐姐这次来的目的,“找人。”
半分钱姐姐的回答简单明了又透露出“别多嘴”的潜台词。
我也真的没有多嘴,只是每天偷偷掰着指头倒数剩下的日子。
半分钱姐姐离开那天,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已然人走茶凉。
半分钱姐姐没有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她带走了几个一直被我冷落的靠垫和我专门为她备下的牙刷和毛巾。
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也不曾听到她有别的什么消息。
半分钱姐姐就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在我的生命中潇洒地呼啸而过。
直到近期的一次同学聚会,半分钱姐姐也没有参加。席间大家谈笑风生,我忍了再忍,还是没忍住向别人打听起半分钱姐姐的情况。
“她今天有个募捐活动,来不了了。”
“募捐?”这两个字跟半分钱姐姐联系在一起,总觉得有种微妙的尴尬感。
“对啊,她是少年儿童基金会的志愿者,还有其他一大票的公益组织。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她已经算是老成员了,真是想不到。”
我没有再问下去,默默在心里抽了自己两个嘴巴。
后来我又听说,因为做公益几乎没有什么积蓄的半分钱姐姐辞去了工作,去一个偏远山区做了支教老师。
我时常回想起我们那一个星期的室友情缘,并因此暗自悔恨。
我们总是以为自己看透了什么而沾沾自喜,于是太多的成见遮蔽了我们的双眼。
如果下一次还有机会相见,我想我会拥抱半分钱姐姐,哦,不,是半分钱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