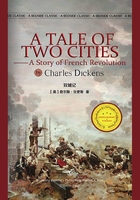杨思倩下班回到宾馆,她一进门就瘫坐在地,头无力地靠在床沿上。房间里异常安静,就连杨思倩呼吸的气息她自己都听得很清晰,这可怕的寂静仿佛是一团黑魆魆的魅影,重重地压迫在她的心上。
杨思倩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播放她最喜欢的歌曲《回忆的沙漏》,“像流星的坠落,灿烂夺去了轮廓,这刹那过后世界只是回忆的沙漏,像流星的坠落,绚丽地点亮了整个星空,像你故事在我生命留下不褪色的伤口......”如泣如诉的歌声仿佛是在诉说着杨思倩的心声,她听着听着,顿时泪雨滂沱,是啊,李昱就是一颗划破天际的流星,他用热血和生命点亮了无边无际的夜空,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他的光亮却如此璀璨夺目、熠熠生辉。
杨思倩一边流泪一边回想着李昱生前的点点滴滴,她至今都不敢相信,那个喜欢吟诗颂词的李后主走了,那个喜欢和自己拌嘴的李哥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他还没有来得及向父母告别、没有对妻子说一句知心话、还没有看一眼自己的孩子,他就急匆匆地走了,杨思倩回想起自己眼睁睁地看着李昱被推出隔离病房时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她浑身颤抖。
突然,杨思倩起身走到镜子前摘下口罩,她凝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庞,脸颊上被口罩勒出的痕迹清晰可见,杨思倩解开盘在头顶上的头发,栗色的大花卷自然而然地披散下来,杨思倩摸了摸柔顺的秀发,然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朝着自己的头发用力地剪下去,霎那间,一缕缕的头发悄无声息地飘落下来,它们好像是被风雨吹打过的花瓣,顿时失去了原来的生机,凌乱地散落在地上。
第二天早上在宾馆的大门口,夏鹃和杨思倩都被对方的模样惊到了,夏鹃的双眼红肿得像两个大桃子,她昨天晚上哭了一夜,夏鹃接受不了李昱离开的事实,她在心里反反复复地问自己,这么年轻的生命、这么好的同事,怎么就没有扛过去呢?白发人送黑发人,李昱的父母该有多么悲痛啊。
“夏主任,你的眼睛肿成这样,怎么不戴副墨镜?”杨思倩盯着夏鹃的双眼问。
“墨镜放在家里了,没有带来。”夏鹃回答。
“你昨天哭了很久吧?”杨思倩继续问。
“嗯,同事一场,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李昱看起来嘻嘻哈哈的、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其实,他的内心特别善良纯真;你别看他平时斯斯文文、还有点柔柔弱弱的,但他给病人插管的时候动作麻利、勇敢果断。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同事之间天天在一起上班,我们与同事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同事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重要陪伴。”
杨思倩点点头,而后叹道:“唉,这么好的人走了,老天真是不开眼啦。”
夏鹃摸了摸杨思倩参差不齐的头发,责备道:“这么漂亮的头发剪掉了多可惜啊,你不该剪的。”
“我这是剪发明志,以表我的决心。”
“没有了漂亮的头发,我看你怎么做新嫁娘?”夏鹃嗔怪道。
杨思倩听了夏鹃的话,忽然记起曾经和李昱说的玩笑话“待我长发及腰”,杨思倩的鼻子一酸,带着哭腔说道:“李医生为了抗击新冠病毒,他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我只是舍弃了自己的头发,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夏鹃见杨思倩又哭了,连忙安慰道:“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头发剪了感染的风险也就降低了,只是你自己剪得参差不齐,今天晚上下班后,我再帮你修一修,你干脆和我一样,剪成男孩子头。”
杨思倩含着眼泪朝着夏鹃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