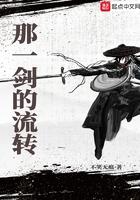“司徒兄,你说贵妹在上面与云,奥不,与三皇子殿……”
小楼下,司徒南恶狠狠瞪了神情古怪的黄子易一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当人人都是你这般好色之徒么!我呸,你小子就是三天不打皮痒,欠收拾!”
“司徒匹夫你少拿爷撒气,坑坏我宝剑之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直到如今我方才明白,原来你们兄妹俩是合伙演了一出大戏啊,更他娘可气的是把我当傻子哄。匹夫,赔我宝剑来!”
黄子易自觉占理,顿时撒起了泼。司徒南面色难看,却也不好说什么,这事儿确实是他兄妹理亏,蓦的,他眼睛一转。
“子易啊,得知殿下真实身份后,你就没有什么想法么?我兄妹固然利用了你,但也并不是白白利用,如若不然,你岂有机会得知真相?世间之事本就祸福相依,你那破剑值几个钱?”
黄子易闻言沉默,随后叹了口气,“司徒兄,我不是傻子。与你们兄妹不同,我非长子,胸中也无多少墨水,虽会些武艺,但又如何能入皇子殿下之眼?”
“啧,这倒是个麻烦。”司徒南轻叹摇头,但见黄子易神色黯然,心中未免不忍,便出言缓和道,“谁教你爹厉害,生了足足六个儿子,七个女儿,你小子好色估计就是随了根儿了。”
“匹夫,你欺人太甚!”黄子易闻言双目瞪如铜铃,差点儿动手,好在李云青来的及时。
“司徒兄也是好意,黄兄便饶了他吧。”李云青缓步来到二人近前,劝道,“黄兄聪慧,应能明辨善恶,司徒兄方才所言我听到了,虽然过分了些,却是真心实意的劝解,念其一番好意,黄兄便饶了他吧。良师益友,古来难寻,得其一便受用不尽。”
“殿下所言甚是。”紧随其后而至的司徒静出言道,“我兄长匹夫粗人,向来不会说话,黄世兄大人大量,就不要计较了。”
“对对对,小妹说得对,我是粗人、匹夫,黄兄见谅。”自知失言的司徒南拱手致歉,情真意切,倒是个可爱之人。
黄子易心如明镜,微微摇头叹了一声,“哎,我懂的。”
“黄兄啊,有些话,本不该我说的。但与你相交一场,实在不忍你意志消沉,如司徒小姐与我所言那般每日放浪形骸。”李云青神色郑重,认真的道,“人生于世,来也干净,去也干净,王侯将相也好,普通百姓也罢,不同之处甚多,但相同之处亦不少。
出身豪门自有其优,身份尊贵自有其良,但历数古今,封侯拜相,成就大功业者,却多为布衣草莽。远的不说,只说我李氏先祖,生于乱世,上数九代俱是农户,后来呢?起兵幽州,建不世功业,定鼎开国,与齐楚燕韩庆魏晋赵同列于世,由此可见。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现如今,奸佞于朝,幽州不稳,关外又有异族蠢动,正是男儿建功立业,报效家国之时。
黄兄堂堂七尺男儿,何故白日放歌纵酒,浪费大好青春?”
噗通,黄子易跪倒在地,“草民黄子易,愿投效殿下,甘为马夫仆役,望殿下不弃收留!”
……
司徒将军府。
“妹子,这位三殿下真是好生厉害啊!三言两语,愣是说得黄子易恨不得给他卖命,乖乖,这张嘴都比得上那帮腐儒了。”
“兄长慎言。你我兄妹既已投入门下,便应恪守臣子之礼,无论人前人后,都不该妄议。”
“妹子所言有理,为兄我记下了。只是,妹子啊,你当众道破殿下身份,他没有怪你么?”
“当众?哪里当众了?且不提你我兄妹,当时在场的,唯有黄子易算半个外人。兄长啊,你以为黄子易真的是感动涕零方才投效的么?实在太天真了些。”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其一,三殿下最有望继承大统。其二,黄子易并非家中嫡长,此生功业无望。其三,我道破殿下身份,黄子易若想活命,唯有投效一途,否则即便殿下不杀,我也要杀之!”
“妹子,你……”
“为臣者,当事为主忧,黄子易若不投效,终为后患。即便如今投效,也要严加防范,免其鼠目寸光,卖主求荣坏我大事。兄长即刻便遣人监视,如有异动当以雷霆电势除之,绝不姑息。
此番之所以捎上他,一是因其心思还算玲珑,可堪造就。二则是,你我兄妹之首功。若他忠心效主,便是荐才之功,若他头生反骨,便是除患之功。”
“妹子啊,我是你亲哥不?”
“兄长何意?”
“我脑子笨,哪怕有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会给你数银子。妹子啊,我是你亲哥,可别卖我。”
司徒静闻言当即跪了下去。
“妹子你咋了,快起来。我就是说说,说说而已啊!”
“兄长方才所言,字字如刀刺入我心。小妹惶恐乞饶。”
“哎呀,我错了,为兄错了还不成吗,妹子你快起来。”司徒南赶忙把自家妹子搀了起来,附身拍了拍其流裙上的尘土,“妹子啊,兄长我胸无点墨,守业尚且艰难。父亲膝下唯有你我,理当相互扶持,本来我是想。
且不提光宗耀祖,能守住咱们司徒家的基业就很好。但这两天为兄观你行事,颇有春秋苏仪之风,谈笑间游刃有余,说句大不敬的,便是皇子殿下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呐!妹子且勿怪为兄失言,实在是有感而发。”
司徒静闻言,摇了摇头,叹道:“兄长啊,小妹自认,若论智计谋划,足可排进当世前列,但比之苏仪,未免过了。
还有便是,兄长啊,你觉得能说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皇子殿下,岂是被他人玩弄于掌中之辈?
当时阁楼之上,我与殿下二人密谈,惊出了三次冷汗。殿下眼中杀气自起便从未淡去,几次达到顶峰,欲要取我性命。”
“什么?!”司徒南顿时大惊失色,慌了手脚,“妹子,实在不行咱们不跟他了。以你智慧,保全司徒家足够,何苦每日跟他提心吊胆,不行,绝对不行!”
“兄长勿慌。殿下只是想过杀我,但终究没有动手啊,今日不杀,日后便性命无虞。最危险的一关,咱们已经过了。”
“还是不成,万一他成事之后翻脸不认人呢?当皇帝的哪个不心狠手辣,不行,这不行!”
“兄长,三殿下眼界非常,我已证实,其此番来扬,正是为了慕容冤案。若其登临大宝,定是贤明之君,百姓之福。
他本可掩饰杀气?却始终杀机毕露,为何?不过是想敲打我罢了,若非惜才,大可不必如此作为,何苦让我心生嫌隙呢?
如此便可明证,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辜负旧人的。而这也正是其最大缺点,为君者,不可有情有义,但即便是对我这初投之人,他也全了为主情义啊!
古语云,良禽择木而栖。在我看来,为主者可以无能,可以无贤,但必须有情有义,唯有情义之君方值效忠,这话与帝王无情自相矛盾,可换而言之,若君完美无缺,要谋臣何用?
世间之事无有十全十美,两相其害取其轻方为良择。这是殿下教我的第一个道理,我深受触动,今用于此,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