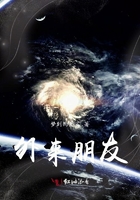一弯明月悬在夜空中,皎洁的月光照在医馆的牌匾上赫然露出了几个大字---当归阁。林砚不在意的撇撇嘴,心里却把安乐街上这一处小小的变化记了下来,安乐街这条街上都是些老牌子,能在这儿开张的,背后总得有些势力才行。
林砚只停顿了几息时间,起身朝那群正驶向京城的车马而去,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行踪被暴露在街角的乞丐眼里,亦或者根本不在意这卑微的生命。乞丐又朝外看了几眼,窸窸窣窣的爬起来,蹒跚的朝深巷里走,不久便传来细微的敲门声,叩,叩叩,叩,叩叩......
夜色是最好的保护色,一切都在进行,且不为人知,当事实暴露在阳光下,人们是惊讶,害怕,愤怒,怀疑,还是不为所动呢。
“七爷,太子殿下派我来接您回府。”
韩七闻言撩开马车的帘子,只瞅见了林砚一人,当下便冷了脸:“你们家那位,当真只派了你一人前来?”
林砚扶正了脸上的面具,又拱了拱手,道:“殿下以为,京城内人多眼杂,万一走漏了风声.......”韩七冷哼一声,便不再多说。
林砚撤开身子,“大人,请。”一群人浩浩汤汤的前行,只留下林砚一人,他抬起头心中疑惑:殿下怎么会这个时候传书过来呢。疑惑归疑惑,他伸手让信鸽停下,将信纸抽出来,纸上赫然写到:东西是假的,见机行事,切不可冲动。
“兔有三窟,无碍。”林砚的眉头很快抚平,东西早晚会到手,并不急于一时,最可喜的不过就是他的小殿下,在这件事之后也能学会什么叫“人心难测”。林砚又看了看手中的纸条,无奈的笑了笑,这么明显的意图,看来他的教导之路还很长啊。
林砚跟上车队,将他们安置在一座闲置的府邸,随后换了一身儒衣,摘下面具,赫然是一个儒雅书生的扮相,他看向窗户,透过窗纸看到外面已经微微发白,天要亮了。“既然没法去见殿下,那就先去探探那个医馆的底细吧。”他微微一笑,离了客栈朝安乐街走去。
与此同时,皇城内某一处地牢里,却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啊啊啊啊饶了我饶了我啊啊啊,别过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一阵阵求饶声从一个血肉模糊的物体上传出,若不是口吐人言,你根本无法相信,这居然是个人?
秦桁今年16岁了再过四年就该行冠礼了,可眼前这个不能称之为人的人却是出自他手。“疯了?”秦桁有点婴儿肥,脸上的稚嫩还没完全褪去,任何人看到都会心生喜爱,忍不住想揉揉他的脸,可这个唇红齿白的少年郎,嘴里吐出的话却冷漠至极,“你逃避现实的办法可真真管用啊......”他顿了顿,瞥了身后几人一眼,又道:“一个人若想更长久的活着,那么就努力的增加手中的筹码,可别让我失望啊。”他身后几人闻言,均跪下齐声道:“诺。”
秦桁心情极好的走出地牢,他适应了外面的光线后,便朝永乐宫走去,“这次效果似乎不错啊。”疯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却获得了心腹之人的忠心,他冷笑一声,不知道帝王之道是不是这般取舍的呢。“不过,言之昨晚居然没有来见孤,等他回来定要好好罚他。”话音刚落,一个戏谑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六弟怎么又要罚言之?”
“三哥?你怎么来了?”秦桁闻言惊喜的问到。秦默一直住在京城外,鲜少回到宫中,这一次想必是为了太后的生辰吧。
秦默顿了一下,又笑道:“三哥回来难道不是好事吗?我先去向父皇请安,回头再去找你。”“三哥慢走。”秦桁盯着他的背影,直到看不见才收回眸子。
当今太后与秦默的生母虞贵妃乃是同宗,两人自是希望秦默能成为未来的帝王,只是当今圣上不知为何在秦桁出生当日,便下诏立其为太子,但是其生母在产后三天因感染风寒去世。试想,一个连思想都还没有的小孩子,纵使有皇帝照看,在这尔虞我诈的宫中,他又能躲过几次暗箭呢。
“可我就是活下来了。”秦桁想起往日种种,忍不住出言讽刺,“我真要好好的感谢你们啊。”随后,他放松下来,轻轻笑了笑,缓缓道:“言之,谢谢你。”在他还是个稚童时就一直在他身边,即使那时候他的言之才十二岁。
只是他的言之对他太好了,对于当时的秦桁来说,林砚就是他的信仰,替他挡下一切未知的危险,以至于他都忘记了,人心到底是如何。不然他怎么可能轻易相信那个韩七呢。“我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啊,...蠢死了,呼——,言之回来肯定要笑话我...”秦桁朝永乐宫走去,口中的话被风吹的支离破碎,听不清楚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