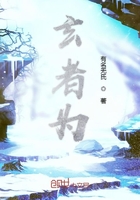她只追到冷然刚才的位置,如同一朵正在绽放的花朵,却忽然凋谢。
冷然固执要走的心停了停,不是因为紫嫣的冷嘲热讽,而是由地底传来了死亡的声音,那是一声沉闷的枪声。枪声打破了对抗的气氛,却袭来了一股浓浓的阴霾。
“你不记得我说过的话了?只有在我身边才最安全。”也不知三月堂主怎么地就到了冷然身边,恰好拦住了他的去路,显然怕他趁乱逃走,仍旧冷冷地说,“随我来吧。”
斜斜的楼梯下端有一个方才被忽略的暗门,紫嫣很灵巧地打开,率先抢了进去。
这时,如果飞出一颗子弹来,后果可想而知,她难道一点都不怕吗?
怕又该如何?
她还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保护后面的人,也就是从小带她长大的师娘。
当然,像她这样从小接受训练保护师娘的人,还有很多。
也就在她钻出来的时候,正对面的墙里也有一个小暗门倏地却是合上了。这里居然有埋伏,而且里头的护卫显然不止一个。
现在,她的前面也有了一道安全的屏障,一个全副武装的黑衣人正悄悄地贴壁而下。
几乎与一楼平行的碎石阶梯,笔直地逆向通往地下室。
地下室里,已经有了灯火,照得通明。
但走完最后一层台阶的冷然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随之而来的却是今天晚上的第二个目瞪口呆。
如果说一楼的各式各样有些凌乱的话,这里则是整齐划一放眼过去,一排排有序的书架上几乎没有空格,满满地堆砌着厚薄不一的图书。他仿佛置身在知识的海洋里,心内莫名的一热。
但是这种心情没能维持太久,文明褪去,杀戮登常
靠老井的那堵外墙,几排书架的尽头,一声枪响,却倒了三具尸首。
此刻,已有一帮人正在迅速地打扫战常
默默地看了一会,稍微靠后站着的三月堂主脸色明显地不豫。
心领神会的紫嫣抢先发问:“小孟,怎么回事?连这里也不安全了,你这个舵主怕是不要当了。”
一个蹲着身子的黑衣人连忙停下手里的活,扭头站了起来,正是小孟。
他趋前几步,讪讪地说:“老板娘受惊了,当真是该死。是这样的,刚才和几个兄弟巡察过来,听到里面有动静,便叫上了小石的人,兵分两路摸黑进来。”
“我们说好了以灯亮为号,一致采取行动。但对方似乎早有察觉,灯刚一亮,大部分都给走脱了,只留下三个手脚稍欠麻利的。”
紫嫣皱了皱眉,难以置信地偏过头,面向站得很远的一个年轻人说:“你们由外头包抄进来,居然会被人走脱了?”
那袖手旁观的年轻人显然就是小石,听到紫嫣的问话却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他的表情有些麻木,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有如一尊塑像。
沉默,其实也能算是一种回答。
从小一起长大的紫嫣哪能不知道小石的脾性?
紫嫣也就不去和他一般计较,转眼便见小孟对着身后比划了一下,解释说:“他们都是由这堵墙里逃出去的。”
“墙里?”紫嫣徐步过去,曲指敲了敲,厚实的石壁纹丝不动,掉头就说,“这怎么能出得去?真是活人说鬼话。”
谨以这些冒似华丽忧郁的短篇,让你靠近子迹的世界,精彩的空灵我分明地听到了几声鸡鸣,仿佛觉得你就在我跟前,又似乎在黑暗深处用一种无奈的眼神望着我,为我说了一个很荒唐又残缺不全的故事在着恼。
生活本来就是一杯白开水,时间与空间冷淡地把那些酸甜苦辣电割成一粒粒似乎看不见的微量元素。我能说什么呢?我的感情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就好像先前轻手轻脚地起床以为攫住了一点东西,此刻又很矛盾,只是无谓地作艰苦地自我挣扎状。我实在给不了什么真言哟,你是不是也在选择?选择一种接近旁人无法理解的曼妙的心情去体味去感觉?
在这城市渐明未明的澄空,会有一种情怀让人刻骨难忘。我恍惚间看到了云海深处走来的他,为我悄悄地捎来一颗星。
夕阳沉落,暮色由陆羽茶庄的前厅侵入雅间,你能想象它的另一端变幻无常吗?我蜷缩在沙发上,无形的幽光一浪一浪地如潮涌来。任你负隅顽抗,绷紧臂弯,却越发地感到莫须有的惆怅。
凤尾草和红花图案的绿帘已然严严拉上,几幅用金银各色丝线绣着的狩猎图依旧静静地待在墙上,给昏黑更添了一层诡秘。
一个女人迈步进来,带着几分鬼气的落寞。她也没有习惯开灯,步子好沉由远及近,最后伫足而立,隔着茶几对面俯瞰我。
我伸直了腿,宁愿低垂头。我看也不用看,知道是她。
忽然一声叹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真正的叹息之声,轻微而且悠远。随着这与死亡很近很近的声音渐落,她无言地缓缓地坐了去。
前厅的灯恰巧亮了,闪着耀眼的光刺到我的神经。我艰难地搜索,把目光定格在一副别致的挂历上。10月13日,昨天没有被翻过去,仿佛就要人们记住这个悲哀的日子。
这个悲哀的日子失去所有的人性,罪恶杀死我的表哥迟天成,还把他的尸体用利刃肢解成两佰多块的血肉模糊抛到护城河去。我努力地压抑情绪,有些哆嗦地掏出香烟,点燃了搁到唇边。星火忽闪忽灭,辉映我惨淡的脸。
这时,敲门声扣了几下,然后好亮好亮,彻底把我推到对面。我们隔着一个服务员装扮的女孩,就这样凝望着。她的目光散淡而迷茫,朦胧中浅浅的晚秋的风韵。
当女孩做足最后一个动作,她说:“不用进来了。”语音柔弱却有不容拒绝的迫力。她端过一杯红茶,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纳入口中,神色依然落寞。我盯住她,感觉有一张浓厚的大网向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是你吗?”我阴郁地掐灭另一支烟,她倏然停祝余烟缭绕,透过烟圈她那端着茶杯的手微微抖颤,却没有要说话的样子。她略为思索,又抬起了那盏红茶,目光更加扩散。
我逼到嘴边的话生生地咽了去,不忍打破此刻的沉默,更不敢想象那一丝可怖的念头,那两百多块的血肉模糊怎么可能是她的亲手所为?她的善良贤慧绝不是凭空而来,在她身上常常可以读到人们一贯以为的一个女人所有的优秀品质。十年前我就已经很能肯定,甚至一路走来都有她的影子在激励我,使我能像绅士般宽容地优雅地善待生活。